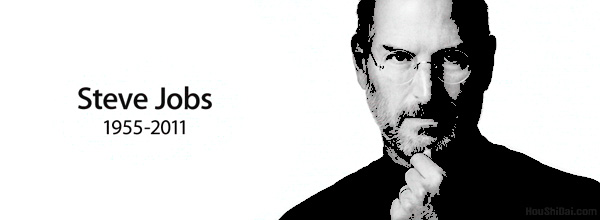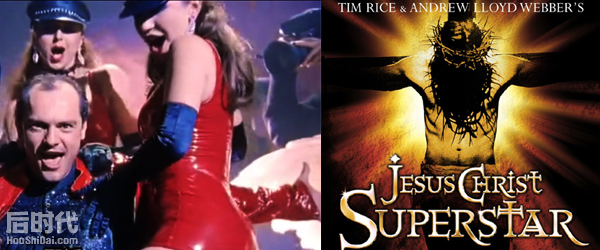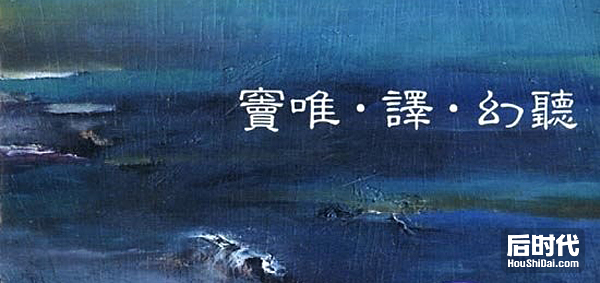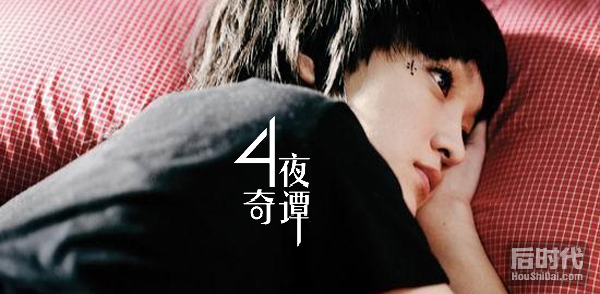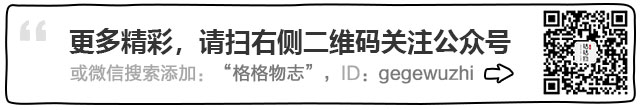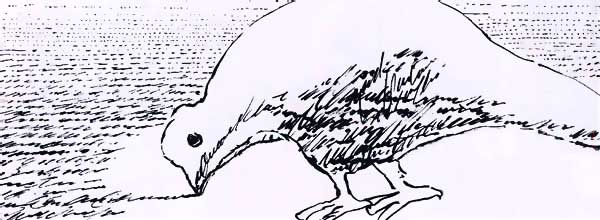八部半 8½ 拍给费里尼自己的电影
这部电影是给专业人士看的,比如说,文艺工作者,精神病患者。一般观众不宜尝试:)

这部电影是费里尼之前所有电影的集中,也是他之后所有电影的源头,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电影导演的创作危机和生活危机。闪回、幻想和梦呓被大量穿插在电影里,人物的内心状态直接地呈现在银幕上。回忆、幻觉、想象以及梦境与现实的片断交织在一起。
看费里尼的电影,就像做了一场荒诞却又真切非常的梦,潜藏在心底的孤独、忧伤、焦虑、邪恶、快乐以及怀念和向往通通一涌而出,马戏团式的布景、嘉年华会式的热闹嘈杂,与空荡的广场、孤独的灵魂相映成趣,在尼诺·罗塔轻快的音乐声中,演绎着一幕幕笑里含悲的黑色幽默喜剧。现代社会里令人窒息的贫困、挥之不去的精神危机、不得安宁的思绪在费里尼的影像中,被净化为一份漠然与坦荡。他拒绝批判,执着地用一种自传式的情怀,呈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描述着我们所不敢面对或者不愿面对的现实生活,因此他让真实变得荒诞,又让荒诞变得真实,最终超脱表面的是非而直抵内心的本质。也正是这样,戏剧化的情节对于费里尼来说不再重要,一种类似于日常生活状态的结构应运而生,没有固定流向的情节和没有因果关系的人物活动,随着角色的心理变化,在混乱多变的主观思绪引导之下,迎来最终的结局。
费里尼的每一部电影,都能给人带来意外和惊喜,他如此执着,又如此纯真,如魔术师般千变万化,以至于让人无法确切的定义所谓的费里尼影像风格。在费里尼看来,电影就是生活,就是一种被视觉化的记忆,所以在他的影片中,没有自以为是的炫耀和卖弄,没有导演的刻意经营,一切显得纯粹自然。摄影机恍然不复存在,电影里的一切顿时与观众没有了距离,不管是公元前的罗马,或者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抑或是淳朴美丽的里米尼,看起来都如同在我们身边,漫画化的影像中,一种苦涩忧愁的情绪弥漫心境,然后是默默的沉思。比利·怀特说:“他(费里尼)是一个一流的小丑,有伟大、独特的想法。”是的,只有小丑,才能在苦闷压抑的世界里载歌载舞、恣肆张狂,却还能得到那些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者的掌声。而取悦别人,满是欢笑的脸上,那两行晶莹的泪珠,分明记载着小丑的细腻和不为人之的悲怆。从这点看来,有谁能比小丑活得如此多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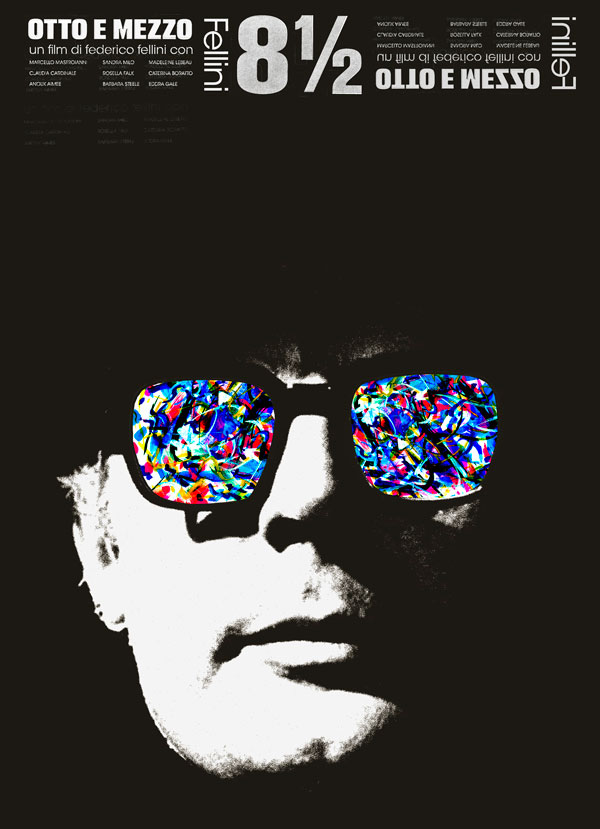
《八又二分之一》片名:
费里尼早期的创作一开始走的是关注物质贫困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道路。但从1954年的《大路》开始,费里尼接连拍摄了孤独三部曲(《大路》、《骗子》、《卡比利亚之夜》),并与新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他的作品开始关注人的心理贫困的问题。1962年当他着手开拍本片时,之前他拍摄了给他带来极大声誉的讽刺资产阶级腐烂生活的《甜蜜的生活》人人都期望费里尼的下部作品同样是部杰作。
但费里尼却陷入了创作危机。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拍什么。虽然制片人已经准备好了资金,演员和工作人员也都到位,他依然没有头绪。
直到一天一个工作人员生曰,请费里尼参加生日宴。工作人员说期待费里尼拍出好电影,费里尼灵光一现,决定以自己的创作危机为题。
拍一个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的导演。
之前他一共拍过6部长片(《白酋长》、《浪荡儿》、《大路》、《骗子》、《卡比利亚之夜》、《甜蜜的生活》),1部与人合导的长片(处女作《卖艺春秋》),以及两个集锦短片(《都市爱情》、《三艳嬉春》),从序列上说(6+0.5+0.5+0.5),本片是他的第“八又二分之一”部电影。
因此影片取名为《八又二分之一》。
才思濒临枯竭的导演Guido和他的制作班底来到一处疗养胜地策划他的下一部电影,同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努力促成这部电影,但是没人真正了解Guido的意图,他们无形中构成的压力使Guido与原本构想的电影越来越远。
Guido想从梦中找寻灵感:他梦见自由的飞翔,却被人拉回到地上(拉回到现实生活)。他一次次梦中父母、妻子、友人,可他们都离他而去,留下他独自哭泣。
Guido想从童年找寻灵感:他想念幼年孩子们互相吓唬的咒语,他想念上学后与同学一起看住在海边的女巨人Saraghina跳桑巴舞,她巨大的身躯,她的粗糙、旺盛就像活生生的“大地母亲”,可是小天主教徒Guido被迫与大自然的本性隔绝,学校只允许他欣赏修女的干尸(典故见Lourdes修女木乃伊)。Saraghina一段唯美抒情,有着童话故事的色彩。可是Guido的编剧却认为这段故事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和深度。
Guido想从爱情中找寻灵感:他把多年前的情人Claudia视为缪斯女神,每每把她幻想成女主角,可是当Claudia真的来到Guido面前,他又觉得她只是个生活中的爱神,达不到影片的高度。Claudia都不能使他满意,就更别说助理们挑选的演员了(试镜这段太搞笑了,很尖刻)
Guido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只能让他对现实更加失望,他赌气想着自己被记者们逼得爬到桌子下面自杀了。Guido的痛苦在一切电影人、一切艺术家身上都那么普遍,这种现实对幻想的扼杀永远存在。Guido最终想通了,他的记忆虽然痛苦,他身边的人虽然庸俗、做作、不可理喻,但这都是他思想的源泉,所以他谅解了生活,并在电影的结尾给出了一个现实与梦想融合的场景(所有演员拉起手跳圆圈舞)。
在我看来马戏团小丑和影片的结尾是最“超现实”的,因为马戏团小丑是始终游离在故事之外的旁观者,既不属于Guido的幻想,也不受Guido现实生活的限制,他是与导演Fellini同样高度的“世外智者”。故事的结尾之“超现实”,在于我们都知道现实永远不及幻想,Guido的电影可以不拍了,Fellini的《八部半》却要给出个结论,“无从解释的解释”多少会牵强。
Guido的扮演者Marcello Mastroianni英俊又带点孩子气,这张永远挂满疲倦、无奈、牵强的脸,让人实在不忍心责怪。整个电影都有点舞台风格,置身其间的摄影机就像迈着狐步的舞者,优雅的从一个舞伴转到另一个舞伴,模拟着导演注意力的角度。演员们的表演典型可爱、故事梳理得很细致、想象力开阔,两个半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确实是部有趣的电影。

关于《八又二分之一》的若干镜头、若干场戏、若干个梦和意识流的解说——
在50年代,随着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的作品,《野草莓》以及法国导演阿雷乃的 《广岛之恋》等问世,无技巧式闪回为电影赋予了崭新的视听语言;在电影中梦和现实之间的过渡到了,可以直接交替出现的地步,观众甚至分不清楚哪些是梦哪些是现实,按照费里尼的说法:梦是唯一的现实,没有逻辑的梦,常常能反映现实中人的焦虑。
1、
这部电影是由梦和现实交织组成
开篇的这个超现实场景就是梦境
和费里尼的其他杰作一样
表现出让人惊叹的电影技巧和超乎寻常的想象力
把一个成年人精神上的困惑表现的淋漓尽致
以梦境的方式开篇
街道背景布置也许很象他早期的现实主义影片
但很快《八又二分之一》打破了现实主义传统
让观众关注摄影机本身,好似受困于堵车
又急又想知道堵车原因
首次暗示摄影机本身也是本片主角之一
古依多首次出现是他的后脑勺
镜头很快从他的脸上移开
没有汽车声等一切声效表明这是在梦镜
莫名其意的画面以擦车窗动作开始
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擦
接着是男主角导演古依多的车出现了雾
增强超现实和焦虑的气氛
巴士上只有手臂而无面容的乘客
再次暗示我们处于非现实之中
这是由费里尼,分镜头画师皮埃罗,格拉迪摄影师吉瓦尼•迪•凡纳佐共同构思的
车流中的主角除了古依多外
只有卡拉,她是他的情妇
她正被一位陌生人挑逗得很开心
这一模糊朦胧中的紧张感
是本片的主要特点之一
无法明白是什么含义
显然古依多正在做再生之梦
他从车内出来暗指出生过程
本段从痛苦发展到自由解放
可以被看作是死后复活过程
和他的上部影片《甜蜜的生活》开篇里
他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飞过罗马一样
这次费里尼让古依多飞向了天空
仔细看下这两位
马上骑士是克劳迪娅的经纪人
克劳迪娅是古依多新片中的名星
另一位男人是新闻记者
拍片计划如地球引力一样吸着古依多
把他拉他落回现实中后
《八又二分之一》的故事正式开始了
看这个男主角从空中跌落的镜头
直接过渡到了梦醒的现实中
随后镜头的移动
交待剧中人的空间位置 这里出现了三个人物,景别也不同
但却很自然地交待出来了
彷佛人物是自己凑到镜头里来的
但其实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这样的镜头在影片中还有很多
2、
漂亮的横移镜头
伴随着瓦格纳的音乐
前景是老人喝水 看后面远景的虚焦处还有修女
神职人员走过
带出了后面纵深这群修女
镜头又回到了近景
再慢慢移动到指挥的手
出现了指挥的近景
镜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切换
有人称这是个“摄影机的舞蹈动作”
因为这些移动都象芭蕾舞一样精心设计
这几个镜头虽然很短
但经过精心安排
有些人甚至以为是一镜拍成的
Ps:原来镜头是这么讲究的一件事,心驰神往,目眩神迷!
3、
古依多在火车站接站是一个精彩段落
第一个场景,画面几乎看不出具体场景
然后借古依多站起来的动作
镜头开始向右侧横移
场景开始变化
到了这一景,火车进站,跟刚才的景完全不同
这个火车进展的场面十分漂亮
镜头转至了古依多的特写
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他脸上
引起一定的悬念
注意下车的这三个人
一个是教士,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孩子
隐喻了道德和家庭的突然介入
让古依多有些心慌意乱
他马上说她没来,而且有些心安理得
注意他戴上了眼镜,恢复自己原来的样子
此时火车开走,镜头的左右分别出现了
象征道德和家庭的三人和情妇卡拉
古依多的回头其实是犯罪感的下意识表现
代表道德和家庭的三人全部走出画面
镜头马上换到了两人的近景
暗示他们的关系的亲密
那些道德问题都已经被离镜头 如此近的感觉忘掉了
费里尼常使用很简单的镜头和场面调度
但可以表达多层含义
这也正符合了摄影机运动产生含义之说
4、
古依多和情妇在一起
他在这里哼拍子
其实在暗示他对卡拉的这种谈话心不在焉
他对她只有性的要求
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这段做爱戏很有意思
古依多让卡拉扮演一个妓女
这里出现了镜子
镜子的比喻在影片比比皆是
它暗示古依多到了人戏不分的境地
他给卡拉化妆完全象是在拍戏
但其实他们是在生活中,在做爱
但古依多对此很兴奋
他鼓励卡拉这么做
在生活中依然充当导演
镜子暗示了人物迷失在自己的想象中艺术中无法自拔
而卡拉对此没有意识
以为是个游戏
如果她对这种做爱方法觉得不舒服
古依多可能早就抛弃她了
这里即将出现个幻想的梦
古依多做爱后她的母亲出现在房间里
好像在擦什么
镜头转到墓地
原来是在擦父亲的墓
这个擦的动作暗示了古依多在性方面的犯罪感
古依多发现了死去的父亲追随着他到了父亲的坟上
制片人出现了
古依多最担心的事来了
所有他的恶梦最终都要跟创作有关
在这里他的父亲对话
他穿上了童年的校服
可以跟后面的梦相连
这是现代性的表达
因为人的思维是流动的
所以有些电影需要看上几次
才能完整体会其中的妙处
穿童年装的古依多和母亲拥抱
而母亲变成妻子
这个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母子、夫妻间的关系混乱
梦境反映现实
古依多这里的舞步
也会出现在对应的
影片的后半部情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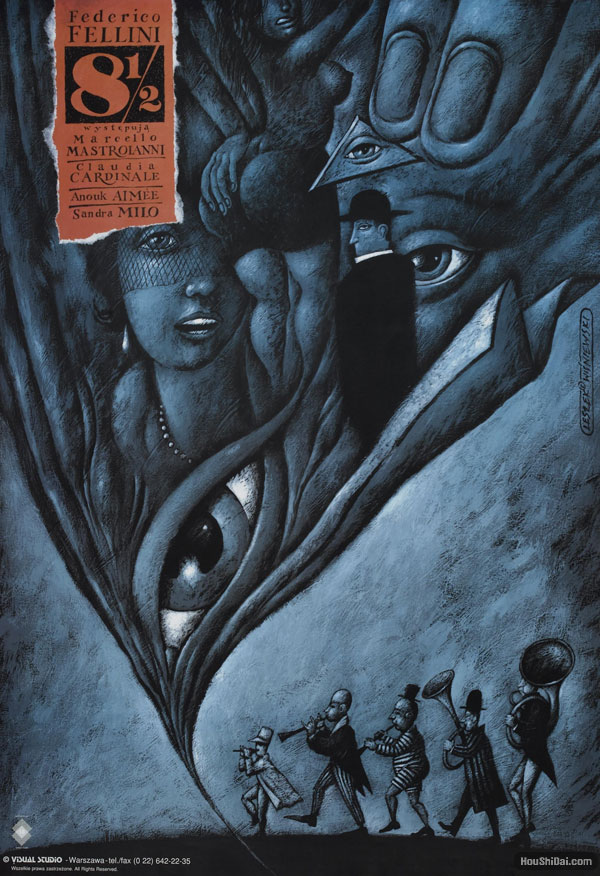
5、
这个段落值得介绍
整个段落一气呵成
从他走出电梯开始
助理导演从画面左侧进入
镜头跟着他们
稍做移动
古依多想逃走
摄影机跟着他
又一人从画面右侧进入
注意每次都是别人进入
古依多的空间
他的生活被这些人搞糟
看这个画面,他还是无法出画
现在古依多似乎是脱离了画框的限制
但其实还没有结束
他和女演员对话不久
在这里
画面远处的记者进入
注意他占据了古依多要逃离的画面左侧
他还是面对这些人
无法从画框中突
镜头在这个女人身上
第一次脱离了古依多
但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他随即又给包围
他忐忑不安
希望能尽快摆脱
镜头转移至女演员脸上
暗示这个段落可以暂停
马上又来一次包围
他漫不经心地挑选演员
其实什么也没有听
当然也无法决定
这和费里尼当时的情况十分相似
整个段落至此渲染了一种让人崩渍的情绪
古依多看到制片人下跪
这个玩笑有些过分
但其实是当时制片和导演之间的真实写照(现在也是?)
古依多象小丑一样展示这手表
这个远景中古依多仍然被困在画面中
Ps:如果没有吴孟达的解说字幕,我一个看热闹的外行是看不出这场戏的精彩的。此时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大愉悦,好比一个初学画画的人在梵蒂冈在米兰在卢浮宫在那些个大教堂和博物馆里看到了那些稀世之作后的震撼,诚惶诚恐,莫名不可言状。
6、
古依多在聚会的时候戴了个小丑鼻子
表示他对这种聚会的反感
他不喜欢这种夸夸其谈的聚会
生活中的费里尼就是这样的人
他对电影之外的东西不感兴趣
摩术师出现后和大家玩的这个游戏即将带出第二个梦境
在刚才的第一个幻想之梦里
古依多从情妇联想到了母亲
再从母亲联想到了妻子
这三者,构成了古依多生命中完美的女性形象
他在生活中寻找这个结果却陷入困惑中
这与他生活中的情况很相似
魔术师让古依多想一个词
他说出了阿萨尼西马萨这句话
这句话在接下来的梦境画面中会有明确的解答
魔术师进入他的心灵世界唤起一次记忆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
一个童年的记忆会长久地储藏在心里
场景变化了
转到了古依多的童年
温暖的童年
古依多在奶妈和袓母照顾下,感到无限安全
在大酒桶里洗澡
注意这个小女孩
在影片后段同样场景中她会以成年人方式出现
洗澡后用温暖的毛毯包裹
哄他上床睡觉
注意这里的黑白光影效果十分突出
小女孩爬了起来告诉古依多不要睡觉
小女孩的这个动作可以在后面再次看到
费里尼的这个经验类似某种儿童拼字游戏
阿萨尼西马萨是意大利语阿尼马的变形
意即心灵、精神、意识
这个梦如此甜蜜温暖
和影片中其他梦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是影片中十分重要的梦
它带给古依多的童年经验影响了他的成人期
这个梦也同样是
费里尼对心理学家荣格的一篇论文《婚姻的心理关系》的一种呼应
论文以女性观点讨论男性心理
荣格指出大部分男性对女性的感情生活的讨论
都是一种心灵投射
这里的心灵在原文中就是阿尼马的意思
荣格指出最吸引男性的
是所谓的狮身人面形女性
既有蓄意勾引的媚术
又有飘忽不定的姿态
因此流露出让人意乱情迷
充满了无限可能
这种女性兼有成熟与年轻
母亲与女儿的双重特质
她与生具来的天真和狡猾
完全能让男性撤除警戒
因此这个梦暗示了在童年时代获得过温暖的古依多
在成年后依然在寻找安全感
费里尼电影最大的元素
在于自由联想
自由联想是意识流中形成思想素材流向的根据
意志对思想的影响越小
自由联想的程度也就越大
比如当一个人集中精神上课时
不受意志控制的意识依然在流动
比如你在看这部电影时
你的思维随时在流动
看到了某个画面
你联想到它是黑白的
马上就可以想到黑白电视机
再从黑白电视机想到你小时候
看黑白电视机的情景
从看电视可能想到黑猫警长
然后从黑猫警长再想到彩色的动画片
从彩色动画片可能想到别的
这样自由思维连续流动
产生无穷无尽的思维源泉
八又二分之一正是这样一个结构
往往通过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一个画面一个人
或者别的
来引出记忆或幻想
而在童年时期产生的未能解决的心理冲突
影响着意识流中的思想的流向
费里尼在试图揭示
他的主人公古依多那些尚未解决的冲突
没有采用拍摄主人公思想中的连续不断的意识流
而是选择了其中的几个幻想
使我们能深入地看到古依多内心状态的联想
有评论认为这部影片有两条线索
一条是叙述
这部悬而未决的影片遭受挫折的故事线索
另一条是由闪回和幻想构成的
旨在探索幼年动机或成年逃避现实的线索
两者平行出现构成了整部影片
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
不单单是一部意识流电影
它还关系到精神分析领域
从这个角度上说这部电影开启了现代电影之门
用美国电影学者所罗门的话来说
费里尼在创造一种新的电影形式
这种形式让本片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即使放在今天看来这部电影也一点不过时
7、
看镜子再一次出现在画面中
狭窄的长廊给人压抑的感觉
而长廊尽头的镜子加深了这种感觉
并再一次把古依多投射到镜子里
而在镜子里的可能就是费里尼本人
精疲力尽地和古依多相互映射
在影片后面还有这样的场面
克劳迪娅又出现了
她代表了导演心目中的美
高于一切
并能给予古依多安慰和温暖
她有卡拉的丰满身材
也有奶妈的温柔体贴
还有妻子的娴淑
她综合的古依多对女性的所有想象
现在在这个私密的空间里
克劳迪娅开始担任另外一个角色
她换上了睡衣
坐在书桌旁
翻阅电影剧本
然后取笑这个剧本
古依多象孩子一样深陷在床上
陷入了困境
克劳迪娅再度出现
她安慰着古依多
她的亲吻具有无穷的力量
也许是爱情之吻
也许是灵感之吻
门钤惊醒了古依多的幻想
注意他起来的姿势
是他陷入的那个原来的姿势
摄影机没有拍他的脸
用脚表示不赞同
表示他还未恢复到成人心态

8、
和主教见面的段落是另外一个心理透视
童年时代的记忆再度被开启
而这开启的方式十分巧妙
通过古依多百无聊赖地四处张望
看到了一个妇女走下山坡
而在她走下山坡时因为怕裙子脏
而拉高了裙子露出了一截大腿
这个简单的动作引发了古依多的联想
打断了他和主教的见面
在这里
天主教的严格教规和粗俗的村妇之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时也开始暗示观众
天主教规和女色对古依多的童年
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也造成了他成人期
对待女性的态度
闪回自然地过渡到了童年
占据画面絶对重要位置的老师
暗示了学校的严酷
在这个画面中古依多彷佛从雕塑中逃出
他的服装,刚才在墓地梦中出现过
大海是费里尼电影的重要元素
代表了自由和纯洁
现在将出现古依多通过
农妇的大腿想到的童年时代
见过的海边妓女莎拉吉娜
古依多送钱给她
她就给他们跳上一段艳舞
其实这个角色很可怜
但在这里却是性的象征
莎拉吉娜代表了费里尼对女性身体的迷恋
费里尼喜欢体态丰腴的女子
在许多作品中有流露
莎拉吉娜一点也不漂亮
甚至有些恶心和可笑
但对于童年的古依多来说
也许她是他心目中最美的女人
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的童年经验
对于第一个性启蒙者有着特殊的感情
即使她是丑陋的不完美的
在这里,则是违背天主教义的
所以在这个段落里
观众可能不会觉得舞蹈很可笑
反而会产生自己的童年回忆
一些失落的往事
教士追古依多一段故意加快了影片速度
象是默片的追逐戏
产生喜剧效果
这个镜头也是横移
但开了个视觉玩笑
也有很强烈的讽刺效果
审判的仪式有点恐怖
因为这些教士其实是由几个中年妇女扮演的
这里古依多和母亲见面
母亲做作的表演增加了这里的喜剧气氛
也暗示了其实她内心没有觉得这是一种罪过
看她抹眼泪的样子十分搞笑
带高帽子的样子后来同样出现在了《罗马》一片中
费里尼对宗教的态度比一般的意大利人来得豁达
天主教常和他过不去
这个惩罚的场面费里尼强烈地讽刺了天主教
年轻的教士像个法西斯式的虐待狂
罪恶感在古依多心中成形
造成了他的心理阴影
忏悔室彷佛地狱制造出恐怖气氛
古依多离开忏悔室时
他来到圣母像前
注意看她的脸与他通过酒廊时看到的时髦女人的脸一样
这个场面揭示了古依多对女性的两种态度
一类视为圣女,一类视为妓女
对他敬爱的女人,比如妻子,性会变得肮脏
对放荡的女人,象卡拉,他可以随意堕落
由于古依多无法视女性为完整的个体
即既是自由的主体
又是男性欲望投射的客体
因此,古依多才在满怀罪恶感中
寻找完美的圣女他心中的偶像
但事实上这个偶像并不存在
在现在我们回看刚才为什么费里尼要把莎拉吉娜的片段
直接接在与主教会面之后
其实是因为主教象征了制造古依多性欲原罪的天主教机制
费里尼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表现出
一个矛盾、交织在不同现实下的人
影片要描述这个人的一切可能性
象一栋大楼
观众走进去能见到楼梯走廊以及家具和别的
甚至最隐秘的角落
他要描写出由无数折磨人的不断改变的迷宫组成的人生
日常生活就是交织着记忆、情感、幻想、过去和现在重叠的迷宫
在迷宫中乡愁和预感混合
有时人们会迷失自己
不清楚自己是谁
他的过去是怎样的
他又要往何处去
人生至此象是一段没有感情悠长但却不入眠的酣睡
费里尼对于心理分析学说的认知,
来自于他的一个德国心理医师朋友伯尔尼汉
他把心理分析思想带给了费里尼
心理分析学说给费里尼一个启示
没有办法对任何事都有普遍的看法
无法把个人喜好和品味归类
分成自己是那个类型
了解了自我之后
费里尼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而他此后的作品也开始越来越关注人的内心世界
他认为人生的许多探险中最值得去经历的
是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
但却会激起一些英雄色彩
9、
这里古依多将和妻子偶遇
我们可以再次欣赏到摄影机的流畅运动
这同样是一个横移镜头
镜头隐藏在人群中
和主角走在人群里的视点相一致
古依多的妻子露易莎出现了
注意她的打扮
镜头跟至此,反打至古依多的脸
证明刚才这个镜头来自古依多的主观视点
扮演露易莎的是法国女星阿努克•艾美
她曾主演过许多名片:《甜蜜的生活》、《男欢女爱》
她在本片中的演出十分精彩
她的打扮呈中性,戴着眼镜显得老气
眼镜在后面的情节中有很强烈的暗示作用
现在她摘下了眼镜
你发现她其实很漂亮
这个露易莎的女友在影片中担任着重要角色
她似乎一直在对古依多的个人困惑提出质疑
10、
这里是影片的重要场景飞船发射场
在剧情中古依多拍摄的是部科幻片
所以制片人搭建了巨大的场景
在这部电影放映后
有评论认为这个巨大的发射场象征
讽刺了拍不成的电影和徒劳的努力
11、
这场戏导致了重大冲突
因为古依多对妻子的冷感
露易莎虽然换了睡衣但眼镜还是戴着
注意看古依多睡觉的近景
又一次出现镜子
以上的这些视点其实都是来自假睡的古依多
现在的反打镜头说明的这一点
注意露易莎睡觉的镜头
推得很近
造成了一种错觉
露易莎睡在和古依多同一张床上
现在是古依多的反应镜头
同样是近景
再接露易莎的近景
强化这种假象
费里尼接到两人争吵的远景
才揭示出古依多和露易莎是分开睡的
12、
现在的这一段是本片最激动人心的段落
看这些椅子,《黑超特警组》的美工从这里得到了创意
情妇卡拉出现了
古依多这个喜剧式的动作
暗示了整个段落的表演
都将是喜剧式的
古依多此时的情绪已经到了崩渍的边缘
他无法在面对自己的生活本身
他戴上墨镜拒絶面对生活
镜头一转,生活变成了幻想
幻想总是美好的
妻子夸耀着情妇
和谐地互不干涉
古依多成为了幻想中的胜利者
翩翩起舞的音乐
带出了幻想中妻妾成群的片段
场景回到了童年幻想中的农舍,注意他的妻子露易莎
拿着洗澡水出现
古依多彷佛农舍主人回家
露易莎回头望着观众
提醒我们是在观看电影
导演成了电影的主角
朋友的女友巴巴拉•斯蒂尔、倩妇卡拉
以及其他古依多生命中出现过的女性,都聚齐了
不知道自己角色法国女演员、大堂里的时髦女人
都一一出现
这个场面可能是所有男性一生中
至少幻想过一次的场景
时髦女人是费里尼童年的偶像
在这里出现安慰古依多
其实是在安慰费里尼自己
注意楼上的露易莎女友
她仍然在嘲笑古依多
妻子和情妇和睦相处
均匀地占据了银幕两侧
这个女孩子就是童年梦中坐着吃葡萄的小女孩
成年的古依多在浴盆里做出了她曾做的”阿尼马”动作
注意古依多此刻虽然在洗澡
但仍戴着帽子
帽子象征了他导演的身份
奶妈又出现了
再度带来温暖的记忆
注意妻子在这里扮演的一直是主妇的形象
也很象母亲的形象
童年时代的性启蒙者莎拉吉娜也出现了
她出现在卡拉的前面
暗示了卡拉不过是她在他成年后的一个替代品
古依多对舞女的冷淡
也是费里尼自我的写照
许多人评论说费里尼喜新厌旧
莎拉吉娜突然出现
她是首位反抗的女人
反抗古依多的光说不练
这很象陷入创作危机的古依多的恶梦
瓦格纳的音乐再度响起
女人们开始暴动
古依多如驯兽师般的追打女人
他和莎拉吉娜展开搏斗
这段有些施虐式的场面象是古依多要征服那些困扰他的问题
在这里,所有的问题都简化成了男性对女性
最简单最原始的征服
他的鞭子代表了秩序
妻子在一旁给他说好话
带着赞许的目光
音乐和画面结合的如此好
堪称完美之作
掌声献给了古依多
秩序被恢复
古依多的男性尊严也随之被恢复
注意古依多又在照镜子
此时他脱下的帽子
因为他已经获得了秩序
不需要再确认导演身份了
妻妾成群的这个段落
是电影史上的经典段落
它所激起的不是普通的观众期待中的性欲天堂
反而在这场戏里面性给减低到了最低限度
在这里女人们给他洗澡
然后用毯子包着他
迎合他每个童年的欲望
这些欲望和性无关
所以这个妻妾成群的场面
包含了男性心理的各个层面
十分精彩
13、
露易莎摘掉眼镜,这是很重要的暗示
眼镜是露易莎出现时的标志
现在出现在了电影中
她脱下了眼镜暗示她希望能从妻子的身份中逃离出来
古依多失去了妻子
他还是选择了电影
但他已心神不宁
他无法面对自己拍的这一切
但却走头无路
14、
在让演员试镜这场戏上
放映的片段和生活相互映照
银幕上放映时的开机声
是拍摄时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拍摄马上要开始的提醒声
费里尼把这个音效收在这段戏里
其实也在提醒观众
片中的演员在看银幕
我们在看片中的演员
15、
影片开始进入最引人争议的结尾部分了
古依多象是给绑架到了新闻发布会一样
急促的音乐声中媒体象逼供一样对导演提问
制片人希望导演能说话
但导演一点也说不出来
古依多产生了幻觉还是真的举枪自尽
一直是多年来评论界争议的话题
这涉及到了影片一个重要命题
导演拍这部电影的目的
究竟是对这种崩渍状态的描绘
还是要在混乱中找出新秩序
一种说法是这后面的段落是费里尼在帮助古依多思考
作为一个导演
需要怎样的态度
面对生活和艺术上的问题
因此才有后面的大团圆
持这一观点的
就有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他拍摄的《地下》在片尾有一段
所有人的大团圆庆典
创意直接来自本片的结尾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古依多的自杀是一种幻想
这一段是真实的
大家都离开了
电影也不拍了
这个场景正在被拆除
他被迫接受编剧的劝告
他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魔术师出现了
这时古依多除了幻想就没有别的了
在幻想中克劳迪娅再现
童年的梦境再现
又一次地幻想取代了现实
所有人都换上了纯洁的白衣
象征着古依多找到了新秩序
克劳迪娅走向左面
而生命中真实的人们走向右面
结果他们没有碰面
这暗示了古依多开始在幻想中找到真正对他有意义的
那些生活在他周围的人
电影的灯光亮了起来
一切又彷佛在电影中
马戏团乐队开始进入
这是典型的费里尼式的幻想
乐队成员中年轻的吹笛者代表了年少的古依多
重新获得艺术的能力
古依多拿着导演的话筒
他戴上了帽子
帽子是导演的象征
他回来了
古依多让年少的古依多站在幕布
彷佛是电影开场一样
迎接着所有角色
从飞船发射塔上走来
教士,制片人,他的助手等所有人
古依多生命中的这些人
再次走到地面和古依多相处
古依多加入到了大家之中
从自我幻想的导演到走近生活
古依多走出了一大步
古依多的故事肯定带给了你很多的启示
这也是观看《八又二分之一》最大的乐趣所在
 RSS
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