зҺӢжҫҚ-йҰ–дҪҚиҺ·еҫ—жҷ®еҲ©е…№е…ӢеҘ–дёӯеӣҪе»әзӯ‘еёҲ
вҖңдёҖдёӘең°ж–№зҡ„е»әзӯ‘еҰӮжһңжҳҜеәёдҝ—зҡ„пјҢеңЁйӮЈйҮҢз”ҹжҙ»зқҖзҡ„дәәд№ҹдёҖе®ҡжҳҜеәёдҝ—зҡ„гҖӮвҖқвҖ”вҖ”зҺӢжҫҚ

2012е№ҙ5жңҲ25ж—ҘпјҢжҷ®еҲ©е…№е…Ӣе»әзӯ‘еҘ–пјҲ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пјүйўҒеҘ–е…ёзӨјеңЁеҢ—дә¬дәәж°‘еӨ§дјҡе ӮдёҫиЎҢгҖӮиҝҷжҳҜиҝҷдёҖжңүе»әзӯ‘з•ҢвҖңиҜәиҙқе°”еҘ–вҖқд№Ӣз§°гҖҒе…Ёдё–з•Ңе…¬и®Өзҡ„д»ЈиЎЁе»әзӯ‘иЎҢдёҡжңҖй«ҳиҚЈиӘүзҡ„еҘ–йЎ№иҮӘ1979е№ҙеҲӣз«Ӣд»ҘжқҘйҰ–ж¬ЎеңЁдёӯеӣҪдёҫеҠһйўҒеҘ–е…ёзӨјпјҢзҺӢжҫҚжҳҜйҰ–дҪҚиҺ·еҫ—жҷ®еҲ©е…№е…Ӣе»әзӯ‘еҘ–зҡ„дёӯеӣҪе»әзӯ‘еёҲгҖӮ
жҷ®еҲ©е…№е…Ӣе»әзӯ‘еҘ–иў«и§Ҷдёәе»әзӯ‘дё“дёҡзҡ„жңҖй«ҳиҚЈиӘүгҖӮ1979е№ҙз”ұзҫҺеӣҪиҠқеҠ е“Ҙжҷ®еҲ©е…№е…Ӣ家ж—ҸйҖҡиҝҮж——дёӢеҮҜжӮҰеҹәйҮ‘дјҡеҲӣз«ӢпјҢз”ұжҷ®еҲ©е…№е…Ӣ家ж—Ҹзҡ„жқ°дјҠВ·жҷ®еҲ©е…№е…ӢпјҲA. Pritzkerпјүе’Ңд»–зҡ„еҰ»еӯҗиҫӣи’ӮпјҲCindyпјүеҸ‘иө·пјҢеҮҜжӮҰеҹәйҮ‘дјҡпјҲHyatt FoundationпјүжүҖиөһеҠ©зҡ„й’ҲеҜ№е»әзӯ‘еёҲдёӘдәәйўҒеёғзҡ„еҘ–йЎ№гҖӮз”ұдё“дёҡиҜ„审委е‘ҳдјҡжҜҸе№ҙиҜ„йҖүеҮәдёҖеҗҚдҪңеҮәжқ°еҮәиҙЎзҢ®зҡ„еңЁдё–е»әзӯ‘еёҲгҖӮиҺ·еҘ–иҖ…еҸҜд»ҘиҺ·еҫ—10дёҮзҫҺе…ғеҘ–йҮ‘е’ҢиҺ·еҘ–иҜҒд№ҰпјҢ1987е№ҙеҗҺ委е‘ҳдјҡиҝҳдёәиҺ·еҘ–иҖ…йўҒеҸ‘дёҖжһҡй“ңиҙЁеҘ–з« гҖӮйўҒеҘ–е…ёзӨјеңЁжҜҸе№ҙ5жңҲдёҫиЎҢпјҢең°зӮ№еҲҷеңЁдё–з•Ңеҗ„ең°зҡ„и‘—еҗҚе»әзӯ‘зү©еҶ…гҖӮ
зҺӢжҫҚиҺ·еҫ—жҷ®еҲ©е…№е…ӢеҘ–зҡ„еҺҹеӣ пјҡеҮҜжӮҰеҹәйҮ‘дјҡдё»еёӯжҷ®йҮҢе…№е…ӢпјҲThomas J. Pritzkeпјүд»Ӣз»ҚпјҢйҖүдёӯ48еІҒзҡ„зҺӢжҫҚжҳҜеӣ дёәжүҝи®ӨдёӯеӣҪе°ҶеңЁеҸ‘еұ•е»әзӯ‘зҗҶеҝөдёӯзҡ„дҪңз”ЁгҖӮжҷ®йҮҢе…№е…ӢжҢҮеҮәпјҢжңүе…ізҺ°еңЁе’ҢиҝҮеҺ»зҡ„йҖӮеҪ“е…ізі»й—®йўҳпјҢзҺӢжҫҚжҸҗеҮәзҡ„йқһеёёеҸҠж—¶пјҢеӣ дёәдёӯеӣҪжңҖиҝ‘зҡ„еҹҺеёӮеҢ–иҝҮзЁӢеј•иө·дәүи®®пјҡе»әзӯ‘жҳҜеә”еҪ“д»Ҙдј з»ҹдёәеҹәзЎҖиҝҳжҳҜеә”еҪ“еұ•жңӣжңӘжқҘгҖӮе°ұеғҸд»»дҪ•дјҹеӨ§зҡ„е»әзӯ‘дёҖж ·пјҢзҺӢжҫҚзҡ„и®ҫи®Ўи¶…и¶ҠдәҶйӮЈеңәдәүи®әпјҢдә§з”ҹжІЎжңүж—¶й—ҙйҷҗеҲ¶гҖҒж·ұж·ұжӨҚж №дәҺиҮӘиә«зҺҜеўғеҸҲе…·жңүжҷ®йҒҚжҖ§зҡ„е»әзӯ‘гҖӮ
зҺӢжҫҚпјҢдҪңдёәжҙ»и·ғеңЁдёӯеӣҪе»әзӯ‘第дёҖзәҝзҡ„е»әзӯ‘еӨ§еёҲпјҢд»–зҡ„дҪңе“ҒжҖ»жҳҜиғҪеӨҹеёҰз»ҷдё–дәәиҖізӣ®дёҖж–°зҡ„ж„ҹи§ү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еҜ№йӮЈдәӣе»әзӯ‘еҸёз©әи§ҒжғҜзҡ„дәәиҖҢиЁҖгҖӮеҮӯзқҖеҜ№йЎ№зӣ®еңәең°зҡ„зӢ¬зү№и§Ғи§ЈпјҢеҜ№дёӯеӣҪдј з»ҹж–ҮеҢ–еңЁе»әзӯ‘дёӯзҡ„й«ҳи¶…иЎЁиҫҫпјҢд»ҘеҸҠеҜ№дёҚеҗҢе»әзӯ‘жқҗж–ҷз»„еҗҲзҡ„е·§еҰҷжҠҠжҸЎпјҢдҪҝеҫ—зҺӢжҫҚзҡ„дҪңе“ҒжңүзқҖдёҖз§ҚзӢ¬зү№зҡ„иұЎеҫҒжҖ§е’Ң延з»ӯжҖ§гҖӮиҝҷз§Қзү№ж®Ҡзҡ„еұһжҖ§д»ҺдҪ•иҖҢжқҘпјҡеј•з”ЁзҺӢжҫҚжң¬дәәзҡ„иҜқжқҘи®ІпјҡвҖңеңЁеҪ“еӨ§е®¶жӢје‘Ҫиөҡй’ұзҡ„ж—¶еҖҷпјҢжҲ‘еҚҙиҠұдәҶе…ӯдёғе№ҙзҡ„ж—¶й—ҙжқҘеҸҚзңҒгҖӮвҖқд№ҹи®ёжӯЈжҳҜиҝҷе…ӯдёғе№ҙж—¶й—ҙзҡ„еҸҚзңҒпјҢдҪҝеҫ—зҺӢжҫҚиғҪеӨҹеңЁжө®иәҒзҡ„зӨҫдјҡе’Ңе–§еҡЈзҡ„зҺҜеўғдёӯйқҷдёӢеҝғжқҘпјҢз»Ҷз»ҶдҪ“йӘҢдёӯеӣҪдј з»ҹж–ҮеҢ–зҡ„зІҫй«“е’Ңйӯ…еҠӣпјҢ并еҸ‘жҺҳе…¶дёҺе»әзӯ‘еҶ…еңЁзҡ„еҫ®еҰҷе…ізі»гҖӮиҝҷдҪҝеҫ—зҺӢжҫҚзҡ„дёҖдәӣдҪңе“Ғдёӯе…·жңүе’ҢеӣҪз”»дёӯзӣёеҗҢзҡ„дёҖдәӣжҖ§иҙЁпјҢдҫӢеҰӮпјҡеҸҷдәӢжҖ§гҖӮе°ұеғҸзҺӢжҫҚеңЁиЎЁиҫҫд»–еҜ№2010е№ҙдёҠжө·дё–еҚҡдјҡе®Ғжіўж»•еӨҙжЎҲдҫӢйҰҶзҡ„и®ҫи®Ўж—¶пјҢд»–жҸҗеҲ°йҖҡиҝҮдёӯеӣҪеҸӨдәәеңЁиҮӘ然зҺҜеўғдёӯйҡҸзқҖж—¶й—ҙжҺЁз§»иҖҢиЎЁзҺ°зҡ„дёҚеҗҢжҙ»еҠЁж–№ејҸжқҘиЎЁиҫҫе»әзӯ‘и®ҫи®ЎдёӯвҖңдәәжң¬вҖқзҡ„и®ҫи®ЎжҰӮеҝөпјҢд»ҘеҸҠеҮёжҳҫе…¶дёӯдәәдёҺзҺҜеўғпјҢе»әзӯ‘дёҺзҺҜеўғзӣёиҫ…зӣёжҲҗзҡ„е…ізі»пјҢиҝҷдёҖзӮ№д№ҹдёҺжҳҺжң«жё…еҲқзҡ„и‘—еҗҚ画家йҷҲжҙӘ绶еңЁд»–зҡ„еҗҚз”»гҖҠдә”жі„еұұеӣҫгҖӢжүҖиЎЁиҫҫзҡ„ж„ҸеўғжңүзқҖејӮжӣІеҗҢе·Ҙд№ӢеӨ„пјҢеҮӯзқҖеҜ№йҷҲжҙӘ绶дҪңе“Ғзҡ„зӢ¬еҲ°зҗҶи§ЈпјҢзҺӢжҫҚеңЁи®ҫи®ЎдёӯйҮҮз”ЁдәҶзү№ж®Ҡзҡ„вҖңеҲҮзүҮејҸвҖқзҡ„и®ҫи®Ўж–№жі•пјҢеҸҠйҖҡиҝҮеӨҡдёӘз©әй—ҙеҲҮйқўжқҘеҸҚжҳ еңЁдёҚеҗҢз©әй—ҙзҠ¶жҖҒдёӢе»әзӯ‘еҪўжҖҒе’Ңдәәжҙ»еҠЁж–№ејҸзҡ„еҸҳеҢ–гҖӮзҺӢжҫҚжҳҜзқҝжҷәзҡ„пјҢеӣ дёәд»–еңЁжө®еҚҺзҡ„дё–йЈҺдёӢиғҪдҝқжҢҒе№іе’Ңзҡ„еҝғжҖҒеҺ»еҸ‘зҺ°е»әзӯ‘зҡ„жң¬иҙЁпјӣзҺӢжҫҚжҳҜзқҝжҷәзҡ„пјҢеӣ дёәд»–еңЁиҮӘе·ұзҡ„дҪңе“Ғи®ҫи®ЎжҳҜиғҪеӨҹдҪ“зҺ°еҮәиҮӘе·ұзӢ¬еҲ°зҡ„и§Ҷи§’е’ҢеҜ№дёӯеӣҪж–ҮеҢ–зҡ„й«ҳж·ұи§Ғи§ЈпјҢ并иҙҜз©ҝе§Ӣз»ҲгҖӮ

зҺӢжҫҚз®Җд»Ӣпјҡ
зҺӢжҫҚпјҲwГЎng shГ№пјүзҘ–зұҚеұұиҘҝзңҒеҗ•жўҒеёӮдәӨеҸЈеҺҝйҮҺ家еқЎжқ‘пјҢ1963е№ҙ11жңҲ4ж—Ҙз”ҹдәҺж–°з–ҶпјҢдёӯе°ҸеӯҰеқҮжҜ•дёҡдәҺй“ҒдёҖеұҖиҘҝе®үеӯҗејҹеӯҰж ЎгҖӮд»–дәҺ1985е№ҙжҜ•дёҡдәҺеҚ—дә¬е·ҘеӯҰйҷўпјҲд»ҠдёңеҚ—еӨ§еӯҰпјүе»әзӯ‘зі»пјҢ1988е№ҙиҺ·еҫ—дёңеҚ—еӨ§еӯҰе»әзӯ‘еӯҰзЎ•еЈ«пјҢ2000е№ҙиҺ·еҗҢжөҺеӨ§еӯҰе»әзӯ‘еӯҰеҚҡеЈ«пјҢзҺ°д»»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е»әзӯ‘иүәжңҜеӯҰйҷўйҷўй•ҝгҖҒеҚҡеЈ«з”ҹеҜјеёҲгҖӮзҺӢжҫҚе–ңж¬ўйҳ…иҜ»гҖҒз®«з®ЎпјҢж“…й•ҝд№Ұжі•е’Ңеұұж°ҙз”»пјҢжү§зқҖи·өиЎҢдёӯеӣҪжң¬еңҹе»әзӯ‘еӯҰзҗҶеҝөпјҢдә«жңүвҖңдёӯеӣҪжңҖе…·ж–Үдәәж°”иҙЁзҡ„е»әзӯ‘家вҖқзҫҺиӘүгҖӮд»ЈиЎЁдҪңе“Ғжңүдё–еҚҡдјҡе®Ғжіўж»•еӨҙжЎҲдҫӢйҰҶгҖҒиӢҸе·һеӨ§еӯҰж–ҮжӯЈеӯҰйҷўеӣҫд№ҰйҰҶе’Ң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иұЎеұұж ЎеӣӯзӯүгҖӮ
1963е№ҙ11жңҲ4ж—Ҙз”ҹдәҺж–°з–ҶгҖӮзҘ–зұҚеұұиҘҝзңҒеҗ•жўҒеёӮдәӨеҸЈеҺҝйҮҺ家еқЎжқ‘дәәж°ҸгҖӮжҲҗй•ҝдәҺж–°з–ҶгҖҒеҢ—дә¬гҖҒиҘҝе®үгҖӮ
1981е№ҙжҜ•дёҡдәҺдёӯй“ҒдёҖеұҖиҘҝе®үдёӯеӯҰгҖӮ1981е№ҙеҗҺжёёеӯҰжұҹеҚ—гҖӮ
1985 жҜ•дёҡдәҺеҚ—дә¬е·ҘеӯҰйҷўпјҲзҺ°дёңеҚ—еӨ§еӯҰпјүе»әзӯ‘зі» еӯҰеЈ«гҖӮ
1988 жҜ•дёҡдәҺдёңеҚ—еӨ§еӯҰе»әзӯ‘з ”з©¶жүҖ зЎ•еЈ«з ”з©¶з”ҹгҖӮ
1988иҮі1995 еңЁжөҷжұҹ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пјҲзҺ°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пјүе·ҘдҪңгҖӮ
1990е№ҙе»әйҖ зҡ„жө·е®Ғйқ’е°‘е№ҙе®«жҳҜзҺӢжҫҚзҡ„еӨ„еҘідҪң
2000 жҜ•дёҡдәҺеҗҢжөҺеӨ§еӯҰе»әзӯ‘еҹҺ规еӯҰйҷў
е»әзӯ‘и®ҫи®ЎдёҺзҗҶи®әдё“дёҡеҹҺеёӮи®ҫи®Ўж–№еҗ‘еҚҡеЈ«гҖӮ
зҺ°еңЁ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зҺҜеўғиүәжңҜзі»д»»ж•ҷпјҢжүҺж №жқӯе·һж·ұеәҰиҖ•иҖҳгҖӮ
2010е№ҙиҺ·еЁҒе°јж–ҜеҸҢе№ҙеұ•е»әзӯ‘еӨ§еҘ–гҖӮ
2011е№ҙиҺ·жі•еӣҪ科еӯҰйҷўе»әзӯ‘еӯҰйҷўйҮ‘еҘ–гҖӮ
2012е№ҙиҺ·еҫ—жҷ®еҲ©е…№е…Ӣе»әзӯ‘еҘ–пјҢд»–жҳҜйҰ–дҪҚиҺ·жӯӨж®ҠиҚЈзҡ„дёӯеӣҪдәәгҖӮ
жҷ®еҲ©е…№е…ӢеҘ–е…ёзӨј зҺӢжҫҚиҺ·еҘ–ж„ҹиЁҖпјҡ
иҺ·еҫ—иҝҷдёӘеҘ–пјҢеҜ№жҲ‘еӨҡе°‘жҳҜжңүдәӣдёҚжңҹиҖҢиҮізҡ„ж„ҹи§үгҖӮеңЁеӨҡе№ҙеӯӨзӢ¬зҡ„еқҡжҢҒд№ӢеҗҺпјҢеҜ№дёҖдёӘеңЁиҺ·еҘ–д№ӢеүҚжІЎжңүеҮәзүҲиҝҮдҪңе“ҒйӣҶзҡ„е»әзӯ‘еёҲпјҢдёҖдёӘеҸӘеңЁдёӯеӣҪеҒҡе»әзӯ‘зҡ„е»әзӯ‘еёҲпјҢдёҖдҪҚиҮӘз§°дёәдёҡдҪҷзҡ„е»әзӯ‘еёҲжқҘиҜҙпјҢиҝҷз»қеҜ№жҳҜдёҖдёӘе·ЁеӨ§зҡ„жғҠе–ңпјҢдёәжӯӨпјҢжҲ‘иҰҒж„ҹи°ўиҜ„委дјҡзқҝжҷәе’Ңе…¬жӯЈзҡ„иҜ„д»·гҖӮ
иҖҢдҪңдёә第дёҖдёӘиҺ·еҫ—иҝҷдёӘеҘ–йЎ№зҡ„дёӯеӣҪжң¬еңҹе»әзӯ‘еёҲпјҢжҲ‘еңЁж·ұж„ҹиҚЈиҖҖзҡ„еҗҢж—¶пјҢд№ҹжңүеҮ еҲҶжғ¶жҒҗгҖӮиҰҒзҹҘйҒ“пјҢеҜ№иҝҷдёӘжңүзқҖдјҹеӨ§е»әзӯ‘дј з»ҹзҡ„еӣҪ家пјҢиҝҷдёӘеҮ еҚғе№ҙжқҘжІЎжңүдё“дёҡе»әзӯ‘еёҲеҲ¶еәҰзҡ„еӣҪ家пјҢзҺ°д»Је»әзӯ‘еёҲиҝҷдёӘи§’иүІпјҢд»ҺжҲ‘зҡ„иҖҒеёҲзҡ„иҖҒеёҲз®—иө·пјҢеҲ°жҲ‘д№ҹеҸӘжңүдёүд»ЈиҖҢе·ІгҖӮиҝҷдёӘеҘ–еҜ№дёӯеӣҪе»әзӯ‘з•Ңзҡ„ж„Ҹд№үеҰӮжӯӨйҮҚеӨ§пјҢ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иҝҳеҰӮжӯӨе№ҙиҪ»зҡ„е»әзӯ‘еёҲпјҢжҲ‘еҝ…йЎ»иҜҙпјҢиҰҒж„ҹи°ўиҝҷдёӘйқһжҜ”еҜ»еёёзҡ„ж—¶д»ЈпјҢжӯЈжҳҜиҝҷдёӘж—¶д»Јзҡ„дёӯеӣҪе·ЁеӨ§зҡ„еҸ‘еұ•е’ҢеҸІж— еүҚдҫӢзҡ„ејҖж”ҫпјҢжүҚеҸҜиғҪи®©жҲ‘иҝҷж ·дёҖдёӘе»әзӯ‘еёҲпјҢеңЁеҰӮжӯӨзҹӯзҡ„ж—¶й—ҙйҮҢжңүиҝҷд№ҲеӨҡзҡ„жңәдјҡеҺ»иҝӣиЎҢиү°йҡҫзҡ„е»әзӯ‘е®һйӘҢгҖӮеңЁжӯӨжҲ‘иҰҒж„ҹи°ўжҲ‘зҡ„дјҷдјҙйҷҶж–Үе®ҮпјҢд№ҹиҰҒж„ҹи°ўжүҖжңүжӣҫз»Ҹеё®еҠ©иҝҮжҲ‘зҡ„дәә们пјҢе…¶дёӯдёҖдәӣдәәд»ҠеӨ©е°ұеңЁиҝҷйҮҢгҖӮ
д№ҹи®ёжҳҜеӣ дёәиҝҷдёӘеӣҪ家зҡ„дё“дёҡе»әзӯ‘еёҲеҲ¶еәҰзҡ„е№ҙиҪ»пјҢд№ҹи®ёжҳҜеӣ дёәз»ҸеҺҶдәҶеӨӘеӨҡзҡ„ж—¶д»ЈеҸҳйқ©пјҢжҲ‘и®°еҫ—пјҢиҝҳеңЁ30е№ҙеүҚпјҢжҲ‘еңЁеҚ—дә¬е·ҘеӯҰйҷўе»әзӯ‘зі»еӯҰд№ зҡ„ж—¶еҖҷпјҢвҖңд»Җд№ҲжҳҜе»әзӯ‘пјҹвҖқпјҢе°ұжҳҜиў«з»ҸеёёжҸҗеҮәзҡ„й—®йўҳгҖӮжҲ‘жңҖе°Ҡ敬зҡ„ж•ҷжҺҲпјҢз«ҘеҜҜе…Ҳз”ҹпјҢдёӯеӣҪиҝ‘代第дёҖд»Је»әзӯ‘еёҲпјҢ第дёҖдёӘз ”з©¶дј з»ҹеӣӯжһ—зҡ„е»әзӯ‘еёҲпјҢжӣҫз»ҸжңүеӯҰз”ҹеҫҲиҷ”иҜҡзҡ„й—®д»–иҝҷдёӘй—®йўҳпјҢд»–еҸӘжҳҜиҪ»иҪ»зҡ„еӣһзӯ”пјҡвҖңе»әзӯ‘пјҢдёҚе°ұжҳҜйӮЈд№ҲзӮ№дәӢжғ…еҳӣвҖқгҖӮ
дҪҶе°ұжҳҜиҝҷд№ҲзӮ№дәӢжғ…пјҢеңЁиҝҮеҺ»30е№ҙпјҢж·ұеҲ»зҡ„ж”№еҸҳдәҶдёӯеӣҪзҡ„йқўиІҢе’Ңдәә们зҡ„з”ҹжҙ»гҖӮе®һйӘҢе’Ңеӣ°жғ‘жҳҜеҗҢж—¶еҸ‘з”ҹзҡ„гҖӮеғҸжҲ‘иҝҷж ·дёҖдёӘиҜ»дәҶеӨӘеӨҡе“ІеӯҰзҡ„е»әзӯ‘еӯҰеӯҗпјҢе…ҲжҳҜе……ж»ЎжҝҖжғ…зҡ„жӢҘжҠұзҺ°д»Је»әзӯ‘пјҢеҫҲеҝ«е°ұйҒҮеҲ°еҗҺзҺ°д»Је»әзӯ‘пјҢеңЁеҺҢеҖҰдәҶиҝҷз§Қзҹ«жғ…зҡ„йЈҺжҪ®д№ӢеҗҺпјҢеҸҲдёәи§Јжһ„е“ІеӯҰе’Ңе»әзӯ‘иҖҢе…ҙеҘӢпјҢз”ҡиҮіи®ҫи®Ўе’Ңе»әйҖ дәҶеҮ дёӘпјҢдҪҶеӣ°жғ‘дёҖзӣҙдјҙйҡҸзқҖжҲ‘пјҢе°ұе»әзӯ‘дёҺж–ҮеҢ–зҡ„дәӨеҸүи®Ёи®әиҖҢиЁҖпјҢиҝҷжҳҜж №жәҗдәҺиҮӘжҲ‘ж–ҮеҢ–зҡ„е»әзӯ‘еҗ—пјҹиҝҷе°ұжҳҜдёәд»Җд№ҲжҲ‘еңЁ90е№ҙд»ЈйҖүжӢ©дәҶйҖҖйҡҗпјҢжҲ‘йҖүжӢ©йҖҖеҮәдё“дёҡе»әзӯ‘еёҲеҲ¶еәҰпјҢжҲ‘йҖүжӢ©ж—§е»әзӯ‘ж”№йҖ пјҢж•ҙж—Ҙе’Ңең°ж–№е·ҘеҢ дёҖиө·е·ҘдҪңгҖӮжҲ‘ж„ҸиҜҶеҲ°пјҢе’Ңд»Ҙиҷҡжһ„дёәеҹәи°ғзҡ„зҺ°д»Је»әзӯ‘зӣёжҜ”пјҢжңүеҸҰдёҖз§ҚжҖ»жҳҜжүҝи®ӨжҹҗдәӣдёңиҘҝе·Із»ҸеӯҳеңЁеңЁйӮЈйҮҢзҡ„е»әзӯ‘пјӣе’Ңејәи°ғжҠҪиұЎз©әй—ҙзҡ„зҺ°д»Је»әзӯ‘зӣёжҜ”пјҢиҝҷз§Қе»әзӯ‘жҖ»жҳҜжҢҮеҗ‘е…·дҪ“зҡ„жҹҗең°пјҢеҢ…еҗ«зқҖжӣҙеӨҡж—¶й—ҙе’ҢеӣһеҝҶзҡ„ж„Ҹе‘іпјӣе’Ңе®Ңе…Ёдәәе·Ҙзҡ„е»әйҖ зӣёжҜ”пјҢжӣҙејәи°ғиҮӘ然жҖ§зҡ„дёӯеӣҪе»әзӯ‘дј з»ҹж„Ҹе‘ізқҖеҸҰдёҖз§Қе»әзӯ‘еӯҰпјҢдёҖз§ҚжҲ‘д»ҺжқҘжІЎжңүеӯҰиҝҮпјҢдҪҶеҸҜиғҪеҢ…еҗ«зқҖжҜ”зҺ°д»Је»әзӯ‘жӣҙеҠ дјҳи¶Ҡзҡ„д»·еҖјзҡ„е»әзӯ‘еӯҰгҖӮеҰӮжһңзҺ°д»Је»әзӯ‘е°ұжҢҮдё“дёҡе»әзӯ‘еёҲеҲ¶еәҰпјҢжҲ‘е®ҒеҸҜз§°иҮӘе·ұжҳҜдёҡдҪҷзҡ„гҖӮ
иҝ„д»ҠдёәжӯўпјҢжҲ‘зҡ„е»әзӯ‘и®ҫи®Ўжҙ»еҠЁйғҪеҸ‘з”ҹеңЁдёӯеӣҪпјҢдҪҶжүҖж¶үеҸҠзҡ„й—®йўҳеҚҙдёҚд»…йҷҗдәҺдёӯеӣҪгҖӮеңЁиҝҮеҺ»еҮ еҚҒе№ҙзҡ„е·ЁеҸҳдёӯпјҢдёӯеӣҪе’Ңе»әзӯ‘еӯҰжңүе…ізҡ„и®ёеӨҡй—®йўҳйғҪжӣҫз»ҸеңЁдё–з•Ңе…¶д»–ең°ж–№еҸ‘з”ҹиҝҮпјҢдҪҶдёӯеӣҪеҸ‘з”ҹзҡ„дәӢжғ…其规模жӣҙеӨ§пјҢеҠҝжҖҒжӣҙеҠ зҢӣзғҲпјҢйҖҹеәҰжӣҙеҝ«гҖӮеңЁиҝҷдёӘ100е№ҙеүҚиҝҳеҸӘжңүе·ҘеҢ жІЎжңүе»әзӯ‘еёҲзҡ„еӣҪ家пјҢеҸ‘з”ҹзқҖж·ұеҲ»зҡ„ж–ҮжҳҺеҶІзӘҒгҖӮиҝҷе°ұиҰҒжұӮе»әзӯ‘еёҲдёҚд»…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ҠҖжңҜжү§дёҡиҖ…пјҢиҖҢжҳҜиҰҒжңүжӣҙеҠ е®Ҫе№ҝзҡ„и§ҶйҮҺпјҢжӣҙж·ұжҖқзҶҹиҷ‘зҡ„жҖқиҖғпјҢжӣҙжё…жҘҡзҡ„д»·еҖји§Ӯе’ҢдҝЎеҝөгҖӮжҲ‘зҡ„жүҖжңүе»әзӯ‘и®ҫи®ЎйғҪе’Ңиҝҷз§ҚжҖқиҖғжңүе…і: дёҖз§Қд»Ҙе·ҘеҢ жҠҖиүәдёәдё»дҪ“зҡ„е»әзӯ‘еӯҰеҰӮдҪ•еңЁд»ҠеӨ©з”ҹеӯҳпјҹйқўеҜ№и§„жЁЎе·ЁеӨ§зҡ„дәәе·ҘйҖ зү©пјҢдј з»ҹдёӯеӣҪзҡ„дјҹеӨ§жҷҜи§Ӯзі»з»ҹеңЁд»ҠеӨ©зҡ„ж„Ҹд№үдёәдҪ•пјҹеңЁи”“延еҹҺеёӮд№Ўжқ‘зҡ„зҺ°д»ЈйҖ еҹҺиҝҗеҠЁдёӯпјҢеҰӮжһңдёҚеӨ§жӢҶеӨ§е»әпјҢеҹҺеёӮе»әзӯ‘еә”иҜҘеҰӮдҪ•еҸ‘еұ•пјҹеҰӮжһңе·Із»Ҹиў«жӢҶдёәе№іең°пјҢж–°зҡ„еҹҺеёӮе»әзӯ‘еҰӮдҪ•еңЁеәҹеўҹдёӯжҺҘз»ӯз”ҹжҙ»и®°еҝҶпјҢйҮҚж–°е»әз«Ӣж–ҮеҢ–иә«д»Ҫи®ӨеҗҢпјҹеңЁдёӯеӣҪж·ұеҲ»зҡ„еҹҺд№ЎеҶІзӘҒдёӯпјҢе»әзӯ‘еӯҰд»Ҙд»Җд№Ҳж ·зҡ„еҠӘеҠӣеҸҜиғҪеҢ–и§Јиҝҷз§ҚеҶІзӘҒпјҹйқўеҜ№зҺ°д»Је»әзӯ‘еӯҰиҮӘдёҠиҖҢдёӢзҡ„дё“дёҡеҲ¶еәҰпјҢжҷ®йҖҡж°‘дј—иҮӘдёӢиҖҢдёҠзҡ„е»әйҖ жҙ»еҠЁжҳҜеҗҰеҸҜиғҪдҝқжңүе…¶жқғеҠӣе’Ңз©әй—ҙ? йқўеҜ№дёҘеі»зҡ„зҺҜеўғе’Ңз”ҹжҖҒй—®йўҳпјҢжҲ‘们жҳҜеҗҰеҸҜд»Ҙд»Һдј з»ҹе’Ңж°‘й—ҙе»әйҖ дёӯжүҫеҲ°жӣҙжңүжҷәж…§зҡ„ж–№ејҸпјҹд»Һиә«иҫ№зҡ„з”ҹжҙ»е’ҢдёӘдәәзҡ„зңҹе®һж„ҹеҸ—е…ҘжүӢпјҢеҰӮдҪ•жҺўи®ЁдёҖз§Қйқһе·Ёжһ„зҡ„гҖҒйқһиұЎеҫҒзҡ„гҖҒйқһж Үеҝ—жҖ§зҡ„е»әзӯ‘ж–ҮеҢ–иЎЁиҫҫж–№ејҸпјҹеҰӮдҪ•еңЁејәеӨ§зҡ„зҺ°д»ЈжҖ§еҲ¶еәҰдёӯпјҢеқҡжҢҒдёҖз§ҚзӢ¬з«Ӣе»әзӯ‘еёҲзҡ„е·ҘдҪңжҖҒеәҰе’Ңж–№ејҸпјҹ
жҲ‘з»ҸеёёиҜҙпјҢжҜҸж¬Ўи®ҫи®Ўе»әзӯ‘пјҢжҲ‘йғҪдёҚжӯўжҳҜи®ҫи®ЎдёҖдёӘе»әзӯ‘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и®ҫи®ЎдёҖдёӘдҝқжңүеӨҡж ·жҖ§е’Ңе·®ејӮжҖ§зҡ„дё–з•ҢпјҢиө°еҗ‘дёҖжқЎйҮҚиҝ”иҮӘ然зҡ„йҒ“и·ҜгҖӮиҝҷе°ұжҳҜеңЁжҲ‘еҫ—зҹҘиҺ·еҘ–зҡ„ж—¶еҲ»пјҢжҲ‘жӯЈеңЁжҖқзҙўзҡ„й—®йўҳпјҢд№ҹжҳҜжҲ‘дјёеҗ‘жңӘжқҘзҡ„зӣ®е…үгҖӮ

зҺӢжҫҚдҪңе“Ғпјҡе®ҒжіўеҺҶеҸІеҚҡзү©йҰҶ
еңәең°еңЁдёҖзүҮз”ұиҝңеұұеӣҙз»•зҡ„е№іеҺҹпјҢдёҚд№…еүҚиҝҳжҳҜзЁ»з”°пјҢеҹҺеёӮеҲҡеҲҡжү©еј еҲ°иҝҷйҮҢгҖӮеҺҹжқҘеңЁиҝҷзүҮеҢәеҹҹзҡ„еҮ еҚҒдёӘзҫҺдёҪжқ‘иҗҪпјҢе·Із»Ҹиў«жӢҶзҡ„иҝҳеү©ж®ӢзјәдёҚе…Ёзҡ„дёҖдёӘпјҢеҲ°еӨ„еҸҜи§Ғж®Ӣз –зўҺз“ҰгҖӮжҢүж–°зҡ„规еҲ’пјҢзӣёйӮ»е»әзӯ‘д№Ӣй—ҙзҡ„и·қзҰ»з»Ҹеёёи¶…иҝҮ100mпјҢеҹҺеёӮз»“жһ„е·Із»Ҹж— жі•дҝ®иЎҘгҖӮй—®йўҳиҪ¬еҢ–дёәеҰӮдҪ•и®ҫи®ЎдёҖдёӘжңүзӢ¬з«Ӣз”ҹе‘Ҫзҡ„зү©пјҢиҝҷеә§е»әзӯ‘дәҺжҳҜиў«дҪңдёәдёҖеә§дәәе·ҘеұұдҪ“жқҘи®ҫи®ЎпјҢиҝҷз§ҚжҖқиҖғж–№ејҸеңЁдёӯеӣҪжңүзқҖжј«й•ҝзҡ„дј з»ҹгҖӮдҪҶеңЁиҝҷеә§еұұдёӯпјҢиҝҳеҸ еҗҲзқҖеҹҺеёӮжЁЎејҸзҡ„з ”з©¶пјҢй«ҳеәҰеӣ жӯӨиў«иҮӘи§үйҷҗе®ҡеңЁ24mд»ҘдёӢпјҢе®ғзүҮж–ӯжҖ§зҡ„ж„ҸжҢҮзқҖдёҖз§Қ24mд»ҘдёӢйҷҗй«ҳзҡ„дҪҺеҹҺпјҢеӯҳеңЁдәҺдәәе·Ҙе’ҢеӨ©з„¶д№Ӣй—ҙгҖӮйҖҡиҝҮеӣҪйҷ…з«һж ҮпјҢдёҡдҪҷе»әзӯ‘е·ҘдҪңе®ӨиҺ·еҫ—дәҶиҝҷдёӘйЎ№зӣ®гҖӮ
е»әзӯ‘дёӢеҚҠж®ө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з®ҖеҚ•зҡ„й•ҝж–№еҪўпјҢеңЁдёҠеҚҠж®өејҖиЈӮдёәзұ»дјјеұұдҪ“зҡ„еҪўзҠ¶гҖӮдәә们д»ҺдёӯйғЁдёҖдёӘжүҒе№ізҡ„пјҢи·ЁеәҰ30mзҡ„з©ҝжҙһиҝӣе…ҘеҚҡзү©йҰҶгҖӮеҶ…и§Ӯж•ҙдёӘз»“жһ„пјҢеҢ…жӢ¬дёүйҒ“жңүеӨ§йҳ¶жўҜзҡ„еұұи°·пјҢдёӨйҒ“еңЁе®ӨеҶ…пјҢдёҖйҒ“еңЁе®ӨеӨ–пјӣеӣӣдёӘжҙһпјҢеҲҶеёғеңЁе…ҘеҸЈгҖҒй—ЁеҺ…е’Ңе®ӨеӨ–еұұи°·зҡ„еіӯеЈҒиҫ№дҫ§пјӣеӣӣдёӘеқ‘зҠ¶йҷўиҗҪпјҢдёӨдёӘеңЁдёӯеҝғпјҢдёӨдёӘеңЁе№Ҫж·ұд№ӢеӨ„гҖӮдёҖз§ҚеұұдҪ“зұ»еһӢеӯҰеҸ еҠ еңЁдёҠйқўпјҢе…¬е…ұз©әй—ҙж°ёиҝңжҳҜеӨҡи·Ҝеҫ„зҡ„пјҢе®ғд»Һең°йқўејҖе§ӢпјҢеҗ‘дёҠеҲҶеҸүпјҢеҪўжҲҗдёҖз§Қж №иҢҺзҠ¶зҡ„иҝ·е®«з»“жһ„гҖӮд№ҹз”ЁжқҘйҖӮеә”дёҖзӣҙдёҚзЎ®е®ҡзҡ„еұ•и§ҲеҶ…е®№гҖӮ
е»әзӯ‘зҡ„еҶ…еӨ–з”ұз«№жқЎжЁЎжқҝж··еҮқеңҹе’Ңз”Ё20з§Қд»ҘдёҠеӣһж”¶ж—§з –з“Ұж··еҗҲз Ңзӯ‘зҡ„еўҷдҪ“еҢ…иЈ№пјҢеҰӮдёҖз§ҚеңЁдәәе·Ҙе’ҢеӨ©з„¶д№Ӣй—ҙзҡ„жңүз”ҹе‘Ҫзҡ„е®ҸеӨ§дҝӯж·Ўзҡ„зү©пјҢдҪңдёәеұұзҡ„зү©жҖ§жҳҜе®ғе”ҜдёҖиҰҒиЎЁиҫҫзҡ„гҖӮ е®ғзҡ„еҢ—ж®өжөёеңЁдәәе·ҘејҖжҺҳзҡ„ж°ҙжұ дёӯпјҢеңҹеІёпјҢжӨҚиҠҰиӢҮпјҢж°ҙжңүиө°еҠҝпјҢеңЁдёӯж®өе…ҘеҸЈеӨ„жәўиҝҮдёҖйҒ“зҹіеққпјҢз»“жқҹеңЁеӨ§зүҮй№…еҚөзҹіж»©дёӯгҖӮеңЁе»әзӯ‘ејҖиЈӮзҡ„дёҠйғЁпјҢйҡҗи—ҸзқҖдёҖзүҮејҖйҳ”зҡ„е№іеҸ°пјҢйҖҡ иҝҮеӣӣдёӘеҪўзҠ¶дёҚеҗҢзҡ„иЈӮеҸЈпјҢиҝңжңӣзқҖеҹҺеёӮе’Ңиҝңж–№зҡ„зЁ»з”°дёҺеұұи„үгҖӮ

зҺӢжҫҚзҡ„и®ҫи®ЎдҪңе“Ғ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

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и®ҫи®Ў

зҺӢжҫҚи®ҫи®ЎйЈҺж јпјҡ

з”Ёж—§жқҗж–ҷе”ӨйҶ’еҹҺеёӮзҡ„и®°еҝҶ
иҺ·еҘ–иҜ„е®ЎиҜҚдёӯпјҢжңүиҝҷж ·дёҖеҸҘпјҡзҺӢжҫҚе»әзӯ‘иғҪеӨҹе”Өиө·еҫҖжҳ”пјҢеҚҙеҸҲдёҚзӣҙжҺҘдҪҝз”ЁеҺҶеҸІзҡ„е…ғзҙ гҖӮ
жңҖд»ЈиЎЁд»–жҖқжғізҡ„дҪңе“ҒжҳҜ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пјҢжҳҜзҺӢжҫҚ2004е№ҙз«һж Үиөўеҫ—зҡ„йЎ№зӣ®гҖӮ
вҖңжҲ‘жғіе‘ҠиҜүдәә们пјҢжӣҫз»Ҹзҡ„еҹҺеёӮз”ҹжҙ»жҳҜжҖҺж ·зҡ„гҖӮ10еӨҡе№ҙеүҚ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зҫҺдёҪзҡ„жө·жёҜеҹҺеёӮпјҢжңү30еӨҡдёӘдј з»ҹжқ‘иҗҪгҖӮеҲ°д»ҠеӨ©пјҢеҮ д№ҺжүҖжңүзҡ„дёңиҘҝйғҪиў«жӢҶйҷӨдәҶпјҢиҝҷйҮҢеҸҳжҲҗдәҶдёҖзүҮеҮ д№ҺжІЎжңүеӣһеҝҶзҡ„еҹҺеёӮгҖӮжҲ‘жҠҠиғҪеңЁиҝҷдёӘең°еҢә收йӣҶеҲ°зҡ„еҗ„з§Қж—§е»әзӯ‘жқҗж–ҷеҶҚж¬ЎеҲ©з”ЁпјҢдёҺж–°жқҗж–ҷдёҖиө·еңЁж–°зҡ„е»әзӯ‘дёҠж··еҗҲе»әйҖ гҖӮжҲ‘жғіе»әйҖ дёҖдёӘжңүиҮӘжҲ‘з”ҹе‘Ҫзҡ„е°ҸеҹҺеёӮпјҢе®ғиғҪйҮҚж–°е”ӨйҶ’иҝҷдёӘеҹҺеёӮзҡ„и®°еҝҶгҖӮвҖқ
еҗҢж ·пјҢеңЁи®ҫи®Ўе»әйҖ иұЎеұұж ЎеҢәж—¶пјҢд»–д»Һеҗ„ең°жӢҶжҲҝзҺ°еңә收йӣҶдәҶ700еӨҡдёҮеқ—дёҚеҗҢе№ҙд»Јзҡ„ж—§з –ејғз“ҰпјҢи®©е®ғ们еңЁиұЎеұұж ЎеҢәзҡ„еұӢйЎ¶е’ҢеўҷйқўдёҠиҺ·еҫ—ж–°з”ҹгҖӮзҺӢжҫҚдёҖзӣҙз§үжҢҒвҖңйҮҚе»әеҪ“д»ЈдёӯеӣҪжң¬еңҹе»әзӯ‘иүәжңҜеӯҰвҖқзҡ„еӯҰжңҜзҗҶеҝөпјҢжҳҜдёӯеӣҪжң¬еңҹе»әзӯ‘иҝҗеҠЁзҡ„д»ЈиЎЁдәәзү©гҖӮд»–и®ӨдёәпјҢеңЁиҝҮеҺ»зҡ„20е№ҙйҮҢпјҢдёӯеӣҪеҹҺеёӮеңЁеҸ‘еұ•зҡ„еҗҢж—¶пјҢд№ҹеҮ д№ҺжҠҠдј з»ҹзҡ„дёңиҘҝз ҙеқҸж®Ҷе°ҪгҖӮ
вҖңеӣ дёәеҸ‘еұ•еӨӘеҝ«пјҢжҖқиҖғеӨӘе°‘гҖӮеҫҲеӨҡдәәйғҪи®ӨдёәпјҢеҰӮд»Ҡзҡ„еҹҺеёӮе……ж–ҘзқҖй«ҳеұӮе»әзӯ‘пјҢзӣҙжҺҘеҶІеҮ»дәҶдёӯеӣҪдј з»ҹж–ҮеҢ–гҖӮдҪҶеҸҚиҝҮжқҘзңӢпјҢд»ҘжҲ‘们еӣҪ家иҝҷд№ҲеӨҡзҡ„дәәеҸЈпјҢй«ҳеұӮе»әзӯ‘еҮ д№ҺжҳҜдёҚеҸҜйҒҝе…Қзҡ„гҖӮжҲ‘и§үеҫ—й—®йўҳиҝҳжҳҜзјәе°‘жҖқиҖғе’ҢеҺҹеҲӣжҖ§зҡ„жҺўи®ЁпјҢе°Өе…¶еә”иҜҘжҺўи®Ёе’ҢдёӯеӣҪдј з»ҹз”ҹжҙ»з»ҸйӘҢзҡ„е…ізі»гҖӮвҖқ
зҺӢжҫҚпјҡе»әзӯ‘еёҲеҝ…йЎ»жҳҜжҖқжғіе®¶
д»–жҳҜзӢ¬ж ‘дёҖеёңдҪҶеҸҲеӨҮеҸ—дәүи®®зҡ„е»әзӯ‘еёҲпјҢжӣҙжҳҜжңүз«Ӣеңәзҡ„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пјҢжңүйЈҺйӘЁзҡ„ж–ҮдәәгҖӮвҖ”вҖ”ж–Ү|гҖҠе°Ҹеә·гҖӢи®°иҖ… еҪӯзһҫ е·ҙй»ҺжҠҘйҒ“
вҖңдәҢеҚҒеҮ дёҮдёӘжқ‘иҗҪеңЁж•ҙдёӘдёӯеӣҪеҪўжҲҗзҡ„дёҖдёӘдҪ“зі»пјҢе°ұеғҸз»ҳз”»дёӯеҮәзҺ°зҡ„дёҖж ·пјҢжңүзқҖж— дёҺдјҰжҜ”зҡ„дјҹеӨ§жҲҗе°ұгҖӮ然иҖҢ30е№ҙеҗҺзҡ„д»ҠеӨ©пјҢеҸҜиғҪеҸӘеү©дёӢе…«еҚғеӨҡдёӘиҝҷж ·зҡ„жқ‘еӯҗгҖӮвҖқзҺӢжҫҚиҫ№иҜҙиҫ№жҺЁдәҶжҺЁзңјй•ңпјҢзңјзҘһдёӯеёҰжңүеҝ§иҷ‘пјҡвҖңжҲ‘жүҖж„ҹеҲ°еҘҮжҖӘзҡ„жҳҜпјҢз«ҹ然没жңүдәәжіЁж„ҸеҲ°е®ғ们жӯЈеңЁж¶ҲеӨұгҖӮвҖқ
7жңҲ3ж—ҘпјҢе·ҙй»ҺеҚўжө®е®«пјҢзҺӢжҫҚеңЁвҖңдёӯ欧跨ж–ҮеҢ–й«ҳеі°и®әеқӣвҖқдёҠеҒҡдәҶзІҫеҪ©жј”и®ІгҖӮеңЁд»–зңӢжқҘпјҢиҢ…жӘҗдҪҺе°ҸпјҢжәӘдёҠйқ’йқ’иҚүзҡ„д№Ўжқ‘пјҢе·Іжёҗжёҗд»ҺжҜҸдёӘдәәзҡ„и®°еҝҶдёӯжҠҪзҰ»гҖӮ
дҪңдёә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е»әзӯ‘иүәжңҜеӯҰйҷўйҷўй•ҝгҖҒеҚҡеЈ«з”ҹеҜјеёҲзҡ„зҺӢжҫҚпјҢ2012е№ҙиҺ·еҫ—дәҶжҷ®еҲ©е…№е…Ӣе»әзӯ‘еҘ–гҖӮиҜҘеҘ–йЎ№жңүе»әзӯ‘з•ҢиҜәиҙқе°”еҘ–д№Ӣз§°гҖӮдҪңдёәйҰ–дҪҚиҺ·жӯӨж®ҠиҚЈзҡ„дёӯеӣҪдәәпјҢзҺӢжҫҚеҜ№дёӯеӣҪд№Ўжқ‘ж јеӨ–е…іжіЁгҖӮ
вҖңиҝҷеә§еҹҺеёӮзҡ„еӣһеҝҶжӯЈеңЁж…ўж…ўж¶ҲеӨұвҖқ
зҺӢжҫҚд»Ҡе№ҙиҺ·жҷ®з«Ӣе…№е…Ӣе»әзӯ‘еҘ–ж—¶пјҢгҖҠзәҪзәҰж—¶жҠҘгҖӢеңЁжҠҘйҒ“иҜҘж–°й—»ж—¶пјҢжүҖй…ҚеҸ‘зҡ„еӣҫзүҮжҳҜзҺӢжҫҚд»ЈиЎЁдҪңд№ӢдёҖвҖ”вҖ”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гҖӮ
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жүҖеңЁең°пјҢжӣҫжңү30еӨҡдёӘдј з»ҹжқ‘иҗҪгҖӮдҪҶеҪ“зҺӢжҫҚиҰҒи®ҫи®ЎеҚҡзү©йҰҶж—¶пјҢеҮ д№ҺжүҖжңүдёңиҘҝйғҪиў«жӢҶйҷӨдәҶпјҢеҸ–д»Је®ғ们зҡ„жҳҜжЁЎд»ҝиҘҝж–№зҡ„вҖңе°Ҹжӣје“ҲйЎҝвҖқзҡ„е•ҶдёҡеҢәе»әи®ҫгҖӮ
еңЁзҺӢжҫҚзңјйҮҢпјҢйӮЈйҮҢвҖңеҸҳжҲҗдәҶдёҖзүҮеҮ д№ҺжІЎжңүеӣһеҝҶзҡ„еҹҺеёӮвҖқпјҢиҖҢд»–жүҖиҰҒеҒҡзҡ„пјҢеҲҷжҳҜвҖңе”ӨйҶ’и®°еҝҶвҖқгҖӮ
д»Һиў«жӢҶжҺүзҡ„жқ‘иҗҪйҮҢпјҢзҺӢжҫҚжүҫеӣһ600еӨҡдёҮеқ—еәҹз –з“ҰзүҮгҖӮиҝҷдәӣи¶…иҝҮ80з§ҚдёҚеҗҢе°әеҜёгҖҒжқҘиҮӘдёҚеҗҢе№ҙд»Јзҡ„ж—§з“ҰзүҮпјҢжҲҗдәҶе»әйҖ еҚҡзү©йҰҶзҡ„еҺҹжқҗж–ҷгҖӮиҖҢжҢүз…§е®Ғжіўж°‘й—ҙдј з»ҹе»әйҖ е·Ҙиүәзҡ„е®ҡд№үпјҢзҺӢжҫҚжүҖйҮҮз”Ёзҡ„жӯЈжҳҜжҝ’дёҙеӨұдј зҡ„вҖңз“ҰзҲҝеўҷвҖқжҠҖиүәгҖӮз“ҰзҲҝеўҷйҮҢпјҢжңүзқҖеҸӨиҖҒе®Ғжіўзҡ„иҜ—жғ…з”»ж„ҸгҖӮ
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еңЁеҫҲеӨҡеҪ“ең°дәәзңјйҮҢпјҢжҲҗдәҶдёҖеә§еӣһеҝҶд№ӢеҹҺгҖӮе°ұжӣҫжңүдёҖдҪҚеҘ¶еҘ¶4ж¬ЎеҲ°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еҸӮи§ӮгҖӮзҺӢжҫҚй—®еҘ№дёәд»Җд№ҲпјҢеҘ¶еҘ¶иҜҙпјҢеҺҹжқҘзҡ„家没жңүдәҶпјҢдҪҶеңЁзҺӢжҫҚйҖ зҡ„жҲҝеӯҗдёҠпјҢеҲ°еӨ„йғҪиғҪеҸ‘зҺ°еҺҹжқҘ家зҡ„з—•иҝ№гҖӮ
зҪ‘еҸӢ们жҲҸи°‘вҖңдёӯеӣҪвҖқзҡ„иӢұж–ҮChinaи°җйҹіжҳҜвҖңжӢҶе“Әе„ҝвҖқгҖӮзҺӢжҫҚдәҰжӣҫж•°ж¬Ўж„ҹж…ЁиҮӘе·ұиә«еӨ„зҡ„еҸӨиҖҒеӣҪеәҰиў«жӢҶеҫ—йқўзӣ®е…ЁйқһгҖҒдё§еӨұдәҶи®°еҝҶгҖӮеңЁзҺӢжҫҚзңӢжқҘпјҢзҺ°еңЁдёӯеӣҪеҹҺеёӮз»“жһ„ж”ҜзҰ»з ҙзўҺпјҢжҜҸж Ӣй«ҳжҘјеӨ§еҺҰе°ұжҳҜдёҖзүҮвҖңж®–ж°‘ең°вҖқгҖӮ
е°Ҹж—¶еҖҷпјҢзҺӢжҫҚз”ҹжҙ»еңЁеҢ—дә¬е»әеӣҪй—Ёйҷ„иҝ‘дёҖдёӘе°ҸеӣӣеҗҲйҷўдёӯпјҢеңЁеӣӣеҗҲйҷўеӨ–жһҒзӣ®йғҪжҳҜеҶңз”°пјҢзңӢеҫ—еҲ°еҹҺеёӮиҫ№зјҳгҖӮзҺӢжҫҚиҜҙпјҢеҰӮд»ҠиҮӘе·ұеңЁеҢ—дә¬зҡ„жҲҝеӯҗжӯЈеңЁиў«жӢҶжҜҒпјҢз”ЁдәҺе»әйҖ зӨҫ科йҷўзҡ„ж–°еӨ§жҘјгҖӮвҖңзҺ°еңЁзҡ„еҢ—дә¬еҲ°еӨ„йғҪжҳҜең°ж Үе»әзӯ‘пјҢйёҹе·ўгҖҒж–°еӨ®и§ҶеӨ§жҘјвҖҰвҖҰиҝҷеә§еҹҺеёӮзҡ„еӣһеҝҶжӯЈеңЁж…ўж…ўж¶ҲеӨұпјҢиҖҢжҲ‘ж— иғҪдёәеҠӣгҖӮвҖқ 10е№ҙеүҚпјҢзҺӢжҫҚжӣҫеңЁжқӯе·һдёҖ家д№Ұеә—зҝ»еҲ°дёҖжң¬иҖҒзӣёеҶҢпјҢзңӢеҲ°дёҖеҗҚдј ж•ҷеЈ«жӢҚж‘„зҡ„1900е№ҙзҡ„еҢ—дә¬пјҢд»–йЎҝж—¶жҪёз„¶жіӘдёӢгҖӮ
еңЁзҺӢжҫҚзңӢжқҘпјҢдёӯеӣҪзҡ„д№Ўжқ‘д№ҹжӯЈеҸ‘з”ҹе·ЁеҸҳпјҢвҖңе®ғе’ҢеҹҺеёӮжҳҜеҲҶиЈӮзҡ„вҖқгҖӮвҖңдёӯеӣҪзҡ„еҲ¶еәҰдёӢпјҢд№Ўжқ‘зҡ„жҲҝеӯҗйғҪжҳҜеҶңж°‘иҮӘе·ұе»әзҡ„пјҢе»әзӯ‘еёҲжІЎжңүжқғеҲ©еҲ°д№Ўжқ‘еҺ»еҒҡд»Җд№ҲгҖӮвҖқ
вҖңдёӯеӣҪжӣҫз»ҸжҳҜдёҖдёӘеңЁеҹҺеёӮе’Ңд№Ўжқ‘йҒҚеёғиҜ—жғ…з”»ж„Ҹзҡ„еӣҪ家гҖӮвҖқеңЁзҺӢжҫҚзҡ„жҸҸиҝ°дёӯпјҢдёӯеӣҪеҸӨд»Јзҡ„жқ‘иҗҪпјҢе»әзӯ‘з»қдёҚжҳҜдё»дҪ“пјҢе®ғ们еӨ§йғҪиў«еӨ§ж ‘жҺ©жҳ зқҖпјҢжҲ–дёҖеҚҠеұұж°ҙдёҖеҚҠе»әзӯ‘пјҢе»әзӯ‘е®Ңе…ЁиһҚе…ҘиҮӘ然д№ӢдёӯгҖӮ
еңЁзҺӢжҫҚзңӢжқҘпјҢ6гҖҒ7дё–зәӘд№ӢеүҚзҡ„дёӯеӣҪе’Ң欧жҙІеҫҲеғҸпјҢз»ҳз”»иүәжңҜд»ҘдәәдҪңдёәдё»иҰҒеҜ№иұЎгҖӮ7дё–зәӘд№ӢеҗҺпјҢз»ҸиҝҮдёҖзі»еҲ—ж®Ӣй…·зҡ„еҶ…жҲҳгҖҒз»ҸжөҺеҚұжңәгҖҒж”ҝжІ»и…җиҙҘгҖҒиҮӘ然зҒҫе®ізӯүпјҢдёӯеӣҪзҡ„ж•ҙдёӘзҹҘиҜҶз•ҢеҸ‘з”ҹдәҶд»·еҖји§Ӯзҡ„жүӯиҪ¬вҖ”вҖ”ж•ҙдёӘе…ҙи¶ЈејҖе§Ӣйқўеҗ‘иҮӘ然гҖӮвҖңеӣ дёәиҮӘ然жҜ”дәәй—ҙзӨҫдјҡжӣҙзҫҺеҘҪпјҢжҳҜйңҖиҰҒй•ҝжңҹз»ҙжҠӨзҡ„еҜ№иұЎгҖӮвҖқ
вҖңеҪ“дёӯеӣҪзҡ„зҹҘиҜҶз•Ңе°Ҷе…ҙи¶ЈиҪ¬еҗ‘иҮӘ然зҡ„ж—¶еҖҷпјҢзҡҮеёқ们еңЁйғҪеҹҺйҮҢз”ЁжңЁеӨҙйҖ 100зұіе·ҰеҸізҡ„й«ҳеұӮе»әзӯ‘пјҢиҝҷдәӣеңЁж•Ұз…ҢеЈҒз”»дёҠйғҪиғҪзңӢеҲ°гҖӮдҪҶжҳҜеҲ°дәҶ7дё–зәӘпјҢи§Ӯеҝөж”№еҸҳеҗҺпјҢй«ҳзҡ„е»әзӯ‘и¶ҠжқҘи¶Ҡе°‘пјҢеӣ дёәиҝҷдәӣе»әйҖ дҪҝеҫ—иҮӘ然иө„жәҗд»ҳеҮәдәҶе·ЁеӨ§д»Јд»·гҖӮеңЁе®Ӣжңқзҡ„ж—¶еҖҷпјҢжғіжүҫдёҖж №еӨ§зҡ„жңЁеӨҙжҹұеӯҗе·Із»ҸеҫҲеӣ°йҡҫгҖӮиҖҢдёӯеӣҪзҡ„ж–Үдәәйҳ¶еұӮд№ҹејҖе§Ӣе…іеҝғиҮӘе·ұзҡ„з”ҹжҙ»пјҢ他们дҪҸеңЁиҮӘ然д№ӢдёӯпјҢз”ҹжҙ»еңЁйқһеёёжңҙзҙ зҡ„зҺҜеўғйҮҢгҖӮвҖқзҺӢжҫҚиҜҙгҖӮ
йҮҚиҝ”иҮӘ然д№ӢйҒ“
д№ҹи®ёзҺ°еңЁдёӯеӣҪйқўдёҙзҡ„пјҢдёҚд»…жҳҜеӣәжңүе»әзӯ‘иў«жӢҶжҜҒпјҢж–°е»әзӯ‘д№ҹжёҗжёҗеӨұеҺ»зҒөйӯӮгҖӮ
еӨҡе№ҙеүҚпјҢзҺӢжҫҚжӣҫиҝҪйҡҸжІҲд»Һж–ҮгҖҠж№ҳиЎҢж•Ји®°гҖӢзҡ„и„ҡжӯҘжёёиө°3дёӘжңҲпјҢж—…иЎҢдёӯж—ўдёҚз»ҷжҲҝеӯҗз…§зӣёпјҢд№ҹдёҚжҗһеңҹең°жөӢйҮҸпјҢжІЎдёҖзӮ№е»әзӯ‘еёҲж ·еӯҗгҖӮ
еңЁж·ұе…Ҙд№Ўжқ‘ж—¶пјҢзҺӢжҫҚдёҚд»…е…іжіЁжқ‘еә„дёӯжңүеӨҡе°‘з§Қе»әзӯ‘пјҢд»–иҝҳеҸ‘зҺ°дәҶдёҖ件жңүи¶Јзҡ„дәӢжғ…пјҡиҝҷдәӣжқ‘еӯҗйҮҢеӯҳеңЁеӨ§йҮҸеӯҰж ЎгҖӮд»–и®°еҫ—пјҢиҮӘе·ұжӣҫеҲ°иҝҮдёҖдёӘеҸ«йқ’жөӘж»©зҡ„е°Ҹжқ‘пјҢжқ‘е°ҸеӯҰзҡ„иҖҒеёҲе°ұзқҖеӨңиүІдё“зЁӢжӢңдјҡиҝҷдҪҚвҖңжқҘи®ҝиҖ…вҖқгҖӮиҒҠзҡ„д»Җд№ҲзҺӢжҫҚе·Іи®°дёҚжё…пјҢвҖңеҸӘи®°еҫ—йӮЈйҮҢжІЎзҒҜпјҢдёҖдёӘдәәеҗ№зқҖеҸЈзҗҙдёҖи·ҜиёҸжӯҢиҖҢжқҘгҖӮвҖқ
вҖңеңЁдёӯеӣҪзҡ„еҺҶеҸІдёҠпјҢ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жҳҜдҪҸеңЁд№Ўжқ‘зҡ„гҖӮйҷӨдәҶеҪ“е®ҳпјҢйҖҖдј‘гҖҒж”ҫеҒҮжҲ–иҖ…еҲ«зҡ„жғ…еҶөпјҢ他们йғҪдјҡеӣһеҲ°д№Ўжқ‘е’ҢзҲ¶жҜҚз”ҹжҙ»еңЁдёҖиө·пјҢиҝҷеҪўжҲҗдёҖз§ҚеҲ¶еәҰгҖӮжүҖд»Ҙд№Ўжқ‘жңүзӣёеҪ“й«ҳзҡ„иүәжңҜгҖҒж–ҮеӯҰгҖҒж•ҷиӮІж°ҙе№ігҖӮеҶңж°‘зҡ„еӯҗејҹе’Ңиҝҷдәӣж–Үдәәз”ҹжҙ»еңЁдёҖиө·пјҢд№ҹеҸҜд»ҘжҺҘеҸ—й«ҳж°ҙе№ізҡ„ж•ҷиӮІгҖӮиҝҷз§ҚеҲ¶еәҰдёҖзӣҙжҢҒз»ӯеҲ°е·®дёҚеӨҡ20дё–зәӘеҲқпјҢеӣ дёәиҘҝж–№зҡ„ж•ҷиӮІдҪ“зі»иҝӣжқҘпјҢе®ғжүҚз»“жқҹгҖӮвҖқеңЁзҺӢжҫҚзңӢжқҘеҘҮжҖӘзҡ„жҳҜпјҢвҖңеҸӘиҰҒжҳҜиҝӣдәҶиҘҝж–№зҡ„еӯҰж ЎпјҢеҫҲеӨҡеӯҰз”ҹиҝӣдәҶеҹҺе°ұдёҚжғіеҶҚеӣһеҲ°д№Ўжқ‘гҖӮвҖқ
вҖңе®һйҷ…дёҠжҲ‘们еӣҪ家жӣҫз»ҸжңүзқҖйқһеёёйҮҚиҰҒзҡ„дёңиҘҝпјҢжҲ‘з§°д№ӢдёәдёҖдёӘеӣҪ家зҡ„жҷҜи§Ӯзі»з»ҹгҖӮвҖқзҺӢжҫҚжӢ…еҝ§иҝҷж ·зҡ„жҷҜи§Ӯзі»з»ҹзҺ°еңЁжҳҜеҗҰиҝҳеӯҳеңЁгҖӮ
вҖңе…¶е®һжҲ‘们д»ҘеүҚзҡ„е»әзӯ‘еӯҰйғҪдёҚжҳҜиҘҝж–№ж„Ҹд№үдёҠзҡ„пјҢжҳҜд»ҘеӯҰиҖ…е’Ңе®—ж•ҷз»„жҲҗзҡ„дёҖдёӘдҪ“зі»пјҢе®ғжңүдёҖдёӘеҹәжң¬зҡ„д»·еҖји§ӮпјҢжҲ‘们称д№ӢдёәвҖҳйҒ“вҖҷгҖӮеңЁжҲ‘们зҡ„жҖқиҖғйҮҢиҮӘ然永иҝңжҳҜжңҖйҮҚиҰҒзҡ„еӣ зҙ гҖӮвҖқзҺӢжҫҚиҜҙпјҢд№Ўжқ‘е»әзӯ‘жҳҜдёҖдёӘдҪ“зі»пјҢиҝҷдёӘдҪ“зі»жҳҜеӯҰиҖ…е’Ңе·ҘеҢ дёҖиө·еҲӣйҖ зҡ„гҖӮйӮЈйҮҢжІЎжңүдё“дёҡзҡ„е»әзӯ‘еёҲпјҢжңҖе…ій”®зҡ„й—®йўҳеңЁдәҺеҜ№иҮӘ然зҡ„жҖҒеәҰгҖӮ
дёҺеҫҲеӨҡзҹҘеҗҚе»әзӯ‘еёҲзҡ„жҲҗй•ҝд№Ӣи·ҜдёҚеҗҢпјҢзҺӢжҫҚжІЎжңүеҮәеӣҪз•ҷеӯҰгҖӮеңЁд»–зңӢжқҘпјҢдёӯеӣҪжңүдә”еҚғе№ҙзҡ„еҺҶеҸІпјҢжңүйӮЈд№ҲеӨҡдјҳз§Җзҡ„е»әзӯ‘пјҢвҖңжІЎжңүжҜ”еңЁдёӯеӣҪеӯҰе»әзӯ‘жӣҙеҘҪзҡ„ең°ж–№гҖӮвҖқиҖҢд»ҺеӯҰз”ҹж—¶д»Јиө·пјҢзҺӢжҫҚе°ұжғіжҠҠдёӯеӣҪеұұж°ҙз”»зҡ„жҖқз»ҙж–№ејҸ移жӨҚеҲ°е»әзӯ‘йўҶеҹҹгҖӮеӨҡе№ҙеүҚпјҢдёӯеӣҪе»әзӯ‘иҜ„и®ә家еҸІе»әжӣҫдёә5家дёӯеӣҪе»әзӯ‘и®ҫи®ЎдәӢеҠЎжүҖеңЁзәҪзәҰзӯ–еҲ’дәҶдёҖдёӘеұ•и§ҲгҖӮеҪ“е…¶д»–е»әзӯ‘еёҲж»”ж»”дёҚз»қи®Іи§ЈиҮӘе·ұзҡ„дҪңе“Ғж—¶пјҢзҺӢжҫҚеҚҙй“әејҖдёҖе№…жқҺе…¬йәҹзҡ„еұұж°ҙз”»пјҢдёәеӨ–еӣҪеҗҢиЎҢ们讲иө·дәҶз”»дёӯзҡ„з©әй—ҙеёғеұҖгҖӮеңЁзҺӢжҫҚзңӢжқҘпјҢдёӯеӣҪдј з»ҹеұұж°ҙз”»дёҚд»…жҳҜеңЁжҸҸж‘№жҷҜзү©пјҢжӣҙжҳҜдёҖз§ҚжҙһжӮүдё–з•Ңзҡ„и§’еәҰгҖӮ
иҖҢдҪ“зҺ°зҺӢжҫҚвҖңеұұж°ҙз”»жҖқз»ҙвҖқжӣҙдёәеҪ»еә•зҡ„пјҢжҒҗжҖ•жҳҜд»–еҸҰдёҖдёӘд»ЈиЎЁдҪңвҖ”вҖ”е…¶д»»ж•ҷзҡ„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иұЎеұұж ЎеҢәгҖӮиұЎеұұж ЎеҢәе·ҘзЁӢиў«еҲҶжҲҗдёӨжңҹгҖӮз”»еӣҫж—¶пјҢзҺӢжҫҚжІЎжңүеҖҹеҠ©д»»дҪ•з”өи„‘иҪҜ件пјҢиҖҢжҳҜжҢүз…§дёӯеӣҪдј з»ҹз»ҳз”»ж–№жі•жүӢе·ҘдҪңдёҡгҖӮиҖҢжңүдёҖеӨ©пјҢеҪ“дёӯеӣҪзҫҺйҷўйҷўй•ҝи®ёжұҹз«ҷеңЁ3еҸ·жҘјж•°зұій«ҳзҡ„й—ЁжҙһеүҚеҫҖеӨ–зңӢж—¶пјҢзӘҒ然иҜҙпјҡвҖңе’ҰпјҢиҝҷдёҚжҳҜиҢғе®Ҫзҡ„гҖҠжәӘеұұиЎҢж—…еӣҫгҖӢ?вҖқзҺӢжҫҚеҲҷзӯ”пјҡвҖңдҪ еҸ‘зҺ°дәҶ?вҖқ
жҢүз…§зҺӢжҫҚзҡ„иҜҙжі•пјҢдёӯеӣҪзҡ„дҪ“зі»еҸҜиғҪе’ҢеӨ§е®¶жғізҡ„дёҚдёҖж ·пјҢе®ғеҹәжң¬еҸ‘з”ҹеңЁжҳҺжңқгҖӮжҳҺжңқзҡ„ж”ҝжІ»дҪ“зі»жҺҘиҝ‘еҗӣдё»з«Ӣе®Әзҡ„дҪ“зі»пјҢд№ҹе°ұжҳҜд»Ҙж–Үдәәдёәдё»зҡ„еҶ…йҳҒдҪ“зі»гҖӮеңЁд№Ўжқ‘жҳҜд»Ҙж–Үдәәдёәдё»зҡ„иҮӘжІ»дҪ“зі»пјҢжҳҜиҮӘжҲ‘з®ЎзҗҶзҡ„иҮӘжІ»дҪ“зі»гҖӮеӨ§е®¶е…ұдә«дёҖдёӘд»·еҖји§ӮпјҢд»ҘиҮӘжІ»зҡ„ж–№ејҸжқҘз®ЎзҗҶгҖӮ
вҖңзҺ°еңЁзҡ„е®ҳе‘ҳеңЁи°ҲеҹҺеёӮ规еҲ’зҡ„ж—¶еҖҷд№ҹеңЁжғіпјҢеҰӮдҪ•жҠҠиҝҷз§ҚиҘҝж–№зҡ„з®ЎзҗҶж–№ејҸжё—йҖҸеҲ°д№Ўжқ‘еҺ»гҖӮдҪҶжҳҜдёӯеӣҪд№Ўжқ‘зҡ„ж•°йҮҸеәһеӨ§пјҢеӨҚжқӮзҡ„й—®йўҳеҫҲеӨҡгҖӮе»әзӯ‘зҡ„дҝқжҠӨй—®йўҳиғҢеҗҺжҳҜеҲ¶еәҰзҡ„й—®йўҳпјҢд»…д»…и°ҲдҝқжҠӨжҳҜдёҚеӨҹзҡ„гҖӮдёҚеҸҜжғіиұЎдёҖдёӘжңүдә”еҚғе№ҙеҺҶеҸІзҡ„еӣҪ家дјҡеҰӮжӯӨдёҚзҲұжғңиҮӘе·ұзҡ„ж–ҮжҳҺгҖӮеңЁиҝҷж ·зҡ„зҺҜеўғдёӯпјҢе»әзӯ‘и®ҫи®ЎеёҲ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иҒҢдёҡзҡ„и®ҫи®ЎеёҲжҳҜдёҚеӨҹзҡ„пјҢд»–еҝ…йЎ»жҳҜдёӘжҖқжғіе®¶пјҢеҝ…йЎ»иҰҒжңүиҮӘе·ұзҡ„з«ӢеңәпјҢиҖҢдёҚд»…д»…жҳҜдёҖдёӘжҺҘдёҖдёӘең°еҒҡйЎ№зӣ®гҖӮвҖқзҺӢжҫҚиҜҙгҖӮ
ж–Үдәәзҡ„иӢұйӣ„иүІеҪ©
зҺӢжҫҚзҡ„зҗҶжғідёҺз«ӢеңәпјҢжӣҫи®©дёҖдәӣең°дә§з•ҢдәәеЈ«з”ЁдёӨдёӘеӯ—еҪўе®№д»–пјҡеҶІгҖҒжӢ—гҖӮ
зҺӢжҫҚеҮ д№ҺдёҚжҺҘе•Ҷдёҡе»әзӯ‘гҖӮе”ҜдёҖдёҖж¬ЎпјҢжҳҜжқӯе·һй’ұеЎҳжұҹиҫ№зҡ„дҪҸе®…е°ҸеҢәвҖңй’ұжұҹж—¶д»ЈвҖқгҖӮзҺӢжҫҚе°Ҷе…¶е‘ҪеҗҚдёәвҖңеһӮзӣҙйҷўе®…вҖқвҖ”вҖ”жҜҸеӣӣжҲ·е…ұз”ЁдёҖдёӘе°ҸйҷўпјҢйҷўдёӯеҸҜз§ҚиҠұиҚүпјҢйӮ»еұ…еҸҜеқҗйҷўдёӯи°ҲеӨ©гҖӮ
зҺӢжҫҚе–ңж¬ўйҷўе®…й—Іи°Ҳзҡ„йӮЈд»Ҫж„ҸеўғпјҢжёҠжәҗжҲ–и®ёеңЁеҚҒеӨҡе№ҙеүҚзҡ„дёҖдёӘжё…жҷЁпјҡеңЁж№ҳиҘҝдёҖдёӘеҗҚеҸ«жҙһеәӯжәӘзҡ„жқ‘иҫ№пјҢ28еІҒзҡ„зҺӢжҫҚзңӢеҲ°жІ…жұҹиҫ№еҮ дёӘеҶңж°‘йҖ дёҖеә§дёҙжұҹзҡ„еҗҠи„ҡжҘјпјҢйқ’еұұзҝ и°·дёӯпјҢеұӢжһ¶вҖңзҒөз§ҖиҖҢеқҡе®ҡпјҢз»Ҷи…»иҖҢжҫ„жҳҺвҖқгҖӮд№ӢеҗҺпјҢзҺӢжҫҚеңЁгҖҠи®ҫи®Ўзҡ„ејҖе§ӢгҖӢдёҖж–ҮдёӯеҶҷйҒ“пјҡвҖңйӮЈеә§еҗҠи„ҡжҘјжІЎжңүе®Ңе·ҘпјҢж°ёиҝңдёҚдјҡе®Ңе·ҘгҖӮдёҚз»Ҹж„Ҹзҡ„пјҢе®ғжҖ»жҳҜзӘҒе…Җең°е‘ҲзҺ°еңЁжҲ‘зҡ„йқўеүҚгҖӮвҖқ
然иҖҢзҺӢжҫҚжүҖи®ҫи®Ўзҡ„вҖңеһӮзӣҙйҷўе®…вҖқпјҢж„ҸеўғжңӘеҝ…дәәдәәйғҪжҮӮгҖӮжңүдәәдҫҝи§ҶвҖңз©әдёӯйҷўиҗҪвҖқж— з”Ёдё”жҲҗжң¬е·ЁеӨ§гҖӮ вҖңжҲ‘йҷӘзқҖдҪ е®һзҺ°зҗҶжғіпјҢдёҖдёӢдә”еҚғдёҮе°ұдёҚи§ҒдәҶгҖӮвҖқвҖ”вҖ”ејҖеҸ‘е•ҶдёҺзҺӢжҫҚпјҢеҠҝеҝ…жҖҖжҠұзқҖдёҚеҗҢзҡ„вҖңзҗҶжғівҖқгҖӮ
жңүдәәжӣҫиҜҙпјҢзҺӢжҫҚжҳҜвҖңдёӯеӣҪжңҖе…·дәәж–Үж°”иҙЁзҡ„е»әзӯ‘家вҖқгҖӮд»–е–ңж¬ўз®«з®ЎпјҢж“…й•ҝд№Ұжі•еұұж°ҙз”»гҖӮд»–дёҚз”Ёз”өи„‘дёҚдёҠзҪ‘пјҢз”ҡиҮіеҫҲе°‘дҪҝз”ЁжүӢжңәгҖӮд»–и®ӨдёәйӮЈдәӣдәӢзү©еҜ№з”ҹжҙ»ж— зӣҠпјҢд»–иҰҒдҝқжҢҒеҶ…еҝғе®ҒйқҷгҖӮд»–д№җдәҺдҪ“е‘іеҸӨд»ЈдёӯеӣҪж–ҮдәәеңЁйҖ еӣӯж—¶жөҒйңІзҡ„жёёжҲҸж„ҹпјҢд№ҹе–ңж¬ўеҚҡе°”иө«ж–ҜеңЁе°ҸиҜҙгҖҠдәӨеҸүе°Ҹеҫ„зҡ„иҠұеӣӯгҖӢдёӯиҗҘйҖ зҡ„зҘһз§ҳж°ӣеӣҙпјҢжӣҙзқҖиҝ·дәҺеҚЎе°”з»ҙиҜәдҪңе“ҒдёӯжөҒйңІеҮәзҡ„еҘҮзү№иҖҢжөӘжј«зҡ„жғіиұЎгҖӮ
жҜҸж¬ЎеҺ»е·ҙй»ҺпјҢзҺӢжҫҚйғҪе–ңж¬ўеҺ»еңЈж—ҘиҖіжӣјеӨ§иЎ—зҡ„иҠұзҘһе’–е•ЎйҰҶгҖӮйӮЈжӣҫжҳҜжө·жҳҺеЁҒгҖҒиҗЁзү№еёёеҺ»зҡ„ең°ж–№гҖӮеңЁйӮЈдёӘз®Җжңҙзҡ„иЎ—и§’пјҢзҺӢжҫҚе–ңж¬ўиҮӘе·ұй—ІеқҗпјҢдёҖжқҜе’–е•Ўжү“еҸ‘й—Іж•Јж—¶е…үгҖӮ
зӘ—еӨ–иЎҢдәәеҢҶеҢҶгҖӮз©әж°”дёӯдёҖз§Қж°”жҒҜиҪ»иҪ»жөҒж·ҢгҖӮ
йӮЈз§Қж°”жҒҜпјҢжҲ–иҖ…еҸ«еҒҡвҖңдј з»ҹвҖқ;д№ҹжҲ–иҖ…еҸ«еҒҡжғ…жҖҖдёҺж„ҸеўғгҖӮ
жңүеўғдәҰжңүжғ…гҖӮ
зҺ°еңЁзҡ„еҢ—дә¬еҲ°еӨ„йғҪжҳҜең°ж Үе»әзӯ‘пјҢйёҹе·ўгҖҒж–°еӨ®и§ҶеӨ§жҘјвӢҜвӢҜиҝҷеә§еҹҺеёӮзҡ„еӣһеҝҶжӯЈеңЁж…ўж…ўж¶ҲеӨұпјҢиҖҢжҲ‘ж— иғҪдёәеҠӣгҖӮ
дёҚеҸҜжғіиұЎдёҖдёӘжңүдә”еҚғе№ҙеҺҶеҸІзҡ„еӣҪ家дјҡеҰӮжӯӨдёҚзҲұжғңиҮӘе·ұзҡ„ж–ҮжҳҺгҖӮеңЁиҝҷж ·зҡ„зҺҜеўғдёӯпјҢе»әзӯ‘и®ҫи®ЎеёҲ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иҒҢдёҡзҡ„и®ҫи®ЎеёҲжҳҜдёҚеӨҹзҡ„пјҢд»–еҝ…йЎ»жҳҜдёӘжҖқжғіе®¶пјҢеҝ…йЎ»иҰҒжңүиҮӘе·ұзҡ„з«ӢеңәгҖӮ

зҺӢжҫҚд»ЈиЎЁдҪңе“ҒпјҡиӢҸе·һеӨ§еӯҰж–ҮжӯЈеӯҰйҷўеӣҫд№ҰйҰҶ
еҹәең°еҢ—йқўйқ еұұпјҢеұұдёҠе…ЁйғЁз«№жһ—пјҢеҚ—йқўдёҙж°ҙпјҢдёҖеә§з”ұеәҹз –еңәеҸҳжҲҗзҡ„ж№–жіҠпјҢе…ЁдёәеқЎең°пјҢеҚ—дҪҺеҢ—й«ҳпјҢй«ҳе·®4mгҖӮеҚ—еҢ—еҗ‘иҝӣж·ұжө…пјҢдёңиҘҝеҗ‘д»Ҙж°ҙдёәз•ҢпјҢжӣІжҠҳзӢӯй•ҝгҖӮжҢүз…§йҖ еӣҪдј з»ҹпјҢ е»әзӯ‘еңЁвҖңеұұж°ҙвҖқд№Ӣй—ҙжңҖдёҚеә”зӘҒеҮәпјҢиҝҷеә§еӣҫд№ҰйҰҶе°Ҷиҝ‘дёҖеҚҠзҡ„дҪ“з§ҜеӨ„зҗҶжҲҗеҚҠең°дёӢпјҢд»ҺеҢ—йқўзңӢпјҢдёүеұӮзҡ„е»әзӯ‘еҸӘжңүдәҢеұӮгҖӮзҹ©еҪўдё»дҪ“е»әзӯ‘ж—ўжҳҜйЈҳеңЁж°ҙдёҠзҡ„пјҢд№ҹжҳҜжІҝеҚ—еҢ—ж–№еҗ‘з©ҝи¶Ҡ зҡ„пјҢиҝҷдёӘж–№еҗ‘жҳҜзӮҺзғӯеӨҸеӯЈзҡ„дё»еҜјйЈҺеҗ‘гҖӮеҖјеҫ—ејәи°ғзҡ„жҳҜпјҢжІҝзқҖиҝҷжқЎз©ҝи¶Ҡи·ҜзәҝпјҢз”ұеұұиө°еҲ°ж°ҙпјҢеӣӣдёӘж•ЈиҗҪзҡ„е°ҸжҲҝеӯҗе’Ңдё»дҪ“е»әзӯ‘зӣёжҜ”пјҢе°әеәҰжӮ¬ж®ҠпјҢдҪҶеңЁиҝҷйҮҢпјҢеҸҜд»Ҙзӣёдә’иҪ¬еҢ–зҡ„ е°әеәҰжҳҜдёӯеӣҪдј з»ҹйҖ еӣӯжңҜзҡ„зІҫй«“гҖӮиҖҢд»ҺдёҖдёӘж–Үдәәзҡ„и§’еәҰзңӢпјҢйӮЈдәӣе°ҸжҲҝеӯҗд№ҹи®ёжӣҙйҮҚиҰҒпјҢдҫӢеҰӮпјҢж°ҙдёӯйӮЈеә§дәӯеӯҗиҲ¬зҡ„жҲҝеӯҗпјҢеӣҫд№ҰйҰҶзҡ„вҖңиҜ—жӯҢдёҺе“ІеӯҰвҖқйҳ…и§Ҳе®ӨпјҢдҫҝжҳҜдёҖдёӘдёӯеӣҪж–Ү дәәзңӢеҫ…жүҖеӨ„дё–з•Ңзҡ„вҖңи§ӮзӮ№вҖқпјҢдёҖдёӘдәәдёҺиҮӘ然з”ҹжҖҒзӣёдә’е№іиЎЎзҡ„дҪҚзҪ®гҖӮ
еұұи„ҡзҡ„дёҖзүҮз«№жө·жҳҜиғҢжҷҜпјҢжіўе…үзІјзІјзҡ„и“қиүІж№–йқўжҳҜеүҚжҷҜпјҢеҮ дёӘзҷҪиүІвҖңзӣ’еӯҗвҖқдјји·іи·ғиҲ¬зҡ„е§ҝеҠҝпјҢеҸҲдјјйҡҸж„Ҹе Ҷж”ҫзҡ„еҮ дҪ•дҪ“пјҢеҠЁйқҷд№Ӣй—ҙпјҢдёҺеӨ§иҮӘ然е’Ңи°җе…ұеӨ„гҖӮжңүзҜҮе»әзӯ‘иҜ„и®әж–Үз« иҝҷж ·еҲҶжһҗзҺӢжҫҚпјҡвҖңеҫҲй•ҝдёҖж®өж—¶й—ҙпјҢзҺӢжҫҚз—ҙиҝ·дәҺдёҖз§ҚжёёжҲҸвҖҰвҖҰжҷғеҠЁзқҖжүӢдёӯзҡ„жңЁзӣ’пјҢе…ӯеҸӘи§іеӯҗеңЁзӣ’еӯҗдёӯж»ҡеҠЁпјҢеҪјжӯӨж’һеҮ»жҲ–ж’һеҗ‘еҗҲеЈҒеҸ‘еҮәжё…и„Ҷзҡ„еЈ°е“ҚпјҢйҡҸеҗҺе‘ҲзҺ°еңЁжЎҢйқўдёҠзҡ„ жҳҜе…ӯеҸӘе ҶеҸ жҲ–ж•ЈиҗҪзҡ„з«Ӣж–№дҪ“гҖӮвҖқ
иҝҷеҸҘиҜқзҡ„ж„ҸжҖқз”ЁеңЁж–ҮжӯЈеӯҰйҷўдёҠжӯЈжҒ°еҘҪгҖӮвҖңеҮ дёӘе°Ҹз«Ӣж–№дҪ“з”ҡиҮіеҶІз ҙдәҶеӨ§зӣ’еӯҗзҡ„йҮҚйҮҚжқҹзјҡпјҢз ҙиҢ§иҖҢеҮәпјҢд»ҺиҖҢе®ҢжҲҗдәҶдёҖз§ҚвҖҳеӨҚжқӮе»әзӯ‘вҖ”вҖ”з®ҖеҚ•еҹҺеёӮпјҲcomplexhouseвҖ”simplecityпјүвҖҷзҡ„и·ғиҝӣгҖӮвҖқ

зҺӢжҫҚзҡ„иҺ·еҘ–зҗҶз”ұпјҡжҷ®еҲ©е…№е…ӢеҘ–иҜ„委иҫһз§°пјҡвҖңзҺӢжҫҚеңЁдёәжҲ‘们жү“ејҖе…Ёж–°и§ҶйҮҺзҡ„еҗҢж—¶пјҢеҸҲеј•иө·дәҶеңәжҷҜдёҺеӣһеҝҶд№Ӣй—ҙзҡ„е…ұйёЈгҖӮд»–зҡ„е»әзӯ‘зӢ¬е…·еҢ еҝғпјҢиғҪеӨҹе”Өиө·еҫҖжҳ”пјҢеҚҙеҸҲдёҚзӣҙжҺҘдҪҝз”ЁеҺҶеҸІзҡ„е…ғзҙ гҖӮвҖқжҷ®еҲ©е…№е…Ӣе…Ҳз”ҹи®ӨдёәпјҢиҜ„委дјҡеҶіе®ҡе°ҶеҘ–йЎ№жҺҲдәҲдёҖеҗҚдёӯеӣҪе»әзӯ‘еёҲжҳҜе…·жңүеҲ’ж—¶д»Јж„Ҹд№үзҡ„дёҖжӯҘпјҢж Үеҝ—зқҖдёӯеӣҪеңЁе»әзӯ‘зҗҶжғіеҸ‘еұ•ж–№йқўе°ҶиҰҒеҸ‘жҢҘзҡ„дҪңз”Ёеҫ—еҲ°дәҶдё–з•Ңзҡ„и®ӨеҸҜгҖӮд»–иҜҙпјҢвҖңжңӘжқҘеҮ еҚҒе№ҙдёӯеӣҪеҹҺеёӮеҢ–е»әи®ҫзҡ„жҲҗеҠҹеҜ№дёӯеӣҪд№ғиҮідё–з•ҢпјҢйғҪе°ҶйқһеёёйҮҚиҰҒгҖӮдёӯеӣҪзҡ„еҹҺеёӮеҢ–еҸ‘еұ•пјҢеҰӮеҗҢдё–з•Ңеҗ„еӣҪзҡ„еҹҺеёӮеҢ–дёҖж ·пјҢиҰҒиғҪдёҺеҪ“ең°зҡ„йңҖжұӮе’Ңж–ҮеҢ–зӣёиһҚеҗҲгҖӮдёӯеӣҪеңЁеҹҺеёӮ规еҲ’е’Ңи®ҫи®Ўж–№йқўжӯЈйқўдёҙеүҚжүҖжңӘжңүзҡ„жңәйҒҮпјҢдёҖж–№йқўиҰҒдёҺдёӯеӣҪжӮ д№…иҖҢзӢ¬зү№зҡ„дј з»ҹдҝқжҢҒе’Ңи°җпјҢеҸҰдёҖж–№йқўд№ҹиҰҒдёҺеҸҜжҢҒз»ӯеҸ‘еұ•зҡ„йңҖжұӮзӣёдёҖиҮҙгҖӮвҖқ
вҖңйҮҚе»әеҪ“д»ЈдёӯеӣҪжң¬еңҹе»әзӯ‘иүәжңҜеӯҰвҖқжҳҜзҺӢжҫҚз§үжҢҒзҡ„еӯҰжңҜзҗҶеҝөпјҢдҪңдёәжҳҜдёӯеӣҪжң¬еңҹе»әзӯ‘иҝҗеҠЁзҡ„д»ЈиЎЁдәәзү©пјҢд»–еқҡе®Ҳе»әзӯ‘зҗҶжғігҖӮйқўеҜ№е…ЁзҗғеҢ–жөӘжҪ®дёӢзҡ„еҹҺд№Ўе»әзӯ‘йЈҺж ји¶ӢеҗҢеҢ–зҺ°иұЎпјҢд»–д»ҘеҜ№иҘҝж–№зҺ°д»ЈеҹҺеёӮеҸҠе»әзӯ‘и§Ӯеҝөзҡ„еҸҚжҖқдёәзҗҶи®әиғҢжҷҜпјҢжү№еҲӨжҖ§ең°еӣһеҪ’ең°еҹҹе»әзӯ‘дј з»ҹгҖӮзҺӢжҫҚиҜҙпјҡвҖңеңЁеҪ“д»Ҡдё–з•ҢпјҢдәә们зғӯиЎ·дәҺи°Ҳи®ә科еӯҰгҖҒжҠҖжңҜгҖҒз”өи„‘пјҢжҲ‘еҲҷе–ңж¬ўи°Ҳи®әеҹәдәҺжүӢз»ҳе’ҢжүӢе·Ҙиүәд№ӢдёҠзҡ„е»әзӯ‘гҖӮвҖқд»–зҡ„еқҡжҢҒдёәд»–еёҰжқҘдәҶдё–з•Ңзә§зҡ„иҚЈиӘүгҖӮ
жҷ®еҲ©е…№е…Ӣе»әзӯ‘еҘ–иҜ„委дјҡдё»еёӯеё•дјҰеҚҡеӢӢзҲөиҜҙжҳҺдәҶзҺӢжҫҚиҺ·еҘ–зҡ„зҗҶз”ұпјҡвҖңи®Ёи®әиҝҮеҺ»дёҺзҺ°еңЁд№Ӣй—ҙзҡ„йҖӮеҪ“е…ізі»жҳҜдёҖдёӘеҪ“д»Ҡе…ій”®зҡ„й—®йўҳпјҢеӣ дёәдёӯеӣҪеҪ“д»Ҡзҡ„еҹҺеёӮеҢ–иҝӣзЁӢжӯЈеңЁеј•еҸ‘дёҖеңәе…ідәҺе»әзӯ‘еә”еҪ“еҹәдәҺдј з»ҹиҝҳжҳҜеҸӘеә”йқўеҗ‘жңӘжқҘзҡ„и®Ёи®әгҖӮжӯЈеҰӮжүҖжңүдјҹеӨ§зҡ„е»әзӯ‘дёҖж ·пјҢзҺӢжҫҚзҡ„дҪңе“ҒиғҪеӨҹи¶…и¶Ҡдәүи®әпјҢ并演еҢ–жҲҗжүҺж №дәҺе…¶еҺҶеҸІиғҢжҷҜгҖҒж°ёдёҚиҝҮж—¶з”ҡиҮіе…·дё–з•ҢжҖ§зҡ„е»әзӯ‘гҖӮвҖқ
зҺӢжҫҚпјҡжӢ’з»қжҪ®жөҒ
вҖңеҫҲеҘҮжҖӘпјҢеҪ“дҪ зңҹжӯЈиө°дёҠдёҖжқЎзӢ¬еҲӣзҡ„йҒ“и·Ҝж—¶пјҢдҪ дјҡеҸ‘зҺ°иҮӘе·ұиҝӣе…ҘдәҶдёҖдёӘж— з«һдәүзҡ„еёӮеңәгҖӮеҫҲеӨҡйЎ№зӣ®ж‘ҶеңЁйқўеүҚзӯүзқҖдҪ жҢ‘йҖүгҖӮвҖқиҺ·еҘ–еҗҺпјҢзҺӢжҫҚиҝҷж ·иҜ„д»·иҮӘе·ұзҡ„жҲҗеҠҹпјҢвҖңеҪ“дёҖдәӣдәәйҮҚж–°иҖғиҷ‘иҰҒдёҚиҰҒиө°жҲ‘иҝҷжқЎйҒ“и·Ҝж—¶пјҢжҲ‘е·Із»ҸйӘ‘зқҖдёҖеҢ№еҝ«й©¬з»қе°ҳиҖҢеҺ»пјҢеҸӘз•ҷдёӢдёҖеӣўзғҹе°ҳгҖӮвҖқ
дәәиҰҒиҝҮжңүдҝЎеҝөзҡ„з”ҹжҙ»
дҪҚдәҺжқӯе·һиҪ¬еЎҳзҡ„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иұЎеұұж ЎеҢәпјҢжҳҜзҺӢжҫҚжңҖи‘—еҗҚзҡ„д»ЈиЎЁдҪңд№ӢдёҖгҖӮжҢүз…§дј з»ҹи§ӮеҝөпјҢиҝҷйҮҢеә”иҜҘжІЎжңүд»Җд№Ҳи®ҫи®ЎпјҢеӣ дёә50%зҡ„еңҹең°жІЎжңүд»»дҪ•е»әзӯ‘пјҢе…ЁйғЁжҳҜж°ҙжё гҖҒз”°ең°гҖҒиҚүжңЁдёӣз”ҹзҡ„е°ҸеұұпјҢжҲҝеӯҗд»…д»…жҳҜзҺҜеўғдёӯзҡ„ж¬ЎиҰҒеӣ зҙ гҖӮдҪҶиҝҲиҝӣиҝҷйҮҢпјҢйЎҝж„ҹйқ’з“ҰзҷҪеўҷй—ҙжөҒйңІеҮәд№ҰйҷўиҲ¬зҡ„еҸӨйӣ…ж°”жҒҜгҖӮиҖҢиҝңзҰ»дёҖжӯҘпјҢжҲҝеұӢеҸҲдёҺзҺҜеўғиһҚдёәдёҖдҪ“пјҢеҰӮеӨ©дҪңд№ӢеҗҲгҖӮ
иұЎеұұж ЎеҢәе·ҘзЁӢиў«еҲҶжҲҗдёӨжңҹпјҢеҲҶйҳ¶ж®өе®ҢжҲҗгҖӮзҺӢжҫҚеӣһеҝҶпјҢз»ҳеҲ¶дәҢжңҹзҡ„еӣҫзәёеүҚпјҢи„‘еӯҗйҮҢж•ҙеӨ©йғҪеғҸеңЁвҖңиҝҮз”өеҪұвҖқпјҢеҗ„дёӘз»ҶиҠӮеҸҳжҲҗдёҖдёӘдёӘеҲҶй•ңеӨҙпјҢиҝҷж ·иҝҮдәҶдёүдёӘжңҲз”өеҪұпјҢд»–жңҖз»ҲеҸӘз”Ё4дёӘе°Ҹж—¶е°ұжҠҠж•ҙе№…иҚүеӣҫдёҖж°”е‘өжҲҗгҖӮз”»еӣҫж—¶пјҢд»–д№ҹжІЎжңүеҖҹеҠ©д»»дҪ•з”өи„‘иҪҜ件пјҢиҖҢжҳҜжҢүз…§дёӯеӣҪдј з»ҹз»ҳз”»ж–№жі•жүӢе·ҘдҪңдёҡпјҢд»ҺдёҠеҲ°дёӢгҖҒд»Һе·ҰеҲ°еҸігҖӮд»–иҮӘз§°иҝҷеҘ—е·ҘдҪңжөҒзЁӢжҳҜвҖңиғёжңүжҲҗз«№жі•вҖқгҖӮ
ж—¶дёҚж—¶еҶ’еҮәдёҖдәӣйЎҪеҝөзҡ„зҺӢжҫҚиҝҳж•…ж„ҸеңЁж ЎеӣӯйҮҢйҖ дәҶдёҖе№…вҖңз”»вҖқгҖӮдёҖеӨ©пјҢдёӯеӣҪзҫҺйҷўйҷўй•ҝи®ёжұҹз«ҷеңЁ3еҸ·жҘјж•°зұій«ҳзҡ„й—ЁжҙһеүҚеҫҖеӨ–зңӢпјҢзӘҒ然иҜҙпјҡвҖңе’ҰпјҢиҝҷдёҚжҳҜиҢғе®Ҫзҡ„гҖҠжәӘеұұиЎҢж—…еӣҫгҖӢд№Ҳ?вҖқ
зҺӢжҫҚеёҰзқҖеӯ©з«ҘжҒ¶дҪңеү§иў«еҸ‘зҺ°иҲ¬зҡ„жғҠе–ңзӯ”пјҡвҖңдҪ еҸ‘зҺ°дәҶ?вҖқ
еҪ“еҗ„з§ҚеӯҰж ЎгҖҒеҶҷеӯ—жҘјгҖҒе…¬еҜ“жү“зқҖвҖңдәәжҖ§еҢ–вҖқзҡ„е№Ңеӯҗе»әйҖ еҘўеҚҺж—¶пјҢиұЎеұұж ЎеҢәеҚҙеҸҚе…¶йҒ“иҖҢиЎҢпјҢдёҚд»…жҲҗжң¬дҪҺе»үвҖ”вҖ”еҸӘеҸҠжҷ®йҖҡеӨ§еӯҰж ЎеӣӯйҖ д»·зҡ„дёҖеҚҠвҖ”вҖ”е°ұиҝһз”өжўҜгҖҒз©әи°ғиҝҷж ·зҡ„зҺ°д»ЈеҢ–вҖңеҝ…йңҖе“ҒвҖқд№ҹиў«йҷҗеҲ¶дҪҝз”ЁпјҢжҜҸж ӢжҘјйҮҢеҸӘжңүдёҖе°Ҹеқ—ең°ж–№и®ҫжңүз©әи°ғпјҢд»Ҙдҫӣдәә们йңҖиҰҒж—¶дҪҝз”ЁгҖӮ
вҖңдәәиҰҒиҝҮдёҖз§ҚжңүзҗҶеҝөгҖҒжңүдҝЎеҝөзҡ„з”ҹжҙ»гҖӮвҖқзҺӢжҫҚи§ЈйҮҠгҖӮ
е»әзӯ‘з•Ңдёӯжңүдәәи®ӨдёәпјҢиҚ·е…°е»әзӯ‘еёҲйӣ·е§ҶВ·еә“е“Ҳж–Ҝзҡ„еӨ®и§Ҷж–°еӨ§жҘје’ҢзҺӢжҫҚзҡ„иұЎеұұж ЎеҢәжҳҜеҹҺеёӮе»әзӯ‘зҡ„дёӨдёӘжһҒз«ҜпјҢеҲҶеҲ«д»ЈиЎЁдәҶзҺ°д»ЈдёҺдј з»ҹдёӨз§ҚеҸ‘еұ•ж–№еҗ‘гҖӮ然иҖҢпјҢжҷ®еҲ©е…№е…ӢеҘ–зҡ„иҜ„е®ЎиҫһдёӯеҚҙеҶҷйҒ“пјҡзҺӢжҫҚзҡ„дҪңе“Ғ已然超и¶ҠдәҶдёӯеӣҪеҹҺеёӮе»әзӯ‘вҖңеә”еҪ“еҹәдәҺдј з»ҹиҝҳжҳҜеә”еҪ“йқўеҗ‘жңӘжқҘвҖқзҡ„дәүи®әпјҢе®ғе”Өиө·дәҶ вҖңеңәжҷҜдёҺеӣһеҝҶд№Ӣй—ҙзҡ„е…ұйёЈвҖқгҖӮ
еҜ№жӯӨпјҢжңүдёҖдёӘи®©зҺӢжҫҚжҙҘжҙҘд№җйҒ“зҡ„ж•…дәӢпјҡдёҖдҪҚиҖҒеҘ¶еҘ¶4ж¬ЎжқҘеҲ°д»–и®ҫи®Ўзҡ„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пјҢдёҚдёәзңӢеұ•и§ҲпјҢеҸӘдёәеҜ»жүҫжӣҫз»Ҹзҡ„вҖң家вҖқзҡ„еҪұеӯҗгҖӮ
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жүҖеңЁең°пјҢеҺҹжңү30дёӘе°Ҹжқ‘еӯҗпјҢ然иҖҢйҡҸзқҖйҷ„иҝ‘дёҖеӨ„иў«з§°дёәвҖңе°Ҹжӣје“ҲйЎҝвҖқзҡ„е•ҶдёҡеҢәе»әи®ҫпјҢиҝҷдәӣжқ‘иҗҪйҷҶз»ӯйғҪиў«жӢҶжҜҒгҖӮзҺӢжҫҚеңЁи®ҫи®Ўе’Ңе»әйҖ 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ж—¶пјҢжңүж„ҸиҜҶең°дҪҝз”ЁдәҶи®ёеӨҡиҝҷдәӣиҖҒжқ‘иҗҪжӢҶжҜҒеҗҺ收йӣҶеҲ°зҡ„ж—§жқҗж–ҷпјҢ并еҲ»ж„ҸжҠҠе®ғ们е‘ҲзҺ°еҮәжқҘпјҢжӢјз ҢжҲҗеҗҺжқҘйўҮиҙҹзӣӣеҗҚзҡ„вҖңз“ҰзҲҝеўҷвҖқгҖӮ
иҝҷдҪҝеҫ—еҜ№и®ёеӨҡдәәжқҘиҜҙпјҢ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жҲҗдәҶдёҖеә§еӣһеҝҶд№ӢеҹҺпјҢеҖҫжіЁдәҶзҺӢжҫҚеҝғзӣ®дёӯвҖңеҜ№ж—¶й—ҙзҡ„иҜ—ж„ҸдҪ“дјҡвҖқгҖӮеҚҡзү©йҰҶжңҖеҲқе»әжҲҗйҳ¶ж®өпјҢд»–жңүж—¶д№ҹдјҡжқҘеҲ°иҝҷйҮҢпјҢзңӢзқҖйӮЈдәӣжӣҫеңЁиҝҷйҮҢеұ…дҪҸиҝҮзҡ„дәә们пјҢжү¶иҖҒжҗәе№јең°еүҚжқҘпјҢеҜ№зқҖеҚҡзү©йҰҶжҢҮжҢҮзӮ№зӮ№пјҡйӮЈдёҖеқ—и·ҹжҲ‘家еҺҹжқҘзҡ„еўҷдёҖдёӘж ·гҖӮ
иҝ‘еҚҒе№ҙжқҘпјҢзҺӢжҫҚж— ж•°ж¬Ўж„ҹж…ЁиҮӘе·ұиә«еӨ„зҡ„иҝҷдёӘеҸӨиҖҒеӣҪеәҰе·Іиў«жӢҶеҫ—йқўзӣ®е…ЁйқһгҖҒдё§еӨұдәҶи®°еҝҶпјҢд»–дёҚж•ўжғіиұЎпјҢз…§иҝҷдёӘйҖҹеәҰжӢҶдёӢеҺ»пјҢжңӘжқҘзҡ„дёӯеӣҪд»Җд№Ҳж ·?
вҖңеҶҚиҝҮ10е№ҙпјҢжҲ‘们жҒҗжҖ•е°ұжІЎи„ёиҜҙиҮӘе·ұз”ҹжҙ»еңЁдёӯеӣҪдәҶгҖӮзңҹжӯЈеӯҳеңЁдәҺз”ҹжҙ»дёӯзҡ„е®һзү©йғҪдёҚеңЁдәҶпјҢдҪ еҮӯд»Җд№ҲиҜҙиҮӘе·ұиҝҳеңЁдёӯеӣҪ?вҖқзҺӢжҫҚиҜҙпјҢвҖңеҰӮжһңз”ҹжҙ»йҮҢзңҹе®һзҡ„дёңиҘҝйғҪжІЎжңүдәҶпјҢжҲ‘们жҙ»зқҖзҡ„иҖҒеёҲе°ұе·Із»Ҹжӯ»е…үдәҶгҖӮвҖқ
他并дёҚи®ӨеҸҜйӮЈдәӣе°ҒеӯҳеңЁеҚҡзү©йҰҶзҺ»з’ғзҪ©еӯҗйҮҢзҡ„вҖңдј з»ҹвҖқпјҢйӮЈдәӣеҸӘжҳҜдј з»ҹжӣҫз»ҸеӯҳеңЁиҝҮзҡ„иҜҒжҚ®гҖӮвҖңдј з»ҹдёҖе®ҡжҳҜжҙ»зқҖзҡ„вҖқпјҢд»–иҜҙпјҢвҖңиҖҢдё”дёҖж—Ұиў«еҲҮж–ӯе°ұеҫҲйҡҫеҶҚжүҝз»ӯгҖӮвҖқ
е»әзӯ‘еёҲйҰ–е…ҲиҰҒжҳҜдёӘе“Ідәә
иҝҷз§ҚеҜ№дј з»ҹзҡ„еҗ‘еҫҖпјҢжҲ–и®ёеҸҜд»ҘиҝҪжәҜеҫ—жӣҙд№…гҖӮ
зҺӢжҫҚзҡ„з«Ҙе№ҙжӯЈеҘҪиө¶дёҠж–Үйқ©гҖӮеҲ«зҡ„еӯ©еӯҗйғҪи·‘еҮәеҺ»вҖңеҒңиҜҫй—№йқ©е‘ҪвҖқпјҢеҸӘжңүд»–пјҢеҖҹзқҖжҜҚдәІжҳҜеӣҫд№Ұз®ЎзҗҶе‘ҳзҡ„дҫҝеҲ©пјҢзҝ»йҒҚдәҶеҮ д№ҺжүҖжңүиў«иҜ‘жҲҗдёӯж–Үзҡ„дё–з•ҢеҗҚи‘—гҖӮиҝҷи®©д»–жҜ”еҲ«зҡ„еӯ©еӯҗж—©зҶҹеҫҲеӨҡпјҢ并йҖҗжёҗдә§з”ҹеҜ№еҗҢйҫ„дәәзҡ„з–ҸзҰ»ж„ҹгҖӮ
еңЁеҚ—дә¬е·ҘеӯҰйҷў(зҺ°дёңеҚ—еӨ§еӯҰ)е»әзӯ‘зі»иҜ»еӨ§дәҢж—¶пјҢд»–е°ұе…¬ејҖе®Јз§°вҖңжІЎдәәеҸҜд»Ҙж•ҷжҲ‘дәҶвҖқ;еӨ§дёүж—¶жӢ’з»қз”»е•Ҷдёҡж•ҲжһңеӣҫпјҢиҝҳеёҰзқҖеҗҢеӯҰеҲ°ж•ҷз ”е®Өи°ҲеҲӨгҖӮзҺ°еңЁеӣһжғіиө·жқҘпјҢд»–иҝҳжңүеҮ еҲҶеҫ—ж„ҸпјҡвҖңе…ідәҺиҮӘз”ұиЎЁиҫҫпјҢйӮЈеҸҜжҳҜиҝҷжүҖеӯҰж Ў70еӨҡе№ҙеҺҶеҸІдёҠ第дёҖж¬ЎејҖзҰҒгҖӮвҖқ
еҲ«дәәзқЎеҚҲи§үпјҢд»–з»ғжҜӣ笔еӯ—;еҲ«дәәеңЁж•ҷе®ӨдёҠиҜҫпјҢд»–еҺ»еӣҫд№ҰйҰҶиҮӘд№ ;еҲ«дәәз ”з©¶еҗҺзҺ°д»Јдё»д№үе»әзӯ‘пјҢд»–еӣӣеӨ„еҜ»и§…еҗҺзҺ°д»Јдё»д№үз”өеҪұгҖҒеҗҺзҺ°д»Јдё»д№үж–ҮеӯҰгҖӮ
д»–иҝҳиҝҪзқҖжІҲд»Һж–ҮгҖҠж№ҳиЎҢж•Ји®°гҖӢзҡ„и„ҡжӯҘиө°дәҶ3дёӘжңҲпјҢдҪҶж—…иЎҢдёӯж—ўдёҚз»ҷжҲҝеӯҗз…§зӣёгҖҒд№ҹдёҚжҗһеңҹең°жөӢйҮҸпјҢжІЎжңүдёҖзӮ№е»әзӯ‘еёҲзҡ„ж ·еӯҗгҖӮ20еӨҡе№ҙиҝҮеҺ»дәҶпјҢд»–еҚ°иұЎжңҖж·ұзҡ„жҳҜдёҖдёӘеҸ«еҒҡйқ’жөӘж»©зҡ„е°Ҹжқ‘пјҢжқ‘е°Ҹзҡ„иҖҒеёҲе°ұзқҖеӨңиүІдё“зЁӢжқҘжӢңдјҡиҝҷдҪҚдј иҜҙдёӯзҡ„еӨ§еӯҰз”ҹгҖӮвҖңиҒҠеҫ—д»Җд№ҲдёҚи®°еҫ—дәҶпјҢеҸӘи®°еҫ—йӮЈйҮҢжІЎзҒҜпјҢдёҖдёӘдәәеҗ№зқҖеҸЈзҗҙдёҖи·ҜиёҸжӯҢиҖҢжқҘгҖӮвҖқ
дёҠдәҶз ”з©¶з”ҹпјҢеҗҢеӯҰ们зӢӮиҜ»иҘҝеӯҰж—¶пјҢзҺӢжҫҚеҚҙеҶҷеҮәдёҖзҜҮгҖҠеҪ“д»ЈдёӯеӣҪе»әзӯ‘еӯҰеҚұжңәгҖӢпјҢејәзғҲжү№еҲӨдёӯеӣҪе»әзӯ‘з•Ң100е№ҙжқҘе§Ӣз»ҲжІЎиғҪеҪўжҲҗдёҖиӮЎеҜ№дј з»ҹзҡ„继жүҝдёҺеҸ‘еұ•зҡ„йЈҺж°”гҖӮд»…жү№еҲӨзӨҫдјҡеӨ§зҺҜеўғпјҢд»–и§үеҫ—йҡҫд»ҘеҲ°дҪҚпјҢе°ұжӢҝеӨ§еёҲ们дёӢжүӢпјҢд»ҺжўҒжҖқжҲҗеҲ°иҮӘе·ұзҡ„еҜјеёҲйҪҗеә·пјҢдёҡеҶ…жңүеҮ еҲҶеҗҚж°”дәәзү©еҮ д№ҺйғҪи®©д»–ж•°иҗҪдёӘйҒҚгҖӮ
д»–д»ҘйҷҖжҖқеҰҘиҖ¶еӨ«ж–Ҝеҹәзҡ„е°ҸиҜҙдёәзЎ•еЈ«и®әж–Үе‘ҪеҗҚпјҡгҖҠжӯ»еұӢжүӢи®°гҖӢгҖӮзӯ”иҫ©еүҚпјҢиҝҳзү№ж„ҸеңЁж•ҷе®ӨйҮҢжҢӮдәҶиҮӘе·ұеҲӣдҪңзҡ„е·Ёе№…й»‘зҷҪжҠҪиұЎдҪңе“ҒгҖӮи®әж–ҮиҷҪе…ЁзҘЁйҖҡиҝҮпјҢеҚҙеӣ е…¶иЁҖиЎҢвҖңзӢӮеҰ„вҖқпјҢеӯҰж ЎжңӘжҺҲдәҲе…¶зЎ•еЈ«еӯҰдҪҚгҖӮдҪҶйӣӘи—ҸеңЁдёңеҚ—еӨ§еӯҰйҳ…и§Ҳе®Өзҡ„и®әж–ҮеүҜжң¬пјҢжІЎиҝҮеҮ е№ҙе°ұиў«еӯҰејҹеӯҰеҰ№д»¬зҝ»зғӮдәҶгҖӮжңүдәәиҜҙе®ғеғҸдёӘеҜ“иЁҖпјҢеүҚзһ»дәҶдёӯеӣҪе»әзӯ‘з•ҢжңӘжқҘзҡ„20е№ҙгҖӮ
20е№ҙеҗҺпјҢзҺӢжҫҚд»ҺеӯҰз”ҹеҸҳжҲҗдәҶиҖҒеёҲпјҢ并дҫқ然дҝқжҢҒдәҶеӯҰз”ҹж—¶д»Јзҡ„вҖңеҸҰзұ»вҖқгҖӮеңЁд»–зҡ„еёҰйўҶдёӢпјҢдёӯеӣҪзҫҺйҷўе»әзӯ‘иүәжңҜеӯҰйҷўзҡ„еӯҰз”ҹпјҢиҰҒд»Һй”ҜжңЁгҖҒжҢ–еңҹгҖҒз ҢеўҷеӯҰиө·пјҢдә”е№ҙжң¬з§‘еӯҰд№ зҡ„йҮҚиҰҒзӣ®ж ҮжҳҜйҖҗжӯҘжҺҢжҸЎжҲҗдёәдёҖеҗҚе·ҘеҢ зҡ„иғҪеҠӣгҖӮиұЎеұұж ЎеҢә15еҸ·жҘјзҡ„еӨ©дә•йҮҢжңүдёҖе өзҹ©еҪўзҡ„еўҷпјҢжҜҸе№ҙйғҪжҳҜдёҠдёҖжӢЁеӯҰз”ҹз Ңе®ҢпјҢдёӢдёҖжӢЁеӯҰз”ҹеҶҚжҺЁеҖ’йҮҚз ҢгҖӮ
еӨ§дёҖж–°з”ҹеҲҡе…ҘеӯҰпјҢе°ұиҰҒдәІжүӢи®ҫ计并еҲ¶дҪңдёҖдёӘ1:2еӨ§е°Ҹзҡ„жңЁеҮігҖӮйӮЈдәӣеңЁе®¶йҮҢиҝһеҖ’ејҖж°ҙйғҪдёҚдјҡзҡ„еӯҰз”ҹпјҢеҲ°дәҶиҝҷйҮҢз…§ж ·иҰҒжӢҝиө·й”үеҲҖй”ҜжқЎгҖӮжңүзҡ„еӯ©еӯҗдёҠиҜҫж—¶жҠҠжүӢдёҠеҲ’зҡ„е…ЁжҳҜе°ҸеҸЈпјҢдҫқ然е…ҙиҮҙдёҚеҮҸгҖӮдёҠеӯҰжңҹжң«пјҢеҘҪеҮ дёӘеӯҰз”ҹжӢҝзқҖиҮӘе·ұжү“йҖ зҡ„1:1еӨ§е°Ҹзҡ„жңЁеҮіпјҢе…ҙеҘӢең°жүҫеҲ°жңЁе·ҘиҜҫиҖҒеёҲйҷҶж–Үе®Ү(зҺӢжҫҚзҡ„еӨ«дәә)пјҡйҷҶиҖҒеёҲйҷҶиҖҒеёҲпјҢдҪ еҝ«иҝҮжқҘеқҗеқҗгҖӮйҷҶж–Үе®ҮеҫҖдёҠдёҖеқҗпјҢвҖңдёҚй”ҷпјҢжІЎеҖ’вҖқгҖӮ
еңЁзҺӢжҫҚзңӢжқҘпјҢиҝҷ并дёҚжҳҜд»Ҙеҹ№е…»е·ҘеҢ зҡ„ж ҮеҮҶжқҘеҹ№е…»е»әзӯ‘еёҲпјҢзӣёеҸҚпјҢжӯЈеҰӮдҪңжӣІе®¶йңҖеҜ№еҷЁд№җйҹіиүІе’Ңжј”еҘҸжҠҖе·§еЁҙзҶҹжҺҢжҸЎеҗҺж–№иғҪи°ұеҮәеҗҚжӣІпјҢиғҪеӨҹеҜ№е»әзӯ‘жқҗж–ҷе’Ңе»әйҖ ж–№жі•дҝЎжүӢжӢҲжқҘпјҢжӯЈжҳҜжҲҗдёәдёҖеҗҚдјҳз§Җе»әзӯ‘еёҲзҡ„еҹәзЎҖгҖӮе°‘дәҶиҝҷдёӨж–№йқўзҡ„зҹҘиҜҶпјҢеҶҚеҘҪзҡ„еҲӣж„Ҹд№ҹдјҡеңЁе®һи·өиҝҮзЁӢдёӯеӨ§жү“жҠҳжүЈгҖӮ
дёәдәҶејҖйҳ”и§ҶйҮҺпјҢзҺӢжҫҚиҝҳз»ҸеёёйӮҖиҜ·еӨ–еӣҪе»әзӯ‘专家жқҘеӯҰж ЎдёҠиҜҫпјҢ专家дёҺдё»йўҳжҜҸе№ҙдёҚеҗҢгҖӮжҜ”еҰӮ2011-2012еӯҰе№ҙпјҢз”ҹеңҹз ”з©¶ж–№йқўзҡ„еӣҪйҷ…жқғеЁҒгҖҒжі•еӣҪеҚЎд»Јз ”究дёӯеҝғжҙҫеҮәдёӨеҗҚз ”з©¶дәәе‘ҳеёҰзқҖдёҖж•ҙеҘ—е®һйӘҢи®ҫеӨҮжқҘеҲ°иұЎеұұпјҢдёәз ”з©¶з”ҹи®ІжҺҲвҖңеңҹеЈӨзҡ„жүӢе·Ҙйүҙе®ҡж–№жі•вҖқпјҢи‘—еҗҚзҡ„зҫҺеӣҪзҪ—еҫ·еІӣи®ҫи®ЎеӯҰйҷўд№ҹйҖҒеҮәеёҲиө„пјҢдёҺжң¬з§‘з”ҹжҺўи®Ёж°”еҖҷеҜ№е»әзӯ‘иҗҘйҖ зҡ„еҪұе“ҚгҖӮ
еӯҰз”ҹ们зңјдёӯзҡ„зҺӢжҫҚејҸж•ҷеӯҰпјҢеӨҡйқ дёҖиҜӯзӮ№жӢЁгҖҒеҪ“еӨҙжЈ’е–қ帮他们вҖңеӨ§еҪ»еӨ§жӮҹвҖқпјҢиҖҢйқһдҪ и®ІжҲ‘еҗ¬зҡ„еЎ«йёӯејҸзҒҢиҫ“гҖӮ
жқӯе·һеёӮ规еҲ’еұҖ规еҲ’еӨ„еӨ„й•ҝз« е»әжҳҺжҳҜзҺӢжҫҚеҚҡеЈ«з”ҹдёӯзҡ„ејҖеұұејҹеӯҗпјҢиҜ»д№Ұж—¶з»Ҹеёёи·ҹйҡҸвҖңеёҲзҲ¶вҖқеҮәй—ЁдјҡеҸӢпјҢз»ҳз”»гҖҒд№Ұжі•гҖҒйҹіеҫӢгҖҒиҢ¶йҒ“пјҢиҒҡдјҡдё»йўҳж— жүҖдёҚеҢ…гҖӮдёҖж¬ЎпјҢд»–д»Һз«№з¬ӣзҡ„йҹіиүІдёӯж„ҹеҸ—еҮәдёҖз§Қиҝңиҝ‘дәІз–Ҹзҡ„е·®ејӮж„ҹпјҢ并е°Ҷиҝҷз§Қж„ҹеҸ—е‘ҠиҜүдәҶзҺӢжҫҚгҖӮжІЎжғідёҚд№…еҗҺпјҢеңЁдёҖж¬ЎиҜ„еӣҫи®Ёи®әж—¶пјҢзҺӢжҫҚжҢҮеј•д»–пјҡиҝҳи®°еҫ—дёҠж¬ЎдҪ еҜ№з«№еӯҗзҡ„дҪ“дјҡеҗ—?еҒҡе»әзӯ‘е°ұиҰҒжҠҠиҝҷз§Қзү№иҙЁе’Ңе®ғзҡ„е“Ғж јиЎЁзҺ°еҮәжқҘгҖӮ
зҺӢжҫҚжҳҜеңЁеҠӣеӣҫжҒўеӨҚдёҖз§ҚвҖңжғіиұЎдёӯзҡ„вҖқдј з»ҹе»әзӯ‘ж•ҷеӯҰпјҢеӣ дёәдёӯеӣҪеҸӨд»Јж №жң¬дёҚеӯҳеңЁжүҖи°“зҡ„вҖңе»әзӯ‘ж•ҷиӮІвҖқгҖӮиҖҢеңЁд»–зңӢжқҘпјҢдёҖдёӘе»әзӯ‘еёҲйҰ–е…ҲиҰҒжңүжҹҗз§ҚдёҖд»ҘиҙҜд№Ӣзҡ„жҖқжғіпјҢ然еҗҺдёҚж–ӯз”Ёе»әзӯ‘еҺ»иЎЁиҫҫгҖӮжүҖд»ҘпјҢжҲҗдёәеҘҪзҡ„е»әзӯ‘еёҲд№ӢеүҚпјҢйҰ–е…Ҳеә”еҪ“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вҖңе“ІдәәвҖқгҖӮ
зҺӢжҫҚдҪңе“Ғпјҡдә”ж•ЈжҲҝ

вҖңдә”ж•ЈжҲҝвҖқ еҲҶеҲ«ж•ЈеёғдәҺй„һе·һе…¬еӣӯеҗ„еӨ„пјҢе®ғ们жңүзқҖиүәжңҜзҡ„жҰӮеҝөпјҢеҚҙдёҚеҘўеҚҺпјҢеңЁдёҖдёӘе№ҝиўӨзҡ„з”°йҮҺйҮҢдә§з”ҹпјҢеҚҙдёҺеҹҺеёӮиҙҙеҲҮең°дәӨиһҚеңЁдёҖиө·гҖӮе®ғ们з”ұ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е»әзӯ‘зі»дё»д»»гҖҒи‘—еҗҚи®ҫи®ЎеёҲ зҺӢжҫҚи®ҫи®ЎжүҖеҪўжҲҗзҡ„вҖңдә”ж•ЈжҲҝвҖқгҖӮеҪўжҲҗй—Іи¶ЈгҖҒйҡҸйҖӮзҡ„зҠ¶жҖҒпјҡдёҖеә§жҳҜз”»е»ҠпјҢдёҖеә§жҳҜе’–е•ЎеҺ…пјҢдёҖеә§жҳҜе…¬еӣӯз®ЎзҗҶз”ЁжҲҝпјҢдёӨеә§иҢ¶е®Өе»әзӯ‘гҖӮдә”еә§е»әзӯ‘йҮҮз”ЁдёҚеҗҢзҡ„жҠҖжңҜжүӢж®өпјҢдёҚеҗҢзҡ„ ең°ж–№жқҗж–ҷпјҢдёҚеҗҢзҡ„е»әйҖ жҠҖжңҜпјҢеңЁе…¬еӣӯеҶ…иҗҘйҖ еҮәдёҚеҗҢжҷҜи§Ӯе»әзӯ‘зҡ„зү№жҖ§гҖӮиҝҷвҖңдә”ж•ЈжҲҝвҖқдёҚдј з»ҹзҡ„еӣӯжһ—е»әзӯ‘пјҢеҚҙи®©еёӮж°‘еј•еҸ‘дәҶеҜ№дј з»ҹе…ғзҙ гҖҒзҺ°д»Је»әзӯ‘жқҗж–ҷиЎЁзҺ°еҮәзҡ„еҗҺзҺ°д»ЈиүәжңҜжҰӮеҝөгҖӮ
вҖңдә”ж•ЈжҲҝжҳҜ5еӨ„е°Ҹе…¬е»әпјҢдёҖе…ұжүҚ2000е№іж–№зұігҖӮиҝҷзҡ„зЎ®жҳҜдёҖж¬Ўе°Ҹе®һйӘҢпјҢдёә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иұЎеұұж ЎеҢәдәҢжңҹйЎ№зӣ®з§ҜзҙҜдәҶеҫҲеӨҡе»әзӯ‘зұ»еһӢе’Ңе»әйҖ ж–№жі•дёҠзҡ„е®һйҷ…з»ҸйӘҢпјҢиҝҷд№ҹжҳҜжҲ‘们дёҡдҪҷе»әзӯ‘е·ҘдҪңе®Өзҡ„е·ҘдҪңж–№жі•гҖӮвҖқе»әзӯ‘еёҲзҺӢжҫҚиҜҙгҖӮ
жҚ®зҺӢд»Ӣз»ҚпјҢеҮ е№ҙеүҚпјҢдә”ж•ЈжҲҝеҲҶдёәиҢ¶е®ӨгҖҒз”»е»ҠгҖҒе’–е•ЎеҺ…гҖҒз®ЎзҗҶз”ЁжҲҝзӯүгҖӮеҲҶеҲ«з”ЁдәҶ5з§ҚдёҚеҗҢзҡ„е»әзӯ‘зұ»еһӢе’Ңе»әйҖ ж–№жі•гҖӮ
з”»е»ҠиғҢдёҳйқўж№–пјҢеұӢйЎ¶дёҖжіўдёүжҠҳпјҢжӘҗдёӢз©әй—ҙе…·жңүе…ёеһӢжұҹеҚ—е»әзӯ‘зҡ„ж°”еҖҷзү№еҫҒпјҢе»әзӯ‘еүҚеҗҺеҗ„и®ҫдёӨжқЎз ҫзҹіе№Ій“әеёҰпјҢеҸҜд»ҘдҪңгҖҒдёәжҲ·еӨ–зӣҶжҷҜзҡ„еұ•зӨәеңәең°пјӣе’–е•ЎеҺ…еұӢйқўең°йқўеқҮдёәжӣІйқўпјҢ жҹұеӯҗеҫ®еҫ®еҖҫж–ңпјҢжЎҢжӨ…еқҮж №жҚ®ең°йқўзҡ„еҸҳеҢ–зү№ж®Ҡи®ҫи®ЎпјӣиҢ¶е®ӨйҮҮз”ЁеҗҲйҷўеҪўжҖҒпјҢ6зұій«ҳзҡ„йҷўеӯҗдёӯеӣҙзқҖдёҖдёӘ3зұій«ҳзҡ„йқ’з –еҸ°пјҢз§ҚзқҖдёӨжЈөеӨ§ж ‘пјҢж ‘еҪұйҡҸйЈҺ移еҠЁпјӣеҸҰдёҖдёӘиҢ¶е®Өзҡ„еұӢйқў з”ұй’ўжһ„зҺ»з’ғе»әйҖ пјҢеҚ—йқўжңүдёҖе°ҸиҚ·еЎҳпјҢз»ҸдёҖе°ҸжЎҘзӣҙе…Ҙпјӣз®ЎзҗҶз”ЁжҲҝд»Ҙе№іеұӢйЎ¶з«Ӣж–№дҪ“е»әзӯ‘дёәеҺҹеһӢпјҢеұӢдёӯдәәеҸҜз©ҝи¶Ҡе»әзӯ‘дёҖзӣҙзңӢеҲ°ж№–йқўгҖӮвҖңдә”ж•ЈжҲҝвҖқжүҖйҮҮз”Ёзҡ„еўҷз –пјҢжңүзҡ„е®Ңж•ҙжңүзҡ„ж®ӢзјәпјҢжңүзҡ„еҺҡжңүзҡ„и–„пјҢжңүзҡ„йӣ•иҠұжңүзҡ„жІЎзә№пјҢжңүзҡ„е№ізӣҙжңүзҡ„еёҰеј§пјҢйғҪжҳҜд»ҺиҖҒжҲҝеӯҗдёӯжӢҶдёӢжқҘзҡ„еӣһ收еҲ©з”Ёз –пјҢиҖҢдё”йҮҮз”ЁдәҶжңҖдј з»ҹзҡ„еӨҜеңҹжҠҖжңҜгҖӮ
зҺӢжҫҚиЎЁзӨәпјҡвҖңи®ҫи®ЎвҖҳдә”ж•ЈжҲҝвҖҷпјҢеҪ“еҲқеҮәдәҺ3з§ҚиҖғиҷ‘гҖӮдёҖжҳҜеҰӮдҪ•еҒҡжүҚиғҪдҪ“зҺ°е…·жңүдёӯеӣҪж°”иҙЁзҡ„зҺ°д»Је»әзӯ‘пјӣдәҢжҳҜеҰӮдҪ•дёҚеұҖйҷҗдәҺйҖ жҲҝеӯҗжң¬иә«пјҢе’Ңеңәең°гҖҒзҺҜеўғжңүзү№ж®Ҡзҡ„й…ҚеҗҲпјӣеҸҰеӨ–пјҢиҝҳе°қиҜ•дәҶеҗ„з§ҚдёҚеҗҢзҡ„е»әйҖ ж–№жі•е’Ңе»әзӯ‘зұ»еһӢпјҢиӯ¬еҰӮз”ЁеӨҜеңҹжҠҖжңҜгҖҒй’ўжһ„зҺ»з’ғгҖҒйў„еҲ¶ж··еҮқеңҹзӯүдёҖдәӣдёӯеӣҪдј з»ҹзҡ„е»әйҖ ж–№жі•гҖӮе°ұеғҸжҳҜеҒҡ科еӯҰе®һйӘҢпјҢиҝҷдәӣе°Ҹе®һйӘҢеҗҺжқҘеңЁиұЎеұұж ЎеҢәдәҢжңҹйЎ№зӣ®дёӯйғҪжңүжүҖдҪ“зҺ°гҖӮвҖқ
вҖңдёӯеӣҪзҡ„е»әзӯ‘е·ҘдәәеӨҡе°‘еёҰжңүзӮ№дј з»ҹзҡ„жүӢе·ҘиүәпјҢдҪҶжҳҜзҺ°еңЁеҜ№дј з»ҹзҡ„еҒҡжі•еҸҚиҖҢз”ҹз–ҸдәҶпјҢеҫҲеӨҡжүӢе·ҘиүәдёҚз”ЁпјҢжүҖд»ҘйҖҖеҢ–пјҢиҝӣиҖҢиў«йҒ— еҝҳжҺүдәҶгҖӮжҲ‘们用дёҖдәӣе°Ҹзҡ„е®һйӘҢпјҢиҝӣиЎҢдәҶеӨ§и§„жЁЎзҡ„жҺЁе№ҝпјҢиұЎеұұж ЎеҢәдёҖе…ұжңү15дёҮеӨҡе№іж–№зұіпјҢйғҪдҪҝз”ЁдәҶдј з»ҹе·Ҙиүәе’Ңе»әйҖ ж–№жі•пјҢзӣ®зҡ„жҳҜдёәдәҶжҺЁе№ҝпјҢиҝҷж ·жүҚжңүд»·еҖјгҖӮдёӯеӣҪзҡ„жүӢ е·ҘиүәжҲҗжң¬зӣёеҜ№дҫҝе®ңпјҢдҪҶдј з»ҹе·ҘиүәеҸӘжңүиў«дҪҝз”ЁжүҚиғҪеӨҹ继жүҝдёӢжқҘгҖӮвҖқзҺӢжҫҚиҜҙгҖӮ
йҮҚжӢҫжҙ»зқҖзҡ„дј з»ҹ
дј жүҝдј з»ҹдёҚеҸӘйқ и®ҫи®ЎпјҢиҝҳиҰҒйқ е·ҘиүәпјҢе°Өе…¶жҳҜз”Ёж—§з –з“Ұе»әйҖ з“ҰзҲҝеўҷзҡ„е·ҘиүәжҠҖжі•гҖӮ
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жӯЈејҸејҖе·ҘеүҚпјҢзҺӢжҫҚеёҰзқҖе·ҘеҢ еҒҡдәҶдёҖйқўеҮ зҷҫе№іж–№зұізҡ„ж ·еўҷгҖӮеҸҜжҳҜпјҢзҺ°д»Је·ҘеҢ е“ӘиғҪжҺҢжҸЎеҮ еҚҒе№ҙжІЎдәәз”ЁиҝҮзҡ„иҖҒжүӢиүә?еҲҡејҖе§ӢпјҢе·ҘеҢ жҖ»жҢүиҮӘе·ұзҡ„жғіжі•жҸЈжөӢзҺӢжҫҚзҡ„ж„ҸеӣҫпјҢж”№дәҶеҸҲж”№пјҢиҝҳжҳҜдёҚеҜ№и·ҜеӯҗгҖӮе·ҘеҢ жҖҘдәҶпјҡвҖңзҺӢиҖҒеёҲпјҢдҪ еҲ°еә•жғіи®©жҲ‘们жҖҺд№ҲеҒҡе•Ҡ?е°ұеҒҡжҲҗжҲ‘们еҶңжқ‘家йҮҢйӮЈж ·иЎҢдёҚиЎҢ?вҖқвҖңе—іпјҢжҲ‘е°ұжҳҜжғіиҰҒдҪ 们еҒҡжҲҗйӮЈж ·гҖӮвҖқ
дёҖж¬ЎпјҢд»–еҮ еӨ©жІЎжқҘе·Ҙең°пјҢдёҖжқҘе°ұзңӢи§Ғе·ҘеҢ еңЁеўҷдёҠеғҸй“әз“·з –дёҖж ·пјҢе°Ҷз“ҰзүҮж•ҙйҪҗең°з Ңиө·дёҖеӨ§зүҮпјҢвҖңиҝҷдёӘдёҚеҜ№пјҢдҪ 们еҫ—жӢҶ!вҖқе·ҘдәәдёҖеҗ¬иҰҒеӨ§йқўз§Ҝиҝ”е·ҘпјҢзңјжіӘйғҪеҝ«еҮәжқҘдәҶгҖӮзҺӢжҫҚжғідәҶжғіпјҡвҖңиҝҷдёӘеҝ…йЎ»жӢҶпјҢдҪҶдёҚз”Ёе…ЁжӢҶпјҢжӢҶеҲ°жҲ‘иғҪе®№еҝҚзҡ„жңҖеӨ§йҷҗеәҰеҗ§гҖӮвҖқжңҖеҗҺпјҢдёҖеҚҠзҡ„вҖңз“·з –еўҷвҖқиў«дҪңдёәж ·жң¬дҝқз•ҷдёӢжқҘпјҢжҜҸеӨ©з«ӢеңЁйӮЈйҮҢпјҢд»ҘжңҖзӣҙи§Ӯзҡ„ж–№ејҸе‘ҠиҜүе·ҘеҢ пјҢйҖ жҲҗиҝҷж ·дёҚиЎҢгҖӮ
йҷӨдәҶ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пјҢиұЎеұұж ЎеҢәд№ҹеӨ§йҮҸиҝҗз”ЁдәҶз“ҰзҲҝеўҷе·ҘиүәгҖӮдёҖжңҹгҖҒдәҢжңҹеҠ иө·жқҘпјҢе…үеӣһ收жқҘзҡ„ж—§з –з“Ұе°ұи¶…иҝҮ700дёҮзүҮгҖӮиҝҷдәӣж—§жқҗж–ҷзҡ„д»·ж јжңҖж—©еҸӘжңүж–°жқҗж–ҷзҡ„1/10пјҢеҗҺжқҘж¶ЁеҲ°дёҖеҚҠпјҢзҺ°еңЁеӨ§жҰӮжҜ”ж–°жқҗж–ҷиҝҳиҰҒиҙөдәҶ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иҝ‘дёӨе№ҙеёӮйқўдёҠзҡ„ж—§жқҗж–ҷи¶ҠжқҘи¶Ҡе°‘пјҢзҺӢжҫҚеӨ«еҰҮи§үеҫ—жҳҜеҘҪдәӢпјҢвҖңиҮіе°‘иҜҙжҳҺзҺ°еңЁжҜ”еҺҹжқҘжӢҶеҫ—е°‘дәҶе‘ҖгҖӮвҖқ
йқўеҜ№е·ҘзЁӢдёӯйҡҫд»ҘйҒҝе…Қзҡ„е»әзӯ‘жӢҶиҝҒжҲ–ејӮең°дҝқжҠӨпјҢзҺӢжҫҚж·ұж„ҹж— еҘҲгҖӮд»–дёҚж— и®ҪеҲәең°жҠҠвҖңдҝқжҠӨжҖ§жӢҶиҝҒвҖқеҪўе®№дёәвҖңдёӯеӣҪдәәзҡ„еҲӣйҖ жҖ§вҖқгҖӮвҖңж•…е®«(еҫ®еҚҡ)дјҡдёҚдјҡд№ҹеңЁжҹҗдёҖеӨ©иў«ж•ҙдҪ“дҝқжҠӨжҖ§жӢҶиҝҒ?вҖқеҫ—еҘ–еҗҺеңЁдёҖж¬Ўе…¬ејҖеңәеҗҲпјҢд»–е°–еҲ»ең°иҜҙпјҡвҖңйӮЈйҮҢе®һеңЁжҳҜеҢ—дә¬еҹҺйҮҢжңҖеҘҪзҡ„ең°ж®өпјҢе•Ҷжңәж— йҷҗгҖӮвҖқ
зҺӢжҫҚи®ҫи®Ўзҡ„жҲҝеӯҗд№ҹдёҚе…ЁжҳҜж—§иҙ§пјҢд»–д№ҹдјҡеҜ№зҺ°д»Је»әзӯ‘жқҗж–ҷйҮҚж–°и§ЈиҜ»пјҢжҜ”еҰӮжҠҠжөҮжіЁж··еҮқеңҹж—¶з”Ёзҡ„з«№жқҝж”ҫеңЁз“ҰзүҮдёӢеҒҡж”Ҝж’‘пјҢжҲ–иҖ…пјҢж··еҮқеңҹжҲҝйЎ¶дёҠиҝҳиҰҶзқҖж—§з“ҰзүҮпјҢз“ҰеңЁиҝҷйҮҢжІЎжңүд»»дҪ•е®һйҷ…еҠҹз”ЁпјҢеҸӘжҳҜдёҖз§ҚеҜ№дј з»ҹзҡ„жј”з»ҺгҖӮ
д»”з»Ҷж¬ЈиөҸиҝҮзҺӢжҫҚзҡ„дҪңе“ҒпјҢдјҡеҸ‘зҺ°е®ғе®Ңе…ЁжҳҜдёҖз§Қж··жҗӯпјҢж–°ж—§жқҗж–ҷдёҖиө·дҪҝз”ЁпјҢиө·еҲ°зҡ„ж•Ҳжһңи®©дәәзңјеүҚдёәд№ӢдёҖдә®гҖӮвҖңдёҚиҝҮдҪ еҲ«жҠҠд»–жғіжҲҗдёҖдёӘеӨ©жүҚпјҢд»–еңЁиҮӘжҲ‘ж‘ёзҙўзҡ„иҝҮзЁӢдёӯд№ҹиө°иҝҮдёҚе°‘ејҜи·ҜгҖӮвҖқеҜ№зҺӢжҫҚз ”з©¶дәҶеӨҡе№ҙзҡ„еҸІе»әпјҢжҠҠд»–зҡ„жҲҗеҠҹеҪ’з»“дёәеҺҡз§Ҝи–„еҸ‘пјҢвҖңд»–зңҹжӯЈеҒҡе»әзӯ‘д№ӢеүҚпјҢе°ұе·Із»ҸжҠҠдёңиҘҝж–№зҡ„е»әзӯ‘зҗҶи®әеҸӮйҖҸдәҶпјҢжүҖд»ҘдёҖеҮәжүӢе°ұжҳҜи®ҫи®ЎзҗҶеҝөйқһеёёжҲҗзҶҹзҡ„дёңиҘҝгҖӮвҖқ
дёҠжө·дё–еҚҡдјҡе®Ғжіўж»•еӨҙжЎҲдҫӢйҰҶ

зҺӢжҫҚдҪңе“Ғпјҡ2010е№ҙдёҠжө·дё–з•ҢеҚҡи§ҲдјҡеҹҺеёӮжңҖдҪіе®һи·өеҢәе®ҒжіўжЎҲдҫӢйҰҶ
дёӯеӣҪжөҷжұҹе®Ғжіўж»•еӨҙжқ‘жҳҜе…Ёзҗғе”ҜдёҖе…ҘйҖүдёҠжө·дё–еҚҡдјҡзҡ„д№Ўжқ‘е®һи·өжЎҲдҫӢгҖӮж»•еӨҙжүҖиҗҘйҖ зҡ„вҖңжқ‘еңЁжҷҜдёӯгҖҒжҷҜеңЁеҹҺдёӯвҖқзҡ„з”ҹжҙ»жЁЎејҸпјҢжҲҗеҠҹе®һи·өдәҶдёҖжқЎвҖңд»Ҙз”ҹжҖҒдҝғж—…жёёпјҢд»Ҙж—…жёёе…»з”ҹжҖҒвҖқзҡ„зү№иүІз»ҸжөҺеҸ‘еұ•и·Ҝеҫ„пјҢеңЁдёӯеӣҪд№Ўжқ‘еҹҺеёӮеҢ–еҸ‘еұ•дёӯе…·жңүжҷ®йҒҚж„Ҹд№үгҖӮжЎҲдҫӢеӨ–и§ӮдёәдёҖеә§дёҠдёӢдёӨеұӮгҖҒеҸӨиүІеҸӨйҰҷзҡ„жұҹеҚ—ж°‘еұ…гҖӮйҰҶеҶ…еёғзҪ®вҖңеӨ©зұҒд№ӢйҹівҖқгҖҒвҖңиҮӘ然дҪ“йӘҢвҖқгҖҒвҖңеҠЁж„ҹеҪұеғҸвҖқгҖҒвҖңдә’еҠЁзӯҫеҗҚвҖқзӯүзү№иүІеҢәеҹҹгҖӮвҖңеӨ©зұҒд№ӢйҹівҖқзҡ„еҲӣж„ҸжқҘиҮӘдёӯеӣҪзӢ¬зү№зҡ„дәҢеҚҒеӣӣиҠӮж°”ж–ҮеҢ–пјҢеҸӮи§ӮиҖ…еңЁйҰҶеҶ…еҸҜд»Ҙеҗ¬еҲ°дёҚеҗҢиҠӮж°”зҡ„вҖңеӨ©зұҒд№ӢйҹівҖқпјӣеңЁвҖңиҮӘ然дҪ“йӘҢвҖқеҢәеҹҹпјҢеҸӮи§ӮиҖ…еҸҜж„ҹеҸ—ж»•еӨҙжқ‘зҡ„з”ҹжҖҒзҺҜеўғпјҢдҪ“йӘҢжө“йғҒзҡ„д№Ўеңҹж°”жҒҜгҖӮ
ж»•еӨҙйҰҶзҡ„й»‘зҷҪзӣёй—ҙзҡ„ж°‘еұ…йЈҺж јзҡ„еӨ–еўҷжҳҜз”Ё50еӨҡдёҮеқ—еәҹз“Ұж®ӢзүҮе Ҷз Ңзҡ„гҖӮе®ғ们жҳҜе»әзӯ‘еҚ•дҪҚзҡ„е‘ҳе·ҘеҺҶз»ҸеҚҠе№ҙж—¶й—ҙпјҢеҘ”иө°дәҺиұЎеұұгҖҒй„һе·һгҖҒеҘүеҢ–зӯүең°зҡ„еӨ§е°Ҹжқ‘иҗҪпјҢд»Һеәҹејғзҡ„е·Ҙең° йҮҢ收йӣҶжқҘзҡ„пјҢе…¶дёӯеҢ…жӢ¬е…ғе®қз –гҖҒйҫҷйӘЁз –гҖҒеұӢи„Ҡз –зӯүпјҢе№ҙйҫ„е…ЁйғЁи¶…иҝҮзҷҫе№ҙгҖӮ еұ•йҰҶеҶ…еўҷеҗҢж ·жңүзңӢеӨҙгҖӮеңЁеҺҡеҺҡзҡ„ж°ҙжіҘеўҷдёҠпјҢеҮёжҳҫзҡ„зә№зҗҶз«ҹжҳҜз«№зүҮиӮҢзҗҶпјҢд»ҝдҪӣжҳҜжҺ’жҺ’并еҲ—зҡ„еңҶз«№д»Һдёӯеү–ејҖеҗҺеӣәеҢ–еңЁдәҶеўҷдёҠгҖӮиҝҷжҳҜе®Ғжіўе·ҘеҢ йҮҮз”ЁзӢ¬жңүзҡ„з«№зүҮжЁЎжқҝеҲ¶дҪңжҠҖиүә еҲ¶жҲҗзҡ„вҖңз«–жқЎжҜӣз«№жЁЎжқҝжё…ж°ҙж··еҮқеңҹеүӘеҠӣеўҷвҖқгҖӮ

дҝқжҢҒеҶ…еҝғзҡ„е®Ғйқҷ
зҺӢжҫҚиҜҙпјҡвҖңж ҮеҮҶеҢ–з”ҹдә§зҡ„е»әзӯ‘е°ұеғҸиө„жң¬дё»д№үпјҢжҳҜд»ҘејӮеҢ–зҡ„дәәдҪңдёәеүҚжҸҗиҝӣиЎҢи®ҫи®ЎгҖӮвҖқ
з ”з©¶з”ҹжҜ•дёҡеҗҺпјҢеҗҢеӯҰ们зә·зә·иҝӣе…Ҙдә¬жІӘеӨ§еһӢе»әзӯ‘и®ҫи®ЎйҷўпјҢиһҚе…ҘеҹҺеёӮжү©еј зҡ„жөӘжҪ®гҖӮзҺӢжҫҚеҚҙеӣһеҲ°жқӯе·һгҖӮвҖңеҢ—дә¬гҖҒдёҠжө·жІЎжңүжҲ‘еҝғзӣ®дёӯзҡ„дёӯеӣҪпјҢиҖҢжқӯе·һжңүгҖӮвҖқд»–жӣҫиҝҷж ·и§ЈйҮҠзҗҶз”ұгҖӮ
еҲҡеҲ°жқӯе·һпјҢ家еҫ’еӣӣеЈҒпјҢй“әзқҖдёҖеј иҚүеёӯпјҢзқЎеңЁж°ҙжіҘең°жқҝдёҠгҖӮе©ҡеҗҺпјҢд»–еңЁ50е№іж–№зұізҡ„家дёӯжҺўзҙўгҖҒжј”з»ғзқҖдёҖдәӣдёҚз”ҡжҲҗзҶҹзҡ„жғіжі•пјҢжҜ”еҰӮпјҢз”Ёе®Ӣд»ЈгҖҠиҗҘйҖ жі•ејҸгҖӢдёӯзҡ„жҰ«еҚҜз»“жһ„иҮӘеҲ¶з”»жЎҢпјҢеңЁйҳіеҸ°дёҠжһ„йҖ еҮәдёҖдёӘвҖңдәӯеӯҗвҖқвҖҰвҖҰдёҖеӨ©еӨңйҮҢпјҢд»–й¬јдҪҝзҘһе·®ең°зҗўзЈЁеҮәдёҖеҘ—жҲҝеӯҗдёҖж ·зҡ„жңЁеҲ¶зҒҜе…·пјҢе…«дёӘдёҚе°ҪзӣёеҗҢзҡ„еӨ–зҪ©еҘ—зқҖе…«дёӘе°әеҜёзӣёеҗҢзҡ„еҶ…еЈігҖӮжңЁе·Ҙиў«иҝҷдёӘиҜЎејӮзҡ„жғіжі•жҗһжҳҸдәҶеӨҙпјҢд»–еҸӘеҘҪдёҖзӮ№дёҖзӮ№жүӢжҠҠжүӢең°ж•ҷгҖӮеҪ“жңЁзҒҜд»ҘдёҚеҗҢи§’еәҰе®үиЈ…еҰҘеҪ“并ж”ҫе…ҘзҒҜжіЎж—¶пјҢйӯ”е№»иҲ¬зҡ„е…үзәҝжҠҠжүҖжңүе·ҘеҢ жғҠеҫ—зӣ®зһӘеҸЈе‘ҶгҖӮ
вҖңзӯүжҲ‘жҠҠй’ұжҢЈеӨҹдәҶпјҢе°ұеғҸдҪ иҝҷд№ҲеҺ»еҒҡвҖқвҖңзӯүжҲ‘жӢҝеҲ°еүҜж•ҷжҺҲпјҢе°ұеғҸдҪ иҝҷж ·з”ҹжҙ»вҖқвҖҰвҖҰжҳ”ж—ҘеҗҢзӘ—иҝҷж ·иҜҙпјҢдҪҶзҺӢжҫҚдёҚд»Ҙдёә然пјҢвҖңеңЁйӮЈжқЎи·ҜдёҠиө°еҫ—еӨӘд№…пјҢжІҫжҹ“дәҶдёҖиә«д№ ж°”пјҢе°ұеӣһдёҚдәҶеӨҙдәҶгҖӮвҖқ
дёәдәҶдёҚжІҫжҹ“йӮЈз§ҚвҖңд№ ж°”вҖқпјҢзҺӢжҫҚжҜҸе№ҙеҸӘжҺҘдёҖдёӨдёӘйЎ№зӣ®пјҢ并е°ҶеҲӣж„Ҹе’ҢиҙЁйҮҸзҡ„йҮҚиҰҒжҖ§ж”ҫеңЁж•°йҮҸд№ӢдёҠгҖӮи°ҲеҸҠжӯӨж¬ЎиҺ·еҘ–пјҢд»–иҜҙпјҢ他并дёҚжҢҮжңӣдјҡеҜ№дёӯеӣҪе»әзӯ‘з•ҢеёҰжқҘд»»дҪ•еҸҳйқ©жҲ–еҪұе“ҚпјҢдҪҶжҲ–и®ёеӨ§е®¶еҸҜд»Ҙж„ҸиҜҶеҲ°пјҡвҖңеңЁиҝҷз§ҚзҠ¶жҖҒдёӢд»Қ然еҸҜд»ҘжҖқиҖғпјҢд»Қ然еҸҜд»ҘеңЁе·ҘдҪңе’Ңз”ҹжҙ»дёӯдҝқжҢҒдёҖз§Қзү№з«ӢзӢ¬иЎҢзҡ„ж–№ејҸгҖӮвҖқ
е№ҙиҝ‘еҚҠзҷҫзҡ„зҺӢжҫҚпјҢе№ҙиҪ»ж—¶зҡ„зӢӮеӮІжёҗжёҗеҸҳжҲҗдәҶж·Ўе®ҡгҖҒжҺҘеҸ—дёҺе®Ҫе®№гҖӮдёҖж¬ЎпјҢдёӯеӣҪе»әзӯ‘и®ҫи®Ўз ”з©¶йҷўжҖ»е»әзӯ‘еёҲеҙ”жҒәзңӢеҲ°зҺӢжҫҚзҡ„дҪңе“Ғиў«дәәиӮҶж„ҸзҜЎж”№пјҢж°”еҫ—еңЁз”өиҜқйҮҢеӨ§еҸ«пјҡвҖңдҪ жҖҺд№ҲиғҪе…Ғ许他们иҝҷд№ҲеҒҡ?他们зҹҘдёҚзҹҘйҒ“е®ғеңЁдёӯеӣҪзҺ°д»Је»әзӯ‘еҸІдёҠжҳҜд»Җд№ҲдҪҚзҪ®?з«ҹ然е°ұиҝҷж ·жҠҠе®ғжӢҶжҺүдёҖеқ—!вҖқзҺӢжҫҚеҸӘж·Ўж·Ўең°еӣһдәҶдёҖеҸҘпјҡиҝҷе°ұжҳҜдёӯеӣҪпјҢиҝҷе°ұжҳҜзҺ°е®һгҖӮ
з”ҹжҙ»дёӯзҡ„зҺӢжҫҚдёҚз”Ёз”өи„‘дёҚдёҠзҪ‘пјҢз”ҡиҮіеҫҲе°‘дҪҝз”ЁжүӢжңәгҖӮд»–и®ӨдёәйӮЈдәӣдәӢзү©еҜ№з”ҹжҙ»ж— зӣҠпјҢд»–иҰҒдҝқжҢҒеҶ…еҝғзҡ„е®ҒйқҷгҖӮ
еҚҒеҮ ж¬Ўе·ҙй»Һд№ӢиЎҢпјҢд»–жҜҸж¬ЎеҸӘеҺ»дёҖдёӘең°ж–№вҖ”вҖ”еңЈж—Ҙе°”жӣјеӨ§иЎ—зҡ„иҠұзҘһе’–е•ЎйҰҶпјҢдёҖжіЎе°ұжҳҜеҚҠеӨ©пјҢйӮЈжҳҜеҮ еҚҒе№ҙеүҚжө·жҳҺеЁҒгҖҒиҗЁзү№йқҷйқҷжҖқиҖғзҡ„ең°ж–№гҖӮд»–иҜҙпјҢеңЁйӮЈдёӘжңҙзҙ зҡ„иЎ—и§’пјҢд»–иғҪж„ҹи§үеҲ°з©әж°”дёӯејҘжј«зқҖдёҚеҗҢзҡ„ж°”жҒҜгҖӮзҺӢжҫҚи§үеҫ—пјҢиҝҷз§Қж°”жҒҜе°ұеҸ«вҖңдј з»ҹвҖқпјҢвҖңе®ғиғҪи®©дёҖдәӣдёңиҘҝд»ҺиҝҮеҺ»жҙ»еҲ°д»ҠеӨ©пјҢ并且дёҖзӣҙж„ҹжҹ“зқҖдҪ гҖӮвҖқ
зҺӢжҫҚи®ҫи®Ўи§ӮзӮ№пјҡ
вҖңеёҢжңӣжңүз”ҹд№Ӣе№ҙиғҪзңӢеҲ°еәҹйҷӨдҪҝз”Ёж··еҮқеңҹвҖқ
дёӯеӣҪе»әзӯ‘з•ҢзӣјжңӣдёӯеӣҪдәәиҺ·еҫ—жҷ®еҲ©е…№е…ӢеҘ–жҳҜдёҖзӣҙд»ҘжқҘзҡ„жўҰжғіпјҢеҪ“иҝҷз§ҚиҚЈиӘүзңҹзҡ„еҲ°жқҘж—¶еҸҲжңүдәӣиҢ«з„¶гҖӮжҳҫ然зҺӢжҫҚзҡ„иҺ·еҘ–жңүзқҖдёҖдёӘеӨ§зҡ„ж—¶д»ЈиғҢжҷҜпјҢиҝҷе°ұжҳҜжҲ‘2011е№ҙеңЁзӯ–еҲ’зҡ„ вҖңеҗ‘дёңж–№вҖ”вҖ”дёӯеӣҪе»әзӯ‘жҷҜи§ӮвҖқеұ•еңЁзҪ—马еұ•еҮәзҡ„еүҚиЁҖдёӯжүҖиҜҙзҡ„пјҡвҖңе…ЁзҗғеҢ–з»ҷжҲ‘们зҡ„з”ҹжҙ»жүҖеёҰжқҘзҡ„иҙҹйқўеҪұе“Қд№ҹжҳҜзҺ°е®һпјҢжңүиҙЈд»»е’ҢйҒ“еҫ·ж„ҹзҡ„дёӯеӣҪе»әзӯ‘еёҲ们еңЁжҖқиҖғпјҢеҰӮдҪ•йҖҡиҝҮдҪҝз”Ёеӣһ收зҡ„гҖҒжҲ–еҲӣйҖ еҶҚз”ҹжҖ§е»әзӯ‘жқҗж–ҷпјҢжқҘи§ЈеҶіе»әзӯ‘еӨ§йҮҸж¶ҲиҖ—е’ҢеҚ жңүиҮӘ然иө„жәҗзҡ„й—®йўҳпјҢиҝҷз§ҚдәӢеҸ‘з”ҹеңЁдёӯеӣҪпјҢжҲ–и®ёжҳҜеҜ№дҪҚдәҺдё–з•Ңе»әзӯ‘иҪ¬жҠҳзӮ№зҡ„дёӯеӣҪе»әзӯ‘з•Ңзҡ„дёҖз§ҚжҸҗйҶ’гҖӮвҖқиҝҷдёӘеұ•и§ҲеҸҚжҳ дәҶдёӯеӣҪж–°дёҖд»Јзҡ„е»әзӯ‘еёҲзҡ„е»әзӯ‘е®һи·өжҳҜе’ҢдёӯеӣҪеҙӣиө·зҡ„жӯҘдјҗеҗҢжӯҘзҡ„пјҢиҝҷдәӣйЎ№зӣ®е°ұеҸҚжҳ дәҶ他们дёӘдәәе’Ңе»әзӯ‘гҖҒе»әзӯ‘е’ҢеӣҪ家еҗҢжӯҘзҡ„еҺҶзЁӢпјҢиҖҢзҺӢжҫҚжҳҜе…¶дёӯзҡ„дҪјдҪјиҖ…пјҢиҝҷдёӘеҘ–дјҡжҝҖеҠұжӣҙеӨҡзҡ„дёӯеӣҪе»әзӯ‘еёҲе’ҢеҹҺеёӮ规еҲ’иҖ…пјҢж·ұе…Ҙең°иҖғиҷ‘жҲ‘们зҡ„еҹҺеёӮе’Ңз”ҹжҙ»еҰӮдҪ•жҢҒз»ӯжҖ§зҡ„еҸ‘еұ•гҖӮиҖҢдёӯеӣҪеҮ еҚғе№ҙзҡ„ж–ҮжҳҺдёӯпјҢд»ҺжқҘжІЎжңүеҮәзҺ°иҝҮдёҚиғҪжҢҒз»ӯеҸ‘еұ•зҡ„й—®йўҳпјҢеҸӘжҳҜиҝӣе…Ҙиҝ‘д»Је·Ҙдёҡж–ҮжҳҺж—¶д»Јд№ӢеҗҺпјҢз”ҹжҙ»е’ҢиҮӘ然зҺҜеўғжүҚеҸ‘з”ҹзӘҒеҸҳпјҢжүҖд»ҘзҺӢжҫҚжүҖиҜҙзҡ„пјҡвҖңжҲ‘еёҢжңӣжңүз”ҹд№Ӣе№ҙиғҪзңӢеҲ°еәҹйҷӨдҪҝз”Ёж··еҮқеңҹвҖқиҝҷеҸҘиҜқпјҢд»ЈиЎЁдәҶдёӯеӣҪе»әзӯ‘家еҪ»еә•еӣһеҪ’дёӯеӣҪдј з»ҹз”ҹжҙ»ж–№ејҸзҡ„еҶіеҝғпјҢд»ҺиҖҢи®ӨиҜҶеҲ°вҖңе»әзӯ‘еә”иҜҘжҳҜдёҖдёӘз”ҹе‘ҪдҪ“зі»вҖқпјҲзҺӢжҫҚиҜӯпјүгҖӮ
зҺӢжҫҚгҖҠи®ҫи®Ўзҡ„ејҖе§ӢгҖӢ
2002е№ҙпјҢе»әзӯ‘еёҲзҺӢжҫҚеҮәзүҲдәҶд»–зҡ„第дёҖжң¬е»әзӯ‘еӯҰж–ҮйӣҶпјҡгҖҠи®ҫи®Ўзҡ„ејҖе§ӢгҖӢгҖӮеңЁд№Ұдёӯзҡ„дҪңиҖ…д»Ӣз»ҚйҮҢпјҢзҺӢжҫҚиў«иҝҷж ·жҸҸиҝ°пјҡвҖңд»–жҠЁеҮ»дё“дёҡе»әзӯ‘еӯҰпјҢдҪҶд»–зҡ„жүҖи°“вҖҳдёҡдҪҷе»әзӯ‘вҖҷжҙ»еҠЁи¶…и¶ҠдёҖиҲ¬иҖҢиЁҖзҡ„и®ҫи®ЎиҖҢжҢҮеҗ‘жҹҗз§Қе…ідәҺе»әзӯ‘зҡ„е»әзӯ‘пјӣд»–еқҡжҢҒж„ҹжӮҹе»әзӯ‘жң¬иә«пјҢжү§зқҖдәҺеҠҹиғҪи§ЈиҜ»пјҢиҙ¬дҪҺйҖ еһӢиүәжңҜзҡ„йҮҚиҰҒжҖ§пјҢдҪҶд»–зҡ„дҪңе“Ғе…·жңүжҹҗз§Қи¶…и¶ҠйЈҺж јдәүи®әзҡ„иүәжңҜиҙЁйҮҸпјӣд»–еҸҚеҜ№е…ідәҺе»әзӯ‘зҡ„ж–ҮеӯҰеҢ–еҸҷдәӢпјҢдҪҶж— и®әд»–зҡ„и®ҫи®ЎиҝҳжҳҜеҶҷдҪңйғҪе…·жңүжҹҗз§Қйҡҫд»ҘиҫЁеҲ«е…¶жқҘжәҗзҡ„ж–ҮеӯҰж°”иҙЁгҖӮд»–ејәи°ғе»әзӯ‘еёҲйҰ–е…Ҳеә”жҳҜдёҖдёӘж–Үдәәз§үжүҝжҹҗз§Қжү№еҲӨдҪҝе‘ҪдҪҶй”ӢеҲ©зҡ„зҹӣеӨҙдёҚд»…жҢҮеҗ‘иҮӘе·ұд№ӢеӨ–пјҢжӣҙе§Ӣз»ҲжҢҮеҗ‘иҮӘе·ұпјҢз”ҡиҮід»ҘеҳІи®ҪдёҺиҮӘеҳІж¶Ҳи§ЈзқҖвҖҳжү№еҲӨвҖҷзҡ„жҲҫж°”гҖӮвҖқ
2012е№ҙ5жңҲпјҢзҺӢжҫҚеңЁдәәж°‘еӨ§дјҡе ӮйҮ‘иүІеӨ§еҺ…йўҶеҸ–дәҶе»әзӯ‘и®ҫи®Ўз•Ңзҡ„жңҖй«ҳеҘ–йЎ№пјҡжҷ®еҲ©е…№е…ӢеҘ–гҖӮд»–жІЎжңүжө·еӨ–з•ҷеӯҰиғҢжҷҜпјҢиә«д»ҪжҳҜ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зҡ„ж•ҷжҺҲпјҢдёҚеұһдәҺд»»дҪ•е»әзӯ‘и®ҫи®ЎйҷўпјҢеңЁиҺ·еҘ–д№ӢеүҚпјҢд»–дёҖзӣҙзӢ¬з«ӢдәҺеӣҪеҶ…зҺ°иЎҢдё»жөҒдҪ“зі»д№ӢеӨ–пјҢдёҖе№ҙеҮ д№ҺеҸӘжҢүз…§е–ңеҘҪеҒҡдёҖдёӘйЎ№зӣ®пјҢжҜҸдёӘйЎ№зӣ®д»Һи®ҫи®ЎеҲ°е»әжҲҗиҖ—ж—¶ж•°е№ҙгҖӮеҰӮжһңжҢүз…§еӣҪеҶ…е»әзӯ‘и®ҫи®Ўйҷўе№ҙеәҰдәәеқҮдә§еҖјзҡ„ж–№ејҸжқҘиЎЎйҮҸпјҢзҺӢжҫҚеҲӣйҖ зҡ„д»·еҖје’Ңи®ҫи®Ўзҡ„йқўз§Ҝж— жі•е’ҢеӨ§еӨҡж•°е»әзӯ‘еёҲзӣёжҜ”гҖӮд»Һ1980е№ҙд»Јжң«ејҖе§ӢиҮід»ҠпјҢд»–зҡ„е»әжҲҗдҪңе“ҒжңүзәҰдәҢеҚҒеӨҡйЎ№пјҢе…¶дёӯеңЁжқӯе·һе’ҢдёҠжө·зҡ„дёҖдәӣж—©жңҹдҪңе“ҒеңЁе»әжҲҗеҗҺе·Із»ҸжӢҶйҷӨдәҶгҖӮ
жҷ®еҲ©е…№е…ӢеҘ–еҮ д№ҺжҜҸдёҖж¬ЎйғҪжҺҲдәҲдәҶйЈҺеҸЈжөӘе°–дёҠзҡ„е»әзӯ‘еёҲпјҢжҜ”еҰӮе®үи—Өеҝ йӣ„гҖҒеј—е…°е…ӢВ·зӣ–йҮҢгҖҒжүҺе“ҲВ·е“ҲиҝӘеҫ·пјҢзӯүзӯүпјҢ他们еңЁиҺ·еҘ–д№ӢеүҚйғҪжӣҫйўҶеҸ—иҝҮдёҮдј—зһ©зӣ®гҖӮзҺӢжҫҚеҚҙе°ӨеҰӮзӢ¬иЎҢдҫ пјҢзӢ¬иҮӘйҖҶжөҒиЎҢиө°гҖӮе…¶д»–дәәеңЁиҜ•йӘҢж–°жқҗж–ҷпјҢ他收йӣҶж—§дёңиҘҝпјҢжңЁеӨҙгҖҒз“ҰзүҮгҖҒз“·зүҮпјҢеҒ¶е°”еҮ дёӘз«ӢйқўжҚўдёҠзҺ»з’ғдёәдё»и§’д№ҹдёҺж—¶дёӢжөҒиЎҢзҡ„и¶…зҷҪзҺ»з’ғ幕еўҷеӨ§зӣёеҫ„еәӯпјӣе…¶е®ғе»әзӯ‘еёҲи°ӢжұӮжӣҙй«ҳ科жҠҖгҖҒжӣҙжғҠжӮҡзҡ„и®ҫи®Ўж—¶пјҢд»–жӢ’з»қз”өи„‘пјҢиҜҙиҮӘе·ұзҡ„и®ҫи®ЎжқҘжәҗжҳҜиҮӘ然гҖҒе®Ӣз”»дёҺеҸӨиҜ—пјҢеҜ№дәҺе»әйҖ зҡ„зҗҶи§ЈжқҘиҮӘжҷ®йҖҡеҢ дәәпјӣеҪ“еҹҺеёӮеҢ–жөӘжҪ®еҲ°жқҘж—¶пјҢд»–иҜҙвҖңйҮҚиҰҒзҡ„жҳҜпјҢе»әзӯ‘еёҲйҖҡиҝҮиҮӘе·ұзҡ„еҲӣдҪңжҖҺд№Ҳж ·жқҘеё®еҠ©дәә们跨и¶ҠеҹҺд№Ўд№Ӣй—ҙеҜ№з«Ӣд»·еҖји§Ӯзҡ„йёҝжІҹвҖқгҖӮ
зҺӢжҫҚеңЁе»әзӯ‘з•Ңеј•иө·дёҖе®ҡеҸҚе“Қзҡ„йҰ–дёӘдҪңе“ҒпјҢеҸҜд»ҘиҜҙжҳҜиӢҸе·һеӨ§еӯҰж–ҮжӯЈеӯҰйҷўеӣҫд№ҰйҰҶгҖӮд»ҺйӮЈж—¶иө·пјҢд»–зҡ„и®ҫи®Ўе°ұжңүйІңжҳҺзҡ„дёӘдәәзү№еҫҒпјҢеӣәжү§зҡ„и®ҫи®ЎйҖ»иҫ‘йҮҢжңүзқҖе®Ңж•ҙзҡ„зҗҶи®әзі»з»ҹпјҢиҝҷеңЁд»–зҡ„ж—©жңҹи‘—дҪңгҖҠи®ҫи®Ўзҡ„ејҖе§ӢгҖӢйҮҢе·ІеҲқзҺ°з«ҜеҖӘгҖӮ
д№ҰдёӯпјҢд»–жҸҸеҶҷе°ҸеҲ°вҖңе…«й—ҙдёҚиғҪдҪҸзҡ„жҲҝеӯҗвҖқйҮҢзҡ„е°ҸзҒҜе…·пјҢеӨ§еҲ°еҮ еҚғе№іж–№зұізҡ„еӣҫд№ҰйҰҶпјҢзҺӢжҫҚйғҪе°ҶдёӯеӣҪдј з»ҹж„ҸйҹөгҖҒд№ЎеңҹжҠҖиүәж°”жҒҜгҖҒжқҺжё”зҡ„жғ…иҮҙз»“еҗҲеңЁдёҖиө·пјҢеҶҚж··жқӮдёҖдәӣиҜ—ж„ҸдёҺеҗҺзҺ°д»ЈйЈҺж јгҖӮеҸҜд»ҘиҜҙд»–зӢЎзҢҫең°з”ҹжҲҗдәҶеҸӘеұһдәҺиҮӘе·ұзҡ„е“ІеӯҰгҖӮд»–еҸҷиҝ°зҡ„ж–№ејҸеқҰзҺҮгҖҒдҝЎеҝғж»Ўж»ЎеҸҲе…ҙиҮҙеӢғеӢғпјҢеғҸз”ҹйҖ дёҖдёӘе№іиЎҢе®Үе®ҷпјҢйўҶзқҖиҜ»иҖ…йҡҸд»–иҝӣе…Ҙе…¶дёӯгҖӮеҰӮжһңе°қиҜ•еҺ»зҗҶ解他并жңҖз»Ҳи®ӨдёәиҮӘе·ұзңҹзҡ„зҗҶи§ЈдәҶд»–пјҢдҪ дјҡеҸ‘зҺ°пјҢд»–зҡ„е“ІеӯҰеҜјиҮҙдәҶд»–зҡ„и®ҫи®ЎгҖӮ
зҺӢжҫҚдёҚжҳҜйӮЈз§Қйҷ·е…Ҙз»ҶиҠӮи°ғж•ҙзҡ„е»әзӯ‘еёҲпјҢд»–жүҖеҒҡзҡ„жҳҜд»Һе»әзӯ‘зҡ„з”ҹжҲҗдҪ“зі»е’Ңз”ҹжҲҗж–№ејҸдёҠжқҘиҝӣиЎҢжҺ§еҲ¶гҖӮеңЁиҝҷж–№йқўпјҢеҗҲзҗҶжҖ§дёҚе®№иҙЁз–‘пјҢжІЎжңүеҸҜжӣҝд»Јзҡ„йҖүйЎ№гҖӮеңЁд№ҰйҮҢпјҢзҺӢжҫҚдёәд»–зҡ„жңӢеҸӢйҷҲй»ҳи®ҫи®ЎдәҶиүәжңҜе·ҘдҪңе®ӨпјҢдҪҶи®ҫи®Ўж–№жЎҲеҸӘжңүдёӨеј еӣҫзәёе’Ңе…ӯжқЎеҺҹеҲҷпјҢе…¶д»–зҡ„дёҚеҶҚеӨҡиҜҙгҖӮеҜ№дәҺйҷҲй»ҳзҡ„иҝҪй—®пјҢзҺӢжҫҚзҡ„еӣһзӯ”жҳҜвҖңдҪ зӣёдҝЎжҲ‘зҡ„и®ҫи®ЎпјҢжҲ‘зӣёдҝЎдҪ зҡ„ж„ҹи§үвҖқгҖӮеҪ“е·ҘдҪңе®Өе»әжҲҗпјҢиҷҪ然з»ҶиҠӮз•ҘжңүеҸҳеҢ–пјҢдҪҶжүҖжңүзҡ„дёҖеҲҮйғҪжҺҢжҺ§еңЁзҺӢжҫҚжңҖеҲқи®ҫи®Ўзҡ„ж•ҙдёӘз©әй—ҙ秩еәҸжһ¶жһ„дёӯгҖӮд№ӢеҗҺпјҢзҺӢжҫҚжӣҫз»ҸеңЁдёҠжө·зҡ„вҖңйЎ¶еұӮз”»е»ҠвҖқйЎ№зӣ®йҮҢеӣһеҝҶиҝҷж®өеҫҖдәӢпјҡвҖңи®ҫи®ЎеҜ№жҲ‘д№ҹи®ёеҸӘжҳҜиғЎд№ұзҡ„ејҖе§ӢпјҢжҲ‘жғҹдёҖзҹҘйҒ“зҡ„жҳҜи®©е·ҘеҢ 们еңЁдҪ•еӨ„еҒңжӯўпјҢ并жҠҠиҝҷдёҖеҲҮеҪ“еҒҡжҹҗз§ҚзҺ°жҲҗе“Ғе’ҢзӣҳжҺҘеҸ—гҖӮвҖқ
дёӨе№ҙеүҚпјҢжҲ‘жӣҫи§ҒиҝҮзҺӢжҫҚгҖӮгҖҠдё–з•Ңе»әзӯ‘гҖӢжқӮеҝ—иҜ·зҺӢжҫҚеҲ°жё…еҚҺеӨ§еӯҰе»әзӯ‘еӯҰйҷўжј”и®ІпјҢжҠҘе‘ҠеҺ…йҮҢдәәж»ЎдёәжӮЈпјҢеӯҰз”ҹгҖҒж•ҷжҺҲе’Ңе…¶д»–е»әзӯ‘еёҲд»Һеҗ„еӨ„иө¶жқҘпјҢжғізҹҘйҒ“зҺӢжҫҚеҲ°еә•вҖңи‘«иҠҰйҮҢеҚ–зҡ„д»Җд№ҲиҚҜвҖқгҖӮйӮЈж¬Ўжј”и®ІпјҢзҺӢжҫҚиҜҙиө·д»–еңЁе®ҒжіўеҚҡзү©йҰҶзҡ„з«ӢйқўдёҠдҪҝз”ЁдәҶеӨ§йҮҸж—§з –з“ҰпјҢжҖҺд№ҲжӢјжҺҘдҪҝ用并没жңүдёҘж јзҡ„ж–Ҫе·ҘеӣҫпјҢд»–еҸӘи®ҫе®ҡеҺҹеҲҷпјҢе°ҶжҜҸдёҖеқ—з –зҡ„йҖүжӢ©жқғдәӨз»ҷдәҶзҺ°еңәзҡ„е·ҘеҢ 们пјҢжңҖеҗҺз«ӢйқўеҸҳжҲҗдәҶж–‘й©іж— еәҸзҡ„зҠ¶жҖҒгҖӮжҢүз…§д»–зҡ„иҜҙжі•пјҡвҖңи„ҡжүӢжһ¶жӢҶдёӢдәҶдёүзұіпјҢ他们е°ұдёҚж•ўжӢҶдәҶпјҢеӣ дёәеёӮж°‘еҸҚжҳ иҝҷдёӘдёңиҘҝеӨӘеҘҮжҖӘдәҶпјҢеҗҺжқҘжҲ‘们еҺ»еёӮж”ҝеәңеӨ§и®Іе ӮеҒҡдәҶдёҖеҚғеӨҡдәәзҡ„дёӨдёӘе°Ҹж—¶жҠҘе‘ҠпјҢжӢҶдёӢжқҘд»ҘеҗҺеӨ§е®¶е°ұж¬ўж¬Јйј“иҲһпјҢжҜҸеӨ©дёҖдёҮдәәеҸӮи§ӮпјҢжҜҸеӨ©еҸӘиғҪдёүеҚғдәәеҸӮи§Ӯзҡ„еҚҡзү©йҰҶжҜҸеӨ©дёҖдёҮдәәеҸӮи§ӮпјҢиҝһз»ӯдёүдёӘжңҲдёҖзҷҫдёҮдәәеҺ»еҸӮи§ӮгҖӮвҖқ
иҝҷжҳҜзҺӢжҫҚзҡ„зӢ¬еҲ°д№ӢеӨ„пјҢд»–е…·жңүеёғйҒ“иҖ…зҡ„зү№иҙЁгҖӮд»–еҸҜд»ҘйҖҡиҝҮи®Ёи®әдјҡгҖҒжј”и®ІжқҘе®Ји®Іе’ҢйҳҗйҮҠд»–зҡ„е“ІеӯҰпјҢйӮЈз§ҚдёҚд»ҘзҫҺдёәзҫҺпјҢеҪўдҪ“д»ӢдәҺеӨҚжқӮгҖҒз®ҖеҚ•гҖҒзІ—зіҷд№Ӣй—ҙпјҢзңӢдёҠеҺ»зІ—з¬ЁеҚҙеҸҲеӨҚжқӮеҲ°еҢӘеӨ·жүҖжҖқзҡ„и®ҫи®ЎйЈҺж јгҖӮиө·еҲқд»–дҪҝдәәйҡҫдәҺзҗҶи§ЈпјҢд№ӢеҗҺеӣ дёәд»–зҡ„еӣәжү§е·ұи§ҒгҖҒд»–зҡ„иӮҶж„ҸеҰ„дёәпјҢжҲ–иҖ…жҳҜеӣ дёәд»–зҡ„иҜӯиЁҖйӯ…еҠӣпјҢд»–еҸҲи®©дәә欣然жҺҘеҸ—гҖӮ
зҺӢжҫҚе»әзӯ‘и®ҫи®Ўд»ЈиЎЁдҪңе“Ғпјҡ

зҺӢжҫҚдҪңе“Ғпјҡ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иұЎеұұж Ўеӣӯ
дёӯеӣҪзҫҺйҷўиұЎеұұж ЎеӣӯдёҖжңҹдҝҜзһ°

дёӯеӣҪзҫҺйҷўиұЎеұұж ЎеӣӯдёҖжңҹд»ҺеәӯйҷўеӨ–и§ӮиұЎеұұ
дёҺйӮЈдәӣжІүжөёдәҺи¶…йҖҹиҗҘйҖ дёӯзҡ„дёӯеӣҪдё»жөҒе»әзӯ‘еёҲдёҚеҗҢпјҢиә«еұ…еӯҰйҷўиҰҒиҒҢзҡ„зҺӢжҫҚиҝңзҰ»зҺ°е®һзҡ„е–§еҡЈпјҢдёҖж„ҸдәҺд»–зҡ„зҗҶжғіеҹҺеёӮгҖҒе»әзӯ‘зҡ„иҗҘйҖ гҖӮеӣӯжһ—еҹҺеёӮе’Ңеӣӯжһ—е»әзӯ‘зҡ„иҗҘйҖ дёҖзӣҙжҳҜзҺӢжҫҚжўҰ еҜҗд»ҘжұӮзҡ„пјҢиҖҢиұЎеұұж ЎеҢәжӯЈеҘҪе®һзҺ°е’Ңж»Ўи¶ідәҶд»–еӨҡе№ҙжқҘзҡ„еӨҷж„ҝгҖӮ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дәәзҡ„гҖҒдәәж–ҮзҗҶжғідё»д№үзҡ„ж Ўеӣӯ规еҲ’е’Ңж ЎеӣӯиҗҘйҖ пјҢдёӨжңҹиҗҘйҖ зҺҜз»•дәҶиұЎеұұпјҢе‘Ҳж•ЈзӮ№зҠ¶еҲҶеёғеұұйҮҺй—ҙпјҢйҡҸж„Ҹ иҖҢиҮӘ然пјҢжІЎжңүеҲ»ж„Ҹи®ҫи®Ўзҡ„е»әзӯ‘еҪўиұЎпјҢд№ҹжІЎжңүзқҖж„ҸиҗҘйҖ зҡ„дёӯеҝғж ЎеҢәпјҢж ЎеҢәжҳҜй“әеұ•дәҺиұЎеұұи„ҡдёӢзҡ„еӣӯжһ—еҹҺеёӮгҖӮеңЁиұЎеұұж ЎеҢәпјҢзҺӢжҫҚжңүи®ЎеҲ’ең°еӨ§йҮҸдҪҝз”ЁдәҶеҪ“ең°еәҹејғзҡ„ж—§з“ҰпјҢиҝҷдёҚ д»…дҪҝе»әзӯ‘йҷЎеўһдәҶеҺҶеҸІж„ҹпјҢд№ҹиЎЁиҫҫдәҶд»–еҜ№зҺ°е®һзҡ„жҖҒеәҰпјҡиҝҷдәӣж—§з“ҰеӨ§йғЁеҲҶжҳҜ1970е№ҙд»ЈжұҹеҚ—еҲқжӯҘеҜҢиЈ•ж—¶жңҹеӨ§йҮҸе»әйҖ зҡ„дә§зү©пјҢиҖҢд»ҠеңЁеҶҚеәҰзҝ»йҖ иҝҗеҠЁдёӯжғЁйҒӯйҒ—ејғпјҢж—§з“Ұзҡ„еӣһ 收еҶҚеҲ©з”Ёж—ўжҳҜиҝҪеҝҶжӯЈеңЁйҖқеҺ»зҡ„е»әйҖ дј з»ҹпјҢд№ҹжҳҜеә”еҜ№еү§еҸҳзҺ°е®һзҡ„жү№еҲӨжҖ§зӯ–з•ҘгҖӮжӣҙдёәйҮҚиҰҒзҡ„жҳҜпјҢиұЎеұұж ЎеҢәзҡ„规еҲ’дёҺе»әзӯ‘и®ҫи®Ўйҡҗеҗ«зқҖеҶҚйҖ дёңж–№е»әзӯ‘еӯҰзҡ„е®Ҹж„ҝпјҢд№ҹзқҖж„ҸдәҺе»әжһ„ еӣӯжһ—еҹҺеёӮгҖҒе»әзӯ‘зҡ„иҢғжң¬гҖӮ
иҝҷзүҮж ЎеӣӯжҳҜеӣҪз«Ӣ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дёәе®ғзҡ„е»әзӯ‘иүәжңҜеӯҰйҷўгҖҒи®ҫи®ЎиүәжңҜеӯҰйҷўгҖҒе…¬е…ұиүәжңҜеӯҰйҷўгҖҒеҪұи§ҶеҠЁз”»еӯҰйҷўгҖҒе®һйӘҢеҠ е·ҘдёӯеҝғгҖҒеҹәзЎҖж•ҷеӯҰйғЁе»әйҖ зҡ„ж–°ж ЎеӣӯпјҢ500еӨҡж•ҷеёҲе’Ң5000еӨҡжң¬з§‘дёҺз ”з©¶з”ҹеңЁиҝҷйҮҢж•ҷеӯҰгҖҒеӯҰд№ дёҺз”ҹжҙ»гҖӮ
дёӯеӣҪзҫҺйҷўиұЎеұұж ЎеӣӯдёҖжңҹ
2000е№ҙпјҢеӯҰйҷўжІЎжңүйҖүжӢ©иҝӣе…ҘдёӯеӣҪж—¶дёӢжөҒиЎҢзҡ„ж”ҝеәңз»„е»әзҡ„еӨ§еӯҰйҷўеҢәпјҢиҖҢжҳҜйҖүеқҖеңЁжқӯе·һеҚ—йғЁзҫӨеұұзҡ„дёңйғЁиҫ№зјҳпјҢе°Ҫз®ЎиҝҷйҮҢжҡӮж—¶дјҡеӯҳеңЁдёҖдәӣеҹәзЎҖи®ҫж–ҪдёҚи¶ізҡ„й—®йўҳпјҢдҪҶеӯҰйҷўзҡ„ж•ҷжҺҲгҖҒиүәжңҜ家дёҺеҸӮдёҺйҖүеқҖзҡ„е»әзӯ‘еёҲе…ұеҗҢи®ӨдёәпјҢдҫқз…§дёӯеӣҪзҡ„ж–ҮеҢ–дј з»ҹпјҢеңЁе»әзӯ‘йҖүеқҖж—¶пјҢзҺҜеўғдёӯзҡ„еұұж°ҙз”ҡиҮіжҜ”е»әзӯ‘жӣҙеҠ йҮҚиҰҒгҖӮ
е»әзӯ‘еёҲзҺӢжҫҚеңЁиұЎеұұж–°ж Ўеӣӯзҡ„е»әйҖ дёӯдҪ“зҺ°дәҶиҮӘе·ұзҡ„жҖқиҖғдёҺдё»еј гҖӮеҰӮдҪ•еңЁиҝ…йҖҹдё§еӨұең°еҹҹж–ҮеҢ–зҡ„дёӯеӣҪеҹҺеёӮйҮҚе»әжңүең°еҹҹж №жәҗзҡ„еңәжүҖз»“жһ„пјҢеҰӮдҪ•и®©дёӯеӣҪдј з»ҹдёҺеұұж°ҙе…ұеӯҳзҡ„е»әзӯ‘иҢғејҸжҙ»з”ЁеңЁд»ҠеӨ©зҡ„зҺ°е®һпјҢеҰӮдҪ•еҲ©з”ЁеӨ§еӯҰж Ўеӣӯзҡ„е»әйҖ 规模жҺўзҙўдёҖз§ҚеҪ“д»ЈдёӯеӣҪжң¬еңҹж–°зҡ„еҹҺеёӮиҗҘйҖ жЁЎејҸгҖӮеӣһжңӣдёӯеӣҪдј з»ҹеӣӯжһ—йҷўиҗҪејҸзҡ„еӨ§еӯҰе»әзӯ‘еҺҹеһӢпјҢиұЎеұұж–°ж ЎеӣӯжңҖз»Ҳе‘ҲзҺ°дёәдёҖзі»еҲ—вҖңйқўеұұиҖҢиҗҘвҖқзҡ„е·®ејӮжҖ§йҷўиҗҪж јеұҖгҖӮе»әзӯ‘зҫӨж•Ҹж„ҹзҡ„йҡҸеұұж°ҙжүӯиҪ¬еҒҸж–ңпјҢеңәең°еҺҹжңүзҡ„еҶңең°гҖҒжәӘжөҒе’ҢйұјеЎҳиў«е°ҸеҝғдҝқжҢҒпјҢдёӯеӣҪдј з»ҹеӣӯжһ—зҡ„зІҫиҮҙиҜ—ж„ҸдёҺз©әй—ҙиҜӯиЁҖиў«жҺўзҙўжҖ§зҡ„иҪ¬еҢ–дёәеӨ§е°әеәҰзҡ„ж·іжңҙз”°еӣӯгҖӮйӮЈдәӣж Ўеӣӯе»әзӯ‘еӣ жӯӨдёҚжҳҜеӯӨз«Ӣзҡ„и®ҫи®ЎеҮәжқҘ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вҖңиҮӘ然вҖқдёҺвҖңеҹҺеёӮвҖқд№Ӣй—ҙзҡ„жҖқиҖғдёӯжҳҫзҺ°еҮәжқҘгҖӮеңЁдёӯеӣҪзҡ„е»әзӯ‘дј з»ҹдёӯпјҢиҝҷж ·зҡ„е»әзӯ‘иў«з§°дёәвҖңеӣӯжһ—вҖқгҖӮиҝҷдёӘиҜҚж— жі•з”ЁиҘҝиҜӯзҡ„вҖңиҠұеӣӯвҖқеҺ»зҝ»иҜ‘пјҢе®ғзү№жҢҮвҖңиҮӘ然вҖқиў«зҪ®е…ҘвҖңеҹҺеёӮвҖқпјҢиҖҢеҹҺеёӮе»әзӯ‘еӣ жӯӨеҸ‘з”ҹжҹҗз§ҚиҙЁеҸҳпјҢе‘ҲзҺ°дёәеҚҠе»әзӯ‘еҚҠиҮӘ然зҡ„еҪўжҖҒгҖӮ
еҰӮжһңвҖңиҮӘ然вҖқжҳҜдёҖз«ҜпјҢе»әзӯ‘еёҲжҖқиҖғзҡ„еҸҰдёҖз«Ҝе°ұжҳҜвҖңеҹҺеёӮвҖқпјҢдёҖзі»еҲ—дјјд№ҺеңЁзӯүеҫ…жҹҗз§ҚдәӢ件зӘҒеҸ‘зҡ„е°ҸеңәжүҖпјҢдјјд№ҺжңүзӮ№ж•Јжј«пјҢз”ҡиҮіжІЎжңүдёҖдёӘдёҘж јзҡ„з»“жһ„пјҢдҪҶзңҹжӯЈзҡ„з”ҹжҙ»жүҚеҸҜиғҪеңЁиҝҷйҮҢж”ҫжқҫзҡ„еҸ‘з”ҹгҖӮе»әзӯ‘дә§з”ҹдәҶжӘҗдёӢгҖҒжҙһеҶ…гҖҒйЈһйҒ“гҖҒеұӢйЎ¶дёӢжІүйҷўиҗҪгҖҒеұӢйЎ¶е№іеҸ°гҖҒж ‘дёӢгҖҒз”°й—ҙгҖҒжІіиҫ№зӯүеӨҡж ·жҖ§зҡ„ж•ҷеӯҰдәӨжөҒз©әй—ҙпјҢеңЁиҝҷйҮҢпјҢеӯҰйҷўж•ҷиӮІжңҖйҮҚиҰҒзҡ„е°ұжҳҜеҝғзҒөзҡ„иҮӘз”ұгҖӮ
еңЁиұЎеұұж–°ж ЎеӣӯдёӯпјҢжүҖжңүзҡ„е»әзӯ‘йғҪд»Ҙиҝҷеә§вҖңиұЎеұұвҖқдёәжңҖйҮҚиҰҒзҡ„жҖқиҖғдёҺи§ӮзңӢзҡ„еҜ№иұЎгҖӮжҜҸдёӘе»әзӯ‘йғҪеҰӮеҗҢдёҖдёӘдёӯеӣҪеӯ—пјҢе®ғ们йғҪе‘ҲзҺ°еҮәйқўеҜ№иұЎеұұзҡ„жҹҗз§ҚжҢҮеҗ‘жҖ§пјҢиҖҢеӯ—дёҺеӯ—д№Ӣй—ҙзҡ„з©әзҷҪеҗҢж ·йҮҚиҰҒпјҢжҳҜдәә们еңЁжј«жёёж—¶дёҖж¬ЎеҸҲдёҖж¬ЎеӣһжңӣйӮЈеә§йқ’еұұзҡ„дҪҚзҪ®гҖӮйқўеҜ№еҪ“дёӢдёӯеӣҪеҹҺеёӮзҡ„еӨ§и§„жЁЎжӢҶжҜҒйҮҚе»әзҺ°иұЎпјҢи¶…иҝҮ700дёҮзүҮдёҚеҗҢе№ҙд»Јзҡ„ж—§з –з“Ұиў«д»Һжөҷжұҹе…ЁзңҒзҡ„жӢҶжҲҝзҺ°еңәеӣһ收еҲ°иұЎеұұж–°ж ЎеӣӯпјҢиҝҷдәӣеҸҜиғҪиў«еҪ“еҒҡеһғеңҫеҜ№еҫ…зҡ„дёңиҘҝиў«еңЁиҝҷйҮҢеҫӘзҺҜеҲ©з”ЁпјҢ并жңүж•ҲжҺ§еҲ¶дәҶйҖ д»·пјҢйҮҚж–°жј”з»ҺдәҶдёӯеӣҪжң¬еңҹеҸҜжҢҒз»ӯжҖ§зҡ„е»әйҖ дј з»ҹгҖӮиұЎеұұж–°ж ЎеӣӯжҲ–и®ёжҳҜдёӯеӣҪдј з»ҹдёҺзҺ°е®һжҝҖзғҲеҶІзӘҒдёӯиҜһз”ҹзҡ„еҸҰдёҖз§ҚвҖңд№ҢжүҳйӮҰвҖқпјҢ30еә§еӨ§е°ҸдёҚдёҖзҡ„е»әзӯ‘е№ійқҷзҡ„жІүжөёеңЁдёӯеӣҪеҚ—ж–№е№ізј“зҡ„еұұж°ҙд№Ӣй—ҙпјҢиҝҷйҮҢжөҒеҠЁзқҖ5000дёӘиүәжңҜеӯҰеӯҗзҡ„йқ’жҳҘгҖҒжҝҖжғ…гҖҒжІүжҖқдёҺжўҰжғіпјҢжҳӯзӨәзқҖдёҖжқЎйҖҡеҫҖдәә们еҶ…еҝғж·ұеӨ„зҡ„иҝ”д№Ўд№Ӣи·ҜгҖӮ
зҺӢжҫҚи®ҫи®Ўзҡ„дёӯеӣҪзҫҺйҷўиұЎеұұж ЎеҢәдёҖгҖҒдәҢжңҹе·ҘзЁӢгҖӮ
зҺӢжҫҚдҪңе“Ғж¬ЈиөҸпјҡ

зҺӢжҫҚдҪңе“ҒйӣҶ延伸йҳ…иҜ»>>вҖңдёӯеӣҪжңҖе…·дәәж–Үж°”иҙЁзҡ„е»әзӯ‘家вҖқзҺӢжҫҚ
[иҜ·дҝқз•ҷпјҡеҗҺж—¶д»Ј http://www.houshidai.com/]
 RSS
R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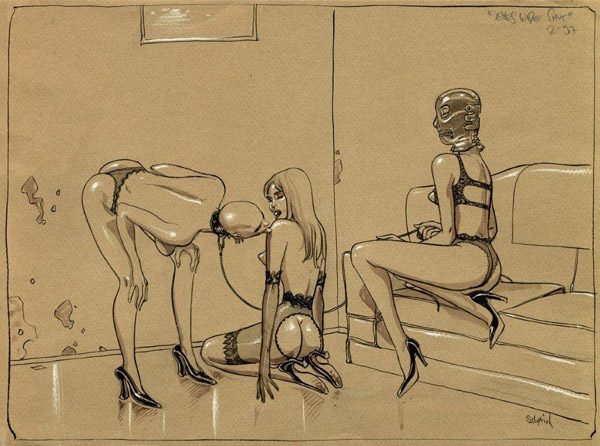

1 жқЎиҜ„и®әдәҶ “зҺӢжҫҚ-йҰ–дҪҚиҺ·еҫ—жҷ®еҲ©е…№е…ӢеҘ–дёӯеӣҪе»әзӯ‘её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