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家”王澍
“我不做‘建筑’,只做‘房子’。房子是业余的建筑。业余的建筑只是不重要的建筑,专业建筑学的问题之一就是把建筑看得太重要。但是,房子比建筑更根本,它紧扣当下的生活,它是朴素的,通常是琐碎的。比建筑更重要的是一个场所的人文气息,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朴素建构手艺中光辉灿烂的语言规范和思想。”

王澍给自己的工作室取名‘业余建筑工作室’,在他看来业余的建筑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批判性的实验建筑态度,但它可能比任何专业建筑学的实验更彻底,更基本。没有彻底性,任何建筑实验活动都将是毫无意义的。
文人王澍
“旧城改造时政府想拆,开发商想拆,住户也想拆,唯一想保护的,也就是我们这些文人。”
“在作为一个建筑师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这是王澍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生活中坚守的信条。
中国古代多的是四体不勤的文人,要么愤世嫉俗躲进自己的小天地,要么曲意逢迎与世俗同流合污。王澍特别欣赏的文人,是清代随园主人袁枚。袁枚35岁辞官后在南京购得一随氏废园,并不大兴土木,也不另赋新名,只是伐恶草、剪虬枝,因树为屋,顺柏成亭,不设围墙,向民众开放。袁枚园居50年,绝意仕进,著作立身,刻意与当时主流社会拉开距离,却树立了文人的另一种生活风范,真正影响了社会。王澍告诉记者,中国文人造园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学活动,人在园在,园子成了有生命的活物,这和今天房子建好后建筑师就掉头不管有着本质的区别。王澍认为,今天的建筑缺少园林的诗意与情趣,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文人与建筑的融合。
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大规模造城运动,这对建筑师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作为文人的王澍却痛心疾首。他甚至认为,全中国的旧建筑都到了要彻底保护的时候,要立即停止拆迁行为。王澍不仅反对所谓的“异地重建”,也反对将老建筑孤零零地设为博物馆。王澍觉得房子和人一样,要活着才有生机,因此他在设计南宋御街时,特意要求保留原住民。在南宋御街陈列馆,王澍特意给民间手工建造留下了一席之地,比如水泥砖墙夯造、木结构桥梁的搭建等。王澍说,这种手工制作方式在欧美已不可能做到,一是造价太高,二是会这种手艺的人越来越少。面对传统与现代、保护与拆迁的冲突,王澍有时也很无奈。王澍指着南宋御街一栋漂亮的老建筑告诉记者:“像住在这样房子里的人,早已不是当初的主人,他们对它其实没有什么感情。旧城改造时政府想拆,开发商想拆,住户也想拆,唯一想保护的,也就是我们这些文人。”
许多人都认为王澍运气好,每次都能遇到一个好甲方。中国美院也有不少人认为,没有院长许江的支持,就不会有今天的象山校区,也就没有王澍的今天。许江在接受采访时并不否认对王澍的欣赏和钟爱,但他同时认为,象山校区的设计机会给了校内每一位教师,只有王澍作好了准备。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王澍时,他很自信地说,他为这个校区已准备了10年。以前的设计体量都很小,凭什么能驾驭这么大的校园?王澍以古人能画小景也能画出《千里江山图》为喻,给出的是一个文人式的回答:“我从来不以大小来衡量我的设计,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他们是做奢侈品的,我是做手工艺的。”和鸟巢、首都机场T3航站楼、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等国外建筑大师的作品不同,王澍的作品大多是低造价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造价,大约是国内同类高校的一半、国外高校的1/10。许多建筑利用了大量废旧的砖瓦,墙面都不抹灰,地面、屋顶等都裸露着水泥,以致许多来此参观的人问学校:你们是不是没有钱了啊?王澍告诉记者,建设节约型校园是一个方面,同时他也想借此表达一种“贫寒的美学”,这也是中国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有钱。况且,光有钱又怎么样,不就是个暴发户吗?”王澍反问。
有人认为,王澍此次获得普利兹克奖,在某种意义上比获得诺贝尔奖更有意义,因为这标志着世界对中国本土建筑文化的认同。相对来说,文化上的认同比起科学研究上的认可要困难得多。王澍自己倒没有想这么多,但也不否认他的建筑里有普世价值的存在。“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王澍说。

从鲁迅到沈从文
完成于2009年的南宋御街陈列馆只有几百平方米,是王澍强调的“以小见大”风格的典型。当《外滩画报》记者提出要以作品为背景采访和拍照时,王澍说:“那就去御街吧。”在御街陈列馆门口,王澍设计了透明钢化玻璃走道和下沉式庭院。参观者走在玻璃路面上,低头就可以看到遗址自下而上叠铺的南宋青砖路、元代大块石路和明清及民国的砖砌路,呈现御街完整的记忆。同时,这也解决了古代遗址和现代交通冲突的问题。
一根根木棍,像藤条一样“编织”成建筑的顶,借鉴了中国桥梁的传统建造方法。“我只是使用一些传统手法,你们感觉这个建筑风格古旧,但整个小楼没一处对古建筑的直接借用,”王澍说:“所以你们觉得这是个‘古’建筑,评价很高。”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引用评审词说明王澍获奖的理由。“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普利兹克建筑奖是每年一次颁给建筑师个人的奖项。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典礼将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届时,王澍将被授予10万美元奖金和一枚铜质勋章。
王澍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他1985年获得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本科学位,三年后从该校研究生毕业。1995年,王澍到同济大学攻读博士,2000年回到中国美术学院工作,从2003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在东南大学建筑系,王澍以狂傲著称,有关他的不少“传说”在建筑界广为流传,其中,版本最多、最知名的是王澍有关“一个半建筑师”的言论——他曾在硕士答辩会现场放言:“中国没有现代建筑师。如果有的话,最多一个半。我算一个,我的导师齐康算半个。”
获得普利兹克奖之后,他的这段“辉煌”经历被媒体反复追问。当记者问及是否确有其事时,王澍哈哈大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事隔多年,衍生出太多版本,以至于我自己都搞不清当年是怎么说的。”他强调,“我只是要表达,中国建筑界虽然不时有思想的火花和批判的意见,却没有持续和深入,没有积累和传承,永远处于开端。”
大二时,王澍公开宣布,自己无课可上,没有老师可以教他。他曾写过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建筑界的状态,从梁思成到导师齐康都被涉及;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死屋手记》为自己的硕士论文命名,影射自己所在的建筑系乃至整个中国建筑界。这篇论文让王澍没能拿到学位,他却连一个字都没改,离开学校时还影印了五本放在学校阅览室。他的一位学弟记得,这篇论文被保存了很久,被后来的学生翻了一遍又一遍。
王澍将自己的经历简单地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言论激烈,1990年代沉寂蛰居,2000年以后埋头工作。王澍记得在毕业十年后,与一位系里的老师碰面时,对方仍然忍不住旧话重提:“每当你从走廊的另外一头走过来,我们都感觉像是一把刀。那把刀寒气逼人,大家都会下意识地避让。”
提及当年的血气方刚,王澍称自己最早受鲁迅的影响很深,思想、言论和行为方式都像刀枪与匕首。后来,自己受沈从文的影响更大。他曾背着行李,按照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行走,用几个月的时间寻找书中提及的村落。“我喜欢沈从文,是因为他的超越性。记得他描写清廷镇压苗族起义,凤凰城头挂着几千颗人头,城边的水被血染红了,但阳光灿烂,青山依旧。这是一种怎样的心境?”王澍说。
眼前的王澍,幽默风趣,常常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早已经蜕去了年少轻狂,似乎有着沈从文式的心境。有一次,一位北京的建筑师带人到王澍设计的一个建筑参观,他惊奇地发现,这个建筑的一部分被拆掉了,变成难看的葡萄架。他打电话给王澍,气愤地说:“你知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建筑在建筑史上的地位吗?”王澍淡定地告诉他,这并不意外,在设计这个作品时,就有人要把这个部分拆掉。
事实上,王澍的很多作品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如1989年建成的杭州国旅航空售票处、1991年建成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国际画廊、杭州孤山室内小剧场和杭州斗乐桥人防地道口等都已被拆毁,时间最短的只存在了3个月。“不仅是我的作品,建筑史上很多里程碑式的作品都被拆除或破坏了,我并不是那种追求所谓永恒作品的完美建筑师。我感兴趣的是我的作品在中国社会中的变化,”王澍告诉记者:“我并不愤怒,因为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中国。”

“业余”建筑师
王澍第一个独立设计的建筑项目是为海宁设计的青少年中心,于1990年完成。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他和同为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在杭州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没有接过任何项目,偶尔帮别人画几张图纸补贴家用;他读了大量书,却不看建筑类书籍。
1997年,王澍重操旧业,设计了使用面积只有五十多平米的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阳台上搭了个亭子,又在家里做了八个木头的两层灯具。在王澍看来,这些灯界定了人和世界或者是建筑里两层空间的最基本关系,很像一种智力游戏。王澍用“八间不能住的房子”形容这组作品。
也是在这一年,王澍和妻子在杭州创办了“业余建筑工作室”。“不谈建筑,只谈房子,所以就是业余的,业余建筑。”这是王澍常说的一句话。关于“业余”,王澍有自己的理解:“业余这个词意味着一个因为兴趣而从事某项研究、运动或者行为,而不是因为物质利益和专业因素。对我而言,不管是一个工匠还是业余的,都是一样的。”
三年之后,王澍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重要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这个作品体现了他的建筑哲学,即如何让建筑自然地存在于山水之间。这座图书馆近一半体积处理成半地下,四个散落的小建筑尺度明显小于主体建筑。
2000年以后,王澍不再言辞激烈,而是埋头工作,但他的作品却一直备受争议。他说:“我从来没有妥协过。作为建筑师,能够说服别人和自己一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这是一种能力。”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一、二期工程,是王澍最重要的代表作。象山校园无论体量还是建造规模都是惊人的,很多建筑形式都是王澍独创的。这里的建筑相对集中,更多土地被营造成自然环境,30座大小不一的建筑点缀在杭州南部依山的农田中,很多地方可以种菜养殖。
象山校园预算只有同时期杭州其他大学城项目的一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提出的要求却是要建造原创的、具有国际水平的校园。王澍告诉许江,这可以实现,但他需要绝对的自由。许江答应了。项目建成后,许江惊喜万分。他漫步校园,猛然发现,对面景色与宋代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颇为相似。王澍说:“你发现了?”对于建筑师而言,建筑摆在什么位置,门洞怎么开,如何控制建筑与山的距离,都是需要仔细估算的。王澍喜欢做这样的事,做完后等别人自己发现。
象山校园的所有建筑墙面都不抹灰,院子只造三面,瓦片用旧的,工匠如同在家里劳作般“随意砌”。工人们用了700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屋顶坡度介于平屋顶和坡屋顶之间,房子从一个面看去完全像是平顶,从另一个面看去则是坡顶。
坊间对于这个建筑群的批评从未间断。那些不规则的走廊和“诡异”的楼梯,让很多人迷路,形同迷宫;每幢楼的窗子都开得很小,学生白天上课也要开灯,灯不够亮都看不清;楼里只有极少的空间安装了空调,以至于大多数的房子“冬冷夏热”。外界对象山校区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把象山校园归为杭州最丑陋的建筑;另外一方则把它与央视大楼相提并论,分别引领中国建筑截然不同的方向。
杭州住宅楼钱江时代是王澍迄今为止唯一的商业住宅项目,开发商是通策集团。住宅是城市建筑中的主体,作为建筑师,王澍希望介入这类项目,直接面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并给予正面的回答。但他的想法商业风险极高,从开始有意向做这个项目,到最终做出决定,王澍和开发商一起喝茶聊天长达两年。终于有一天,开发商对王澍说:“下定决心要做了,我们也理想主义一次。”
王澍打算从中国人原本的生活经验出发设计这个住宅项目。第一次把图拿给开发商时,王澍画的是一个只有两层楼的小盒子,盒子里有四到六户人家。不管最终高层建筑有多高,他想要让住在里面的人回到记忆中生活的两层楼的时代。每家有一个很深的阳台,或者说是院子,院子里有1米以上的浮土,可以种植6米以下的植物。王澍希望:“小区居民可以站在远方,指着那个种着桂花树的地方说:‘看!那就是我家!’”于是,这些两层楼盒子被叠加起来,形成六栋高层建筑,就是现在的钱江时代小区。打造新邻里关系和垂直院宅的理想主义的初衷在有些住户心中并未实现,穿插堆叠形成的错层阳台方便了小偷,钱江时代小区也曾因此登上了杭州报纸的社会新闻版。
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消息传出后,通策集团在微博上说:“王澍获奖,是迟早的事。一个生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的真诚甚至天真的人,总有一天会让人相信,他的艺术世界是真实的。通策人永远会记得与王澍合作的那些痛苦与欢乐并存的时光,更记得那些只存在于图纸上的项目,当一些人向王澍伸出表示祝贺的手的时候,他已经忘了也许是他枪毙过王澍的不少灵感。”

王澍的家
用建筑来写作
一位外国记者曾问王澍:“如果不做建筑师,你会选择做什么工作?”“我想我会是不错的作家。”王澍马上回答。他表示无论是古旧的瓦还是钢筋混凝土,都只是自己写作的工具。
在南宋御街陈列馆顶层,王澍给自己留了个地方。那是一块不大的、两边开放的平台,头顶就是整个建筑的木顶。王澍在封闭的两端布置了长条木凳,指着两排凳子,他说,自己的私心是有一天可以在这里讲学。他的“私心”还体现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14号楼楼顶,也是设想的能上课的地方。
王澍一直有古典文人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解惑的强烈愿望。早在为象山校区选址时,许江和他就带着恢复中国传统书院的想法。“大学应该是在山边有组院子,没有入学和毕业考试,学生可以随时进,随时出,就好像孔子带弟子,流动性很大,随时有变化。”王澍说,这种理想奠定了他作品的基本气质。
王澍有几十张古代书画的珂罗版,用来研究传统绘画。王澍常借这些画作来阐释自己的作品:“有人说从象山校区建筑的屋檐上看到沈周的长线条,从校园里大尺度的连续控制中看到夏圭的痕迹,细腻之处跟李公麟接近。当然和巨然的层峦叠嶂比我还差很多,现在只能说努力向董源的感觉靠近。”进入大学后,王澍开始临帖,最开始是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这个爱好;大三时,他把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论》翻烂了,还能倒背《世说新语》。
他可以连续几天陪妻子逛商场,不知疲倦,他说其实自己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生活;也能够在西湖边坐一整天,看日出日落,一言不发。王澍一直是个不怕孤独的人,研究生时,他曾经在农村住了两年,看书、写字、爬山,独自面对漆黑的夜晚;跟王澍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手机之于王澍并不是即时通讯工具,他极少接手机,偶尔回短信。在得奖的消息发布后,一位青年建筑师给王澍发了8条短信,几天后,王澍回了一条。这个建筑师兴奋地把这些通讯记录发到了网上。“这个消息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因为不会用互联网。”王澍说。
王澍出生于新疆,在西安考的大学。他从小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但是父母却坚持让他学科学。最终,王澍学了建筑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如果一定要说有家学渊源,王澍说来自父亲。父亲的工作是拉小提琴,但从来不在家里拉琴,在家的时候只喜欢做木工。在王澍的印象中,幼时的家里有很多木工工具,自己经常给父亲打下手,做好木工上油漆之前打砂皮。父亲是一个兴趣很多的人,在家的时候会用花盆做小麦品种的改良实验,后来,王澍在象山校区种起了麦子。王澍的儿子今年十岁,名叫斗拱。斗拱小时候在野外玩,脸上被蚊子叮出红疙瘩。同行的人要给他抹风油精,王澍却说:“没关系,应该让孩子适应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家里发现蜘蛛,陆文宇要消灭,王澍总是将其救下,要与它休戚与共。在王澍主持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大一学生都要学习砌墙、木工。带木工课的陆文宇记得,连开水都不会打的孩子们做木工时手被扎出血,磨出老茧。“但做成之后每个人都很兴奋,都要让我坐一下他们亲手做的小板凳。”对于学生的教育,王澍的目标是把他们培养成“哲匠”。

实验建筑运动
2月27日晚上,网络上流传王澍是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的消息。这个消息一度受到质疑,几个小时后,普利兹克建筑奖官方网站正式宣布王澍得奖。对陆文宇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她不断收到各种短信与电话,“简直是炸了锅。”此时,大洋彼岸,王澍正在熟睡。他刚到美国,需要倒时差,蒙头大睡,怎么也醒不过来。到了11点多,王澍查看手机时,刚好接到陆文宇的越洋电话。“你知道普利兹克奖已经宣布了吗?”陆文宇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王澍反问。得知自己得奖,王澍很惊讶。
1983年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获得这个大奖,这一年,他66岁。早在三年前,就有人预言,如果中国有一个人得到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个人肯定是王澍。即便如此,包括王澍在内,所有人都觉得要得奖还需要十年。
一直以来,王澍都被归为“实验建筑运动”一分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获得普利兹克奖,很大程度是因为评委们发现,这种原本只能设计艺术家工作室、茶室等小型建筑的艺术探索,竟被如此大面积地实现了。他说:“直到得奖,我才惊异地发现,原来过去十多年里,我做了如此之多的项目。”
作为实验建筑的代表人物,王澍曾经三次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时至今日,我在国外做讲座时,会有人对我说,你2006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瓦园’真的很震撼。”王澍说。王澍最初设想把25万片拆迁下来的旧瓦带到威尼斯,代表中国城市的大拆迁。后来,瓦片数减少到6万片。“运过去时,海关一打开,里面都是灰,海关问是什么,我们说这是中国的废品,就象征性地报了个价。”中国当代建筑研究学者王明贤回忆:“西方盖一个建筑,是把旧的推翻,用新材料重做,但中国老建筑的旧材料可以继续用,建筑可以再生。威尼斯双年展是很喧闹的地方,可看到‘瓦园’,人们就会变得安静,这是让人沉思的地方,让人沉思建筑到底该怎么发展,城市该怎么发展。”
早在25年前,王明贤就与王澍相识,他把王澍称作实验建筑最重要的代表,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师之一。王澍的刻苦、克制与坚持被认为是他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他坚持“实验”十几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其他建筑师身上出现的“分裂”现象。
在王明贤看来,很多现代建筑和城市的关系很突兀,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提醒了整个世界建筑界,中国有这样一条独特的建筑道路,对世界建筑而言是补充或者新的出路。王澍也表示,有一群建筑师,在做不起眼的建筑,这不是因为他们年轻或者分量不够,而是选择了一条反标志建筑和巨大建筑的道路,自己得奖是对这个群体的巨大鼓励。
“我在学生时代已经很突出了,很多同学很羡慕我的工作状态,但是他们又说,等我赚到钱或等我评上职称了,我就像你一样工作,”王澍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但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到他们赚够了钱、评上了职称,就已经在另外一王澍在杭州南宋御街陈列馆内条路上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了。”

王澍访谈:“异类”的胜利
《中国周刊》对话王澍–建筑师不该失去自省的力量
功利心已经主宰了一切
Q:你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城市,出现越来越多的“地标性建筑”和“标志性建筑”?
A:我是反对所谓的“标志性建筑”的。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时代权力的宣誓,也是集中了商业力量的宣誓。它一方面用大的物质体积来做标识,另一方面掩盖了所在城市里大量历史建筑被拆毁的事实,更对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瓦解视而不见。我认为这类的标志性建筑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反标志性建筑师”。
Q: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标志性建筑”在中国颇有市场。从建筑师的角度,抛却行政和政策压力,需要进行某种反思吗?
A:这个时代,建筑师掌握了太大的权力,而他们在运用这些权力时或许从未想过自己凭什么拥有这些权力。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设计和建筑,对人的生活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你还不做自觉的反向的思考和批判。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建筑师就失去了他在这个时代应该有的自省的力量。这是非常危险的。
Q:“危险”指的是什么?
A:我们的城市,只能进行平庸的批量生产。更高,体量更大,更加夺人眼球,这就是所谓的地标建筑。有人做过统计,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拆毁了将近90%的传统建筑,外形雷同的高楼在一片拆迁的废墟上拔地而起。说的极端一些,我们的城市模样,正在被一群外国人重新塑造。
Q:这个过程中,建筑师应该负有某种责任?
A:现中国复制了那么多“垃圾般的房地产”,都是建筑师干的,建筑师变成了房地产商和开发商的同谋,变成了这个时代这种趋势的同谋。大规模开发之后,建筑和街道只能看不能用,人性消失了,如自然一样生长起来的东西被挤压得没有余地。当你看到有那么多的材料,原来非常有尊严地呆在老建筑上,忽然变成像垃圾一样被扔在地上的时候,作为一个建筑师,不能视而不见,否则就是无德。如果仅仅把建筑师作为一个职业,是很猥琐的。这个时代固然有问题,但建筑师不应把这些外在条件作为自己不能做很好设计的理由。外在的东西有时我们很难左右,但设计师首先可以做自我批判。这是我的立场。
Q:为什么会这样?
A:功利心,这个时代,功利心已经主宰了中国的一切。失落了真实的历史,就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Q:在你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怎样一种建筑?
A:这需要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失去了什么。中国曾经是在城市和乡村都遍布诗意的国家,经历一百年的巨变之后,这种诗意还存在么?
我做过一个统计,本土建筑在传统文化城市中的比例已经不到10%。我们在过去二十几年,消灭了自己过往的建筑90%以上。城市保有的剩下的一点点传统建筑,只在5%-10%之间。这还是指历史文化传统城市,其他更不用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城市里头的传统和文化基本上完蛋了。在我看来,如果建筑能穿过百年、千年持续地存在,这就是挺让人感动的事情。
Q:某种程度上,是要恢复和保留我们的传统吗?
A:在我某天走过一个街的拐角时,如果我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堵墙看起来像是断壁残垣,但当它剥落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的东西非常有条理,黄土、抹灰、砖头这三种东西很有序地结合在一起。我不会想到这是一堵破墙坏掉了,可以重新去翻新它,这是一种时间的过程自然产生的东西。事实上我们讨论的传统,它和未来直接相关。保护传统的目的,是要保有我们的未来。我们在逐渐失去自己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的同时,还在抄袭世界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文化都不爱惜,又如何要求别人尊重你?
Q:我们自己会迷失?
A:如果我们失落了真实的历史,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Q:对此,你的主张是什么?
A:我主张,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那个地方的文化根源,顺其自然、因地制宜。当然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当时在杭州做象山校园,有人说里面怎么还有北方建筑的影子。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定型的讨论,每个地域由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来形成其特殊的东西。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怎么样恢复中国曾经有过的伟大体系,从这个体系中可以看到整个文化的共通点,它分享着某种共通的理念和结构,但在每个地区又有着如此丰富的变化。我认为这种多样性的保持是中国文化里最宝贵的。
Q:具体怎么做?
A:我们传统的建筑一向都是善于回收利用,我们的传统理念中关于“可持续发展”是有一套特殊的办法的,用料不昂贵,表面上看上去容易朽坏,但采用“拆一块补一块修一块”的循环办法,使得很多建筑能维持五百年、一千年,甚至更久。现代的建造使得传统的体系被中断,传统的建筑拆后材料被扔掉,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我们需要用一种具体的方式使这些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而不是采取作秀的方式,用所谓传统元素或符号来假装传统文化还在。
Q:你对此感到乐观吗?
A: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的语境下按照自己的文化脉络、逻辑来演变,而不是用西方的东西来进行粗暴的替换。这样的突围,不仅仅是建筑界所应做的突围,而是这个时期大家整体应有的思维。很多人问我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和追回的可能,我就是一句话,我说哀莫大于心死,这就是我对中国城市现状的看法,我基本是绝望的。
我们阻挡不了功利心摧毁我们的历史。建筑,只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吧。
Q:你如何看待一些文化人和老百姓自发进行的保护传统的行为?
A:我是持肯定态度的。我并不是精英建筑师,认为我们设计的东西更美,说那种东西是“乱七八糟”的,要对其进行清理。从这个方面来讲,我是自觉地站在这个文明状态下弱势群体一方的。
生活不可以被简单化的
Q:你有一个让人感觉有些怪的观点,你不做“建筑”,只做“房子”。怎么理解?
A:对我而言,建筑的根本是自发建造的,是源自日常生活的。我认为建筑不是艺术殿堂里的高级艺术品,建筑活动是人类的一个生存行为。我的建筑试图将这种生存行为,同它所带来的真正存在的感觉联系起来,做“存在感的建筑”。我是“玩味生活复杂性的建筑师”。我从来不认为生活是可以被简单简化的。现代主义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试图以简化生活为前提。这对整个人类文明带来了摧毁性的能量。
Q:“房子”这个概念,给人的感觉,是和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
A:对。中国正经历一个特殊时期,如此巨量的建筑建设,导致城市规划活动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在历史上都不多见的,而我们正好碰到了。这时建筑不止是建筑,它里面所带有价值观、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它是人的一个基本生存活动,是人的需要。
Q:现代住宅设计来源于西方,你似乎对西方建筑理念并不那么认同。
A:我从来都不是简单地认同西方的建筑观念,然后回过头来批判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体现了很多很重要的想法,比如:它起源时并不是简单的艺术行为,是为了解决战后出现的居住问题,是从住宅开始的。因此它最初是一个社会运动,而非艺术运动。这种精神在后来的商业化过程中被逐渐丢失,变成了所谓的国际化风格,一些原初的理想在商业化过程中被消费。如果讨论西方建筑的话,我一直努力让那时的出发点得以回归。对中国的传统建筑、对我们的“房子”,我也持这样的观念。

王澍详细介绍>>王澍-首位获得普利兹克奖中国建筑师
[请保留:后时代 http://www.houshidai.com/]
 RSS
R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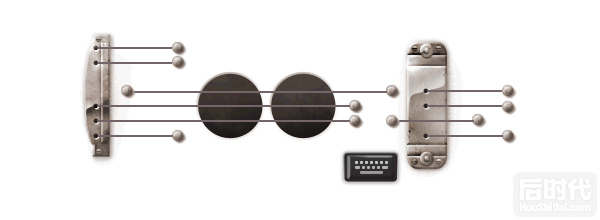



3 条评论了 ““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家”王澍”
王树根本不懂中国建筑,他的建筑形式无非是像西方现代建筑谄媚,打着民族的幌子招摇,在中国建筑的表皮下宣扬的却是西方价值观,叫人哭笑不得。
你说的在某方面确实有些道理,狭隘的民族主义源于内心深处的自卑。但请至少把设计师的名字写对,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
名字写对了也不能改变他的没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