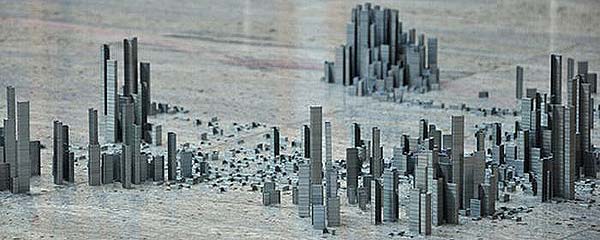朱锷与深泽直人的设计对话

深泽直人访谈视频
深泽直人访谈(深泽直人与朱锷关于设计的对话):深泽直人对于设计的观点
深泽: 对, 并且从一开始就觉得日本的工业设计很落后。(笑)我也曾努力想要改变现状,也曾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行当。产品设计或者说工业设计这一行的内部结构实在太复杂。如果能像刚才大贯先生那样,从客观的角度提出改进的意见还算好,一旦自己深入其中,才发现要想在这一行里做一些改变实在是不容易。我也是从三十岁到三十五岁花了五年时间才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即使自己能突然改变自己,但是不可能突然改变整个社会,所以就只好从自己身边做起,一点一点地慢慢来,到今天还是这样在做。
朱锷:你当时是从哪儿找到突破点的呢?
深泽: 可能是在美国吧, 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自己终于从日本工业设计那个错综复杂的圈子里逃出来了。
朱锷:你设计过一种手表吧,户外型、数字显示的那种。
深泽:叫“AVOCET” ?
朱锷: 那个造型让我很吃惊, 因为那和现在让人一目了然的“深泽风格”的作品完全不同。我当时是冲着手表的外型看上去很“美国味儿”才买的,却没想到设计师原来是日本人。
深泽:我也听说那表在日本卖得还好,你也买了吗?
朱锷:完全是偶然,买的时候一点都不知道是你设计的,知道以后才觉得吃惊。其实我还买过不少你设计的其他作品呢。(笑)无印良品的那个,外型看上去好像排风扇一样的CD机,我买过十几个呢,都当作礼物送给朋友们了。
深泽:拿那个作礼物送人是不错。
朱锷:那简直是最合适而且是很典型的“日本特产”,那个作品很恰当很微妙地表现出了日本人对美的意识。CD机的开关不是按纽,而是过去的那种拉绳式,这就别具一格。现在的电器产品已经不会再想到采用那样的设计,而且还得冒着拉绳是否保险的争议。但是那个作品的精妙之处也正体现在这根拉绳上,将这台挂在墙上的“排风扇”轻轻一拉,代替清风翩然而起的却是音乐声,这个创意实在是太不同凡响了,第一次使用的人大概都吃了一惊。
深泽:那个CD机在打开后有一小段的停顿,因为要等马达在启动后安定下来,所以拉下开关以后过一小会儿音乐才会响起。不仅这台CD机,一般的电风扇和换气扇也是这样,因为它们使用的都是同一种马达,所以也是按下开关后要等一会儿机器才开始运行。
朱锷:这个停顿是您在一开始就设计好的效果呢,还是只是偶然?
深泽:是在一开始就计算好的。其实我是在看了马达的运行效果后受到的启发,才决定开关必须用拉绳式的。那个开关是由香港的一个厂家生产的,据说开关的接头越短精度越强,所以开始的时候就试用了那种短接头,结果一拉绳子,机器就立刻开始运转,完全没有停顿的时间。我们就又改订做接头长的开关,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人家说如今早就不生产那种开关了。我们只好在秋叶原到处找,买到早先那种一按先咔哒响一声才亮的日光灯,再拿去给人家演示,因为如果生产不出那种先咔哒一声,等会儿才响音乐的开关,就制造不出我们所追求的那段空白效果。
朱锷:现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了,这种开关和这种设计方案,这也正是你的设计总是不同一般的地方。
深泽:承蒙你这么夸奖。有时候和别的设计师的这种对谈,会让我觉得挺不好意思。你的设计我看过不少,原研哉这次又给我看了你这次给隈研吾做的平面设计的资料,觉得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其中对于空白画面的设计处理,呈现着一种很好的幽默效果。
朱锷:但其实我从不刻意地追求幽默,你在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也不会把幽默当成重心去考虑对吧?
深泽: 我不会把幽默当成是自己作品的卖点。相反我觉得我的设计其实很严肃。幽默效果的形成,说白了就是让对方感觉不好意思。比如说针对某件事,如果你很严肃地指出对方的失误,说“你是不是这样?!”,那么对方就会表现得很吃惊和慌张,但如果你换一种缓和的角度和方式指出来,对方的反应可能就会是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作品中的幽默其实给人更多的是这种不好意思的感觉。我在设计的时候,有时候因为精神过于集中,会不自觉地把我个人的意愿和主张暴露出来,那时我会用一点幽默来遮掩一下。
朱锷:说到这儿,我觉得您最近的作品都透着一种很强烈的“This is 深泽直人”的感觉。
深泽:我自己倒是感觉不到。
朱锷:我能感觉到,而且一直想问问,你是有意识的在作品上都露出“深泽直人”的痕迹吗?因为你既然创出了“深泽直人”的牌子,那么推出的产品当然得符合“深泽直人”的风格。所以你现在在设计的时候,是否会刻意地沿用这种风格?
深泽: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尖锐。我个人倒是不希望被固定于某种风格之中。但是我的设计对象和你所从事的“形象设计”不同,我设计的说白了都是某种道具或工具,既然是工具,在设计的时候就必须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它的功能,在这种限制下,我所做的其实不同于作家,没有他们那么广阔的表现空间,作品大概也就因此而不免显得千篇一律了。
朱锷:你现在的工作不就是应该做“深泽直人”吗,特别是你在这次米兰家具设计展(MILANO SALONE)上的表现。
深泽:媒体都是这么宣传,有时候也会有过头的报道。
朱锷:但是正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在你的设计中确实着重体现着一种日本人对美的意识吧。
深泽:对,我的这种意识确实很强烈,但并不因此会刻意地去制造一些所谓的“日式风格”。
朱锷:拿我们刚才提到的空白效果来说,也有人将它形容成一种惆怅,一种日本式的美感。无论别人怎么称呼或评价,我觉得你的作品中确实很有这种味道。难怪你会被誉为日本设计师的代表呢,海外正是通过你的作品,才感悟到了这种日本式空白的美。
深泽:与其说我代表了日本,不如说我是连接在海外与日本之间的一条锁链。我自己是深爱日本文化的,我认为我是。我也很想能代表日本,但是我的形象实在太不够格了。真正体现日本美的不是我,而是高仓健。(笑) 他才称得上是日本文化的典型代表,征服了全世界。银幕上高仓健的形象总是那么孤独,要么是心里有喜欢的人说不出口,要么是明明很无辜却无端被卷进阴谋的旋涡,最后的结局总是以高仓健寂寞的离去而告终。他是一个典型的“隐士”,永远住在一间狭小又干净的房间里,一旦要离去,所有的行李就只是一只很小的皮包。永远将自己的生活水准保持在最低需求(笑),一只皮包就能了结一个人生。这我做不到(笑)。用一只皮包就可以整理好自己生活的全部,我认为这其实与日本的文化很合拍。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时候一条手巾就可以解决全部的问题,它体现的是最低限度而又最实用的价值。我向往的正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价值观,不是高仓健的潇洒(笑)。比起一块简单的手巾,可能有人认为设计蓬松柔软的高级毛巾的人,才更配称得上是设计师。但我认为一块手巾,既能擦脸又能洗澡,这种最简单又最充分的价值体现才最高级。
朱锷:你谈的也是你的设计理念中很重要的一点吧。
深泽:对,每当我发现自己的设计有要表现“高级毛巾”的倾向时,就会尽量回避。
朱锷:你的很多创意都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比如那个架在地缝上的伞架,就很实用。
深泽: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自己确实有这种倾向,注重现实和实用性,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关系吧(笑)。
朱锷:现在设计成了一个越来越热门的行业,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深泽:其实我的职业与其说是设计,不如说是我通过自己的作品在向生活提出一个“看!”的建议,如果是抱着这种拿出作品给大家“看”,让大家来评价的心态,那么设计师在对事物观察和构思时的出发点就会有所不同,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么设计这一行越来越热门并没有什么不好。
朱锷:你用“看!”来归结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这感觉听上去很好啊,我就不太喜欢那种拿着自己的设计到处问“您觉得怎么样?”的故作谦虚的姿态。
深泽:我选择用“看!”是觉得这个字比较随意和亲切,不让人觉得太严肃和沉重。
朱锷:但是你的作品恰恰相反,给人的往往是一针见血、直奔主题的印象。
深泽:你别把我得作品形容得跟日本刀似的。倒是我看你的平面作品里好像总会有一个声音在向观众说“看!”
朱锷:是吗?其实我觉得自己更是一个“平面设计批评人”,看到不满意的地方就想要改变,有时采取的可能是会比“看!”更直接和强烈的表现方式。
深泽:有。我觉得人的本性就是这样:觉得自己的心思被看穿了会难为情,听到自己的心思被说穿了会想逃走。你的设计作品给人的感觉,就是针对人的这种心态,把那些隐秘的心思真实而突然地抖露在人前,造成的就是一种既让人惊喜又不免有些为难的效果。
朱锷:你对品牌设计怎么看?
深泽:这很难说。
朱锷:我觉得如果你做些和你完全无关的品牌设计,应该会很适合你。比如说,现在无印良品是你的标志性品牌,你有没有想过甩开它,去全面负责ASKUL,或者松下电器的设计?
深泽:其实,我自己也在尝试着这样做,但一旦我个人的名字太鲜明突出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因为日本民族归根结底是个崇尚平均主义的民族,如果我一个人就能面面俱到并且成绩很好,那在日本这种文化里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无印良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是在田中一光身边待过的,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朱锷:有这么严重吗?
深泽:我认为有。MUJI这个品牌在这一点上就非常好。我为他们设计过很多产品,但是他们从不拿我的名字当招牌,这样我在设计的时候就感觉很轻松。相反,如果哪个品牌打着我的旗号做宣传的话,就会让我有尽快逃走的冲动。对我来说,为有名品牌做设计,不如将自己隐藏在某个无名的世俗角落里,用自己的设计来给周围平庸的气氛带来一些变化,然后在这些变化渐成气候的时候,隐身而退,任身后留下的影响散播或渗透,有时候真想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作为设计师,这种任性其实很危险,所以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好。
朱锷:要真能那样的话,哪怕只是播下点种子,再隐身而退也好呀。
深泽: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属于“隐士”型的人,做了很多事情,但在幕前却看不到你。
朱锷:我确实是个比较正统守旧的人(笑)。刚进入日本设计界时,看见周围设计师们的作品都极有个性,所以觉得自己也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就决定干脆把自己的个性完全隐藏了起来,当作是我的特色。
深泽:在产品设计这一行里,有很多人认为必须先打出名声才能夺天下。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设计的对象,都是那些要在工厂里批量生产的产品,有什么必要非把自己的名字贴在那上面呢。
朱锷:但是不贴的话,也就没有如今的“深泽直人”这个品牌了。
深泽:希望你将来有机会也做些产品设计。
朱锷:我自己也很想能有机会尝试一下。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曾经全面否定过我们的平面设计,那种用高级字体把商品写得看上去很高级的宣传方法,实在很落伍。我设计的版面,内容永远只占中心那一部分,中心或者中心靠下,因为我不愿意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设计的矫饰,所以我从不用那些多余的东西。如果我这样也可以做产品设计的话,那么做做也行。
深泽:可是大家不是认为你的作品很好看吗,我也很喜欢那些真正好看的东西,但是不喜欢那种故意装饰出来的肤浅的好看。
朱锷:我始终认为以内容为中心的设计最好看。你的产品设计,更像是对实际生活的建议,或者说是站在使用者的立场上对现状进行批评和改造。这一点,在现在平面设计行业里也有所体现,现在的平面设计师简直就是站在与这个行业完全对立的立场上,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一般是从这个商品究竟如何开始讨论,到生产它的这家公司究竟如何为止,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将一个商品了解得比较透彻。所以今天的平面设计行业里,包括我自己在内,几乎每个设计师都忍不住想向他们的客户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或建议, 而且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所以最近,我常反思,平面设计的工作原来并不是这样呀,我的职业是平面设计师呀,然后再回过头,用“设计师的工作并不只是设计画面”来安慰自己。
深泽:这样一比较的话,我在设计这一行里,算是从一开始就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单纯的领域里。
朱锷:产品设计相对来说确实单纯,这点很让人羡慕,看到自己设想的方案能够彻底地实现,非常有利于设计师的身心健康。
深泽:有利于健康(笑)。
朱锷:真的是这样,像我们做平面设计的,有时候不得不将自己的工作放在一边,来解决客户突然提出的和设计完全无关的问题。
深泽:产品设计的工作性质,基本上是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做出相应的产品,所以设计出来的东西一般来讲不会有太大偏离。但是平面在设计的时候,创意的空间大,让客户满意的难度就相对比较大了。
朱锷:如果遇到销售对象是女性的商品,我就要先假设自己是个女人(笑),试着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来构思,但是结果往往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有时候真觉得去做实际的产品设计可能会更开心。
深泽:但是产品设计也会遇到各种限制,如果是设计家具的话,还有比较大的自由空间,如果是设计现在的那些电子产品的话,就很受局限了。经常是商家把图纸往你面前一摆,让你照着样儿来设计,如果只是技术上的局限还好,但是这类产品往往还附带有品牌厂家的局限,和来自日本社会的局限,很复杂。所以如果设计的对象是家具或者是来自欧洲的客户,在这方面就很简单,不会太受约束。但是面对这种客户,就要求设计师使出百分之百的力气来拿出优秀的作品,不然的话人家根本不会买你的账。
朱锷:平面设计就不像产品设计那样受到技术性的限制,但是会受到预算的限制(笑)。
深泽:平面设计不像产品设计那样容易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形状上,但是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媒体的限制,究竟哪边的局限性更大,不好比较。但是产品设计确实有它很复杂很麻烦的一面。
朱锷:你有过明明设想得很好,但真正做起来却行不通的情况吗?
深泽:有过很多次。如果明知如此还坚持,就是外行。我也曾经觉得“别人做不出来的我来做”很酷,但是其实是很傻(笑)。设计不是赌博,首先得搞清楚自己的方案究竟能不能实行。
朱锷:其实有时候有局限才更有意思,在各种制约下仍能做到充分表现自己,很有成就感。
深泽:想起三宅一生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现在耍小聪明的设计特别多,设计出来的产品虽然看上去很精巧,但其实都是一些‘精致的垃圾’。”(笑)我觉得他的这个比喻很贴切,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有这样的倾向,设计过于追求漂亮精致,但其实都是不实用的垃圾。
朱锷:不是有个电视节目叫《大改造!!装修前后的巨变》吗,一想到今后日本人家里都照着那样布置就让我不寒而栗,那么简洁、精致,连老太太看了都会觉得“真漂亮”,但是一挪到自己家里,一点都不相称(笑)。设计有时候很难把握,深泽先生也有体会吧,即使自己设计的产品本身再好,但是要做到与周围合拍也很困难,有时越精致越困难。
深泽:可是又不能说单是为了与周围乱七八糟的环境相称而去设计,这确实是个很难解决的矛盾。
朱锷:其实我觉得和现代相反,以前那种日本家庭的感觉更好,虽然乱糟糟的,但是有那么一种只有日本人家里才有的独特气氛(笑)。
深泽: 是啊, 那也是一种日本文化呀。我在《大改造!!》那个节目里,看见过脏乱得不得了的人家,那家人在工人来改造之前不是得先搬出去吗,等家具全部搬空了,我发现房子本身即使不做任何改造也挺好的。所以其实有时候需要改造的不是房子,而是居住其中的人的问题。
朱锷:所以有时候一想到日本文化中特有的,即使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一些东西在渐渐消失,就会让我有种莫名的不安。拿我本人来说,吃饭还是喜欢吃学生食堂里那种便宜饭,有时候快餐也能吃得很香。深泽先生呢,你喜欢过那种很摩登很具有现代”设计“感觉的生活吗?
深泽:我有时候也觉得能生活在自己喜欢的设计空间里会挺好的,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很随意(笑),有时候也会大半夜的跑出去吃松屋的便宜套餐,好像那种日子才过得更有滋味(笑)。我给你说一件我最近发现的很有意思的事:我现在也在大学里教书,学生们不久前都还是高三或者高考复读的学生,这些每天都会在原宿大街上溜溜达达的男孩女孩们,曾经对服装和流行是那么的敏感和挑剔。但一旦进了美术大学,在完成我留的设计一双鞋的作业时,他们原有的那种客观和挑剔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大家一下子都变成了“设计师”,开始发表各自的设计理论。曾经对别人的服饰随口就评价“真土”或“真可爱”的孩子们,如果用他们那时的眼光来做设计,会是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但一旦坐到了“设计师”的位置上,轮到自己来设计,就失去了原来的客观性了。他们的这种状态,要想提高设计质量就得花很大的力气。即使他们中偶尔有谁拿出一两件不错的作品,也只不过是外行人的巧合。只有做到设计一百回,一百回都能保持客观思维的,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设计师。能做到这样,设计出的作品才不会有偏差。
朱锷:听说你每次只给客户提交一个方案。
深泽:对。
朱锷:方案很快就能确定下来吗?
深泽:对,很快。
朱锷:真让人羡慕(笑)。
深泽:我的制作过程也很花时间,只不过最初创意的时间很短。经常会有客户提出想看我的设计图,但是我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不画图纸,当然有时也在纸上大概划拉两下,只是为了给助手说明时用,仅此而已。我把我的创意用图大概画一下,拿给他们“看”,助手们如果点头称是,就说明他们理解了我的意图,那么他们自己就应该能画出图纸,但是如果他们的反应是含糊不清,我就要重新考虑一下是否是我的创意存在问题。
 RSS
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