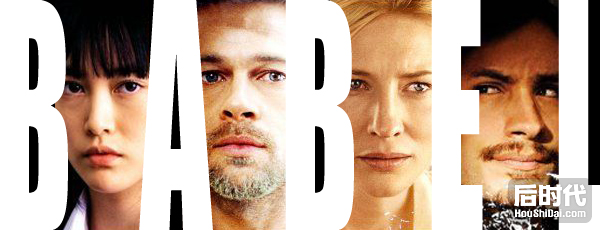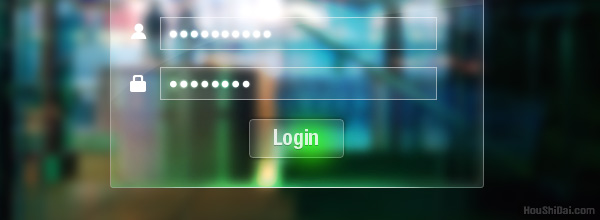《心房客》孤独是最终生活的谜底

“土星环是太空的婚戒。”
“其实在看的过程中,哈哈大笑的时间比感受孤寂多的多。一直到整部片结束,回头想想才发现,啊对,他们都很寂寞!”
荒唐巧合、意外反转的事件之下,冷漠疏离的人际表象之下,哀伤孤独的个体遇到了另一个哀伤孤独的个体,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彼此救赎。

真正的孤独,有时并非是孤身一人,而是我们与人群为伍,但却永远无法沟通。每天,很多人彼此擦肩而过,寒暄微笑,但就是无法走进内心,我们漂浮在彼此的周围,像原子、如孤岛,像两块磁石,彼此都是同类,却始终无法相吸,但作为人类,却又永远无法适应彻底的孤绝,那种对于沟通和交流的欲望,在困窘的现实面前,显得更加令人心碎。
这部《心房客》在风格归类中被划分为喜剧,这种归类本身总流露出一丝残忍的味道,很多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都因为其中那些幽默的细节,被归类为喜剧,比如那部《完美陌生人》,但它们真的算喜剧吗?那些令人发笑的桥段和细节,总能让人们在嘴角上翘之后,心里顿时涌满悲凉。从这个意义上说,《心房客》只不过忠实地倒模了生活本身。这部电影有时会让人想起那部《处子之山》,一样的孤寂,一样的清冷,只不过相较于那种“个体的孤独”,《心房客》展示了一种群体中的孤独。

一桩老公寓中的六个人,三段偶遇,陌生的人们萍水相逢,但又戛然而止。这看似平淡的故事中有着令人窒息的留白,每个人的内心都在翻腾,但表面上都装作波澜不惊。那些情感和情绪中隐藏的不知所措,在各种琐碎的细节中昭然若揭。
双腿瘫痪的男人偶遇了在门口抽烟的夜班护士;孤独落寞的少年结识了新搬来的过气影星邻居;儿子在服刑,孤独的母亲迎来了从天而降的美国宇航员。这故事中,有写实,有魔幻,那从天而降的宇航员成为了这现实主义编排中的一抹神来之笔,一次调皮的恶趣味,一桩令人感伤的象征主义的强行植入。
从表层去看,这故事就是任何一座都市中随意截取的生活片段,人们游荡、发呆、寒暄,不知所终,但那三次相逢却有着明显又微妙的隐喻,在孤独少年的镜头前,前影星开始试着找回自信,纾解心结;而那位老妪和美国宇航员,犹如临时扮演的母子;残疾男人和孤独的女护士,显然萌发着某种近乎爱情的情愫。
男孩儿象征着鲜活的当下,而女演员却沉浸于自己黑白电影中的过往;老人的儿子被囚禁于监狱,而宇航员来自于象征着最广袤又自由的太空,这设定互相对照又彼此反讽,最终形成了一种代偿机制。瘫痪的男人谎称自己是摄影师,足迹遍布世界,而与他相对的护士,每日出没最远的距离不过就是在医院后院的空地,她只能抽着烟遥望星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互相成为了彼此的延伸,达成了对方心理欲望的慰藉。

当老人和宇航员比比划划地问着太空是什么样子,让他穿上儿子的衣服休息,给他做着家乡的饭菜,那种孤独又有谁能体会?那个困于轮椅的男人,为了维系那段微妙的情感,端着老旧的相机,对着电视中的草原拼命按下快门,在窗口对着天空拍照,谁又能说这不是为了爱情拼尽全力?六个人,都是彼此的闯入者,他们带着戒备、窥探和好奇,像小心翼翼的蜗牛,伸出触角,慢吞吞地试探碰触,努力掩盖欲望。
这故事中最令人心酸的是,没有人曾说过哪怕一句孤独,没有人抱怨现在的生活,他们看起来安之若素,但或许其实早已心如死灰。在他们心中,生活似乎就应该如此,无人诉说,无人倾听,也无需改变。
在电影的开头,有一场小小的投票,这栋楼里的住户在一起商讨要不要修电梯,只有那个住在二楼的男人没有同意,大家一致决定,他以后就不能使用电梯了,但一天之后,他就因病瘫痪,不得不乘坐轮椅,偷偷使用那架狭窄的电梯,但楼里也无人知晓此事。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助呢?

这几个人一直在聊一件事,这栋楼周围有一阵奇怪的声音,不定时地飘过,像有人哭泣,像某种神秘的空谷回响,但没人知道那是什么,那成为了一种幻想,一种漂浮在无聊现实生活之上的某种寄托,是这逼仄生活中唯一有趣的东西。但最终,发现是那个肮脏的垃圾箱的一扇门在风中忽闪,吱哑做响。它如同那栋住宅楼的隐喻,又像个说破谜底,人们顿觉失望的拙劣笑话,它拆穿了人们最后一点点念想。这生活就像宇航员永远也修不好的那个厨房水管,就像那个发出怪声的垃圾箱,人们对一些事充满把握,把一些事当做寄托,但最终发现总是进退失措。
[VIA:豆瓣 frozenmoon 杨时旸]
 RSS
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