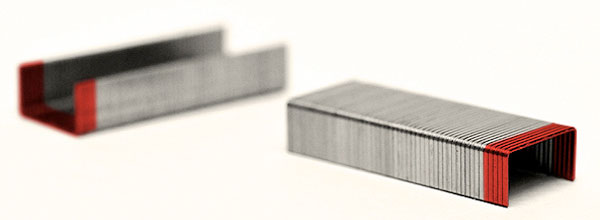逃跑家-乌青
一生中总该会有一次没心没肺的逃跑。

乌青编著的《逃跑家》讲述了:没有计划,没有方向,也没有钱,有 的只是“离开这儿,让一切都见鬼去吧!”的原始冲动,丁西拌、路易、 秋厚布三个年轻人就这样突然背上背包,带上门,开始了一次没心没肺的 逃跑之旅。 整整一年,他们像无头苍蝇似地跑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城市,遇到六 十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发生了很多很多非常多极其多贼多不可思议的故 事。 而他们之间,既逃离着对方,又寻找着对方,其中更是隐藏着一个可 怕的秘密。 他们的故事或许让你震惊,或许让你大笑,又或许让你心碎,甚至暴 跳如雷,但你永远无法忘记。 翻开《逃跑家》,抛弃现实中的条条框框,没心没肺地逃跑吧!
《逃跑家》书摘:
在机场,路易因为摸了一个陌生姑娘的屁股而被机场警察拘留,延误了航班。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甚至没看到那个姑娘长什么样。摸的时候他也没什么欣喜,反而有些茫然和无奈,就好像在地上看到一块钱硬币,觉得应该捡起来。
当时路易坐在登机口附近的椅子上,那个姑娘从旁边走过,拖着一个小行李箱,似乎她突然发现行李箱上的某个拉链没拉好什么的,蹲下来,这时候她的臀沟就露了出来,而路易的目光恰好落在了那片区域。于是他走过去轻轻地摸了一下(其实只是碰了一下)她的屁股,她尖叫起来。
在拘留室,路易麻木地回答了警察的所有问题,他的耳朵里一直幻听出有人砍树的声音,他还想打高尔夫球(他从来没有打过)。
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这么干吗?丁西拌问路易。
我不确定,大概不会吧。我又不是真的想摸她。路易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看到内裤了吗?
当然。
什么颜色的?
粉红色。
会不会因为这个?
我不知道――应该不是吧。
你知道吗?我等了你五个小时啊。丁西拌说。
你当时在干什么呢?路易说。
在肯德基折纸飞机。
麦当劳女服务员的制服要比肯德基的好看。
嗯,粉红色的。
咖啡也好多了。
但如果我在麦当劳折纸飞机它就不押韵了。
你可以在麦当劳慢慢变老。
我当时在那家肯德基做了个统计,那五个小时里,有十二个人来肯德基不是为了吃东西,而仅仅是来嘘嘘。有三个是女的。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你一个人去麦当劳肯德基或者星巴克之类的买了一杯喝的,你想打发时间慢慢喝,过了一会儿你想去洗手间,如果你去了厕所回来八成你的东西已经没了,你又不能一直憋着,怎么办呢?
没办法,我一般憋一会儿然后就去厕所然后就走了,如果两个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可我们通常是一个人。我有一次在星巴克遇到这种情况,我实在合不得那半杯咖啡,就叫邻座的一个陌生女孩帮我看一下别让服务员收走。
我靠,真的?这你都干得出来?
难道这比你在机场里摸陌生女人的屁股更需要勇气吗?
不一样不一样,我这个有点鬼使神差的意思,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你这个是理智的。
我在一本古书上看到,拉屎的时候咬牙对牙齿和肾都很有好处。
啊?你信吗?
当然,我非常信,这是一个经典中医理论,所以我记住了。但遗憾的是每次拉屎的时候我都忘了,而拉完屎就马上想起来了,追悔莫及啊,每每如此。――我的牙不行了。
你还记得周皮球偷麦当劳洗手间里的厕纸吗?
是啊,好大的一卷,放家里可以用半年。
《逃跑家》评论:
没有人能像乌青那样,十几年如一日地过着无聊至极的生活,贫穷,晃荡,想着自杀,搞完女人便寻思逃跑,每天都绝望忧伤,却能在长篇小说的每一页都让人笑。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以不是白痴就是天才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把无聊本身打碎,放大,串联,变成令人惊讶的可笑、诗意和伟大。在城市化生活炮制批量化可复制的都市小说、情感小说与旅行小说的时代,乌青,作为乌有乡长大的逃跑主义青年,始终不肯进入这个世界的轨道中,他在彼此雷同的城市与城市空间中逃窜,为的是不和这世界发生一丁点儿他不想发生的关系。他甚至想从雨点与雨点的间隙中侧身逃离。
长篇处女作《逃跑家》出版前,乌青在微博上略显尴尬地“微火”了一把。有人找出他十几年前写的“口水诗”,大表震惊并嘲讽,优越感落英缤纷。那首曾经著名的毁三观的诗名叫《对白云的赞美》,大意是白云真白,特别白,真他妈的白啊。内容也如此。精确到语句,也大抵如此。万人转发的结果是,乌青,这个刚刚写完一部长篇的“橡皮”头牌诗人、独立影像制作者,我十年前在各大文学杂志上见到的那个年轻人,再次以受争议者的身份,以类似网络炒作的方式,让世人知道了他的名字,而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因此认真阅读他的新小说,除了他的朋友们,没有多少人对这部小说做出公允评判:它究竟是部怎样的小说啊!
《逃跑家》是部乌青式的小说。就像那首饱受争议的诗一样,你可以嘲笑他,但你永远也无法写出那样一首诗。如果说写出那首诗的人不是天才就是白痴,那么,长篇小说这种体裁,给了人们充足的时间对这个在两极间震荡的被评判者做出判断。
其实,如果你知道乌青是在何种心理、生理和自然条件下写出《对白云的赞美》,如果你尝过在火炉城市荒无人烟的大学城饥寒交迫地生活过,不识一人,不名一文,断电断网,如同置身世界尽头的最后一天,如果你此时抬头看天,看到无以名状的白云正以无限而惊人的白冲击着你的语言资料库,你应该可以明白,《对白云的赞美》是一首美妙的诗。它之美妙,在于其不可复制的单纯洁净,仿佛饥寒交迫者空空如也的胃袋,俗丽大都会皮毛之下的彻骨虚无。
就像乌青的诗歌一样,《逃跑家》有着纯净的头脑、结构和修辞。形容词是很难见到的,即使有,也极其质朴。至于情节,就是如乌青的直系师承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般的流浪至死,以及《在路上》那种“自动写作”般的“手机写作”。是的,这部18万字的小说,写作介质是手机,据说写坏了三部触屏手机。相对于凯鲁亚克的打字机,如今作家们的笔记本,手机显然更适合一个逃跑作家,无论厕上车上床上山上,随时可落笔。
《逃跑家》是一个无尽的玩笑,就像生命本身。它的作者太孤独,所以把自己的左手纹到了自己的右手手腕。它的作者太孤独,所以发明了同一主人公的三个分身:丁西拌、路易、秋厚布,他让他们泡妞、赖账、做梦、上路,互相交谈、写信,相爱,怀疑人生。怀疑他们都是可悲的分身,而母体另有其人。
《逃跑家》是乌青一次无计划的逃跑经历的副产品,房子到期了,他带上8000块存款,上路。逃跑历时一年,也正是小说中的叙事时间:从2011年1月1日到11月11日。这两个由诸多孤独的数字组成的时间点之间,有着无数孤独的辰光:孤独的主人公独自上路,不知目的,不问意义,他似乎并不热爱风景,也不享受旅行。
游遍整个中国,却毫无常识中的旅行乐趣,人物所到之处,必然做的无非四件事:去星巴克喝咖啡,去快餐店吃快餐,去青旅住店,各种无厘头泡妞。除此之外,就是饭饱神虚后逛超市,感叹超市商品和无印良品的纸张的贵。日常生活场景冗长无趣,彼此复制,无休无止。
这就是乌青对现代生活和现代城市的理解:城市变成快餐店般的复制空间,一种无限复制的抽象化存在。在《逃跑家》中,他不厌其烦地以专名记录咖啡的品种,快餐的名字和内容,青旅中的陈设。他有种清单迷恋,与格里耶不同,他对物并不膜拜,只是展示精神世界的无聊,和物的世界的繁盛——星巴克的咖啡品种层出不穷,快餐店的营养套餐时时更新,人物的生命和精气神儿却越来越机械化,被抽干抽空,无意义、无情节,无聊无趣,直到剩下被剥离到只剩时间节点的人生本身。在这部虚无、孤独和忧伤到不可救药的小说中,最让人忧伤的是,它竟然笑点儿密布,几乎每页都能让你大笑出声(如:“此刻上面坐着一堆中年男女,男人的神情犹如世界主宰者,女人的神情犹如世界主宰者的主宰者——他们差不多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安排了这世界最后的命运,而后欣然离去,陈本柴闪电般占领了其中一个沙发,然后他很烦——他发现这世界的主宰者似乎有狐臭。”
),而在最后,作者放弃了他伟大的幽默感,在杀死了他对影成三人的三个主人公分身中的两位后,乌青让丁西拌带着他奇怪的明显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名字,再次默默上路。
拯救无聊致死的情节的,是来自乌有乡的梦幻。梦幻场景总能在读者被虐得五迷三道之际像乱码般跳出复制界,带你瞬间浮上迷魂界逍遥一回。失败的兰杀手是第一个bug信号,而后是落魄宅男作家蒲松龄,人物自杀后的世界:没有火来点烟。因为生者无法把火烧给死者,因此人物只能在无法吸烟的地狱中焦躁地弹来跳去。
这种孩童式奇想,烙着乌青的印章。它来自于电影化的视觉思维与想象力,也来自于一双孩童的眼睛。乌青的文字是纯净的,这源自他纯净的生活方式:不工作,没钱,无固定住所,无固定女友。他可以随时抛下行李家当出走,他不想为自己找任何麻烦。尽量不踏入约定俗成的社会轨道半步。你可以说他胆小如鼠,也可以说他无比勇敢。除此,他还拥有令人嫉妒的纯净视觉和由此派生的纯净语言,以及词语与词语的让人惊讶的排列。他仿佛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不在任何一条轴线,不在任何一个台阶,不踏入任何一道门槛,仿佛直接遁入空门,那些神颠颠的对话似乎不出自人间,而个个都是禅宗段子。
虚耗时间的无聊感,来自对时间的错觉。人类作为一种有终结的生物性存在,建构了时间。《逃跑家》警觉于时间,被时间折磨。小说前100节,结绳记事般按天记录。101节,主人公决定“忘掉时间”。然后时间轴继续向前,却在途中出现了混乱。小说的时间变得像猫咪玩过的线团。在错乱的时间线团中,主人公的两个分身相继死去,一些迷雾次第升起,遮住了叙事的天空。直到小说行将结束,人物像重获记忆般记起了时间,他回顾童年,想起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十五年:
“十五年了,也许是时候改变人生了,也许应该像老黄牛那样生活,而不是像一只麻雀。”《逃跑家》的结尾,主人公唯一幸存的分身这样想。他也许会去找一份工作,也许会去死。谁知道呢?也许在乌青看来,找一份工作和去死并没有区别。
作为成名于网络的作家,乌青也质疑了网络化生存的可怕后果。在面对人人对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与笔记本等网络终端的公共空间时,主人公突然获得上帝之眼般地发问道:“这些是人吗?什么又是人呢?网络是人类的工具还是反过来,人类是网络的工具?照这种发展最终人将变成一个个网络终端,人活着只是为网络提供数据。而丁西拌觉得这些数据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想这些让他头疼,最好的办法是去找点事儿做,“事儿连着事儿,就像网络链接,只要你找到一点事儿做就发现有无止境的事儿可以做,如同你点开网上的任意一个链接就可以点一辈子,刷微博或社交网站可以刷一辈子。”
可是在小说中,乌青并没有给出一个让人愉快的答案。他让人物在思考到头疼后转而走出星巴克,去觅食,回旅店,再次邂逅了一个姑娘。
如果你试图在乌青的小说中寻找意义,那将是徒劳。它和这个小说的人物与作者一道,带着时间,逃跑了。逃到哪里去?也许是禅宗公案般的语言中,也许是梦乡虚境中,也许是柳泉居士的奇想聊斋世界中,反正只要离开此地就行。
卡夫卡写过:如果我在旅途中不得到什么,我一定会死去。还好旅程似乎没有尽头,因此你不知道是否接下来就会得到些什么。作为一个总是无法摆脱自杀念头的逃跑主义青年,乌青就像他钟爱的电影《死神通告》中的主人公,手里握着一块免死牌小石头,一路狂奔,直到想死而不得,直到死神允诺了对他的诅咒。与《逃跑家》的人物不同,它的作者得到了语言,得到了作品。也许这是抵制被生命消耗殆尽并生存下去的唯一理由。
访谈:《城市画报》VS乌青
1,《逃跑家》中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密布到让人迷惑,且并不讨论哲学。这是聪明的做法,也是你多年来坚持的做法。这除了与你的日常生活状态相关外,还有什么刻意为之的理念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吗?
我觉得日常生活的细节可能是现实和小说之间最亲密的元素,故事可以虚构,情节可以虚构,而细节不存在虚构,因为这一切都是由细节构成的——无论是现实的世界还是小说的世界。
而语言就像“上帝粒子”。
2,《万有坏力》这个名字受《万有引力之虹》的启发?后者中,万有引力是一种无所不在的与宇宙同存亡的控制力,该小说作者也用他的主人公提供了一种反作用力,最终反作用力结盟,虽然前景不容乐观,但这也是上帝这个编程佬的程序设计的一部分,是为终极阴谋论。你的万有坏力的“坏”意味着什么?似乎是一种极为消极的抵抗,比麦田守望者更为绝望的守望。
与其说“万有坏力”的证明来自《万有引力之虹》还比如说它来自于中国足球——中国足球花了这么多人力财力经过这么多年努力想尽一切方法结果糟糕透顶,所有人都对它失去了信心。我觉得它就应该这样——消灭所有的希望。它是存在的,你不能因为中国足球太烂就说中国没有足球(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
3,你的人生就是一场逃跑,真的可以不问意义?在痛苦与虚无中你选择什么?你的下一步逃跑计划?
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了那就不是逃跑了,意义无处不在,唯有“不知道”是没有意义的(前提是不去考虑该说法的严谨性)。
4,你每一次写作都尝试突破,为什么这么多年才写了一部长篇?《逃跑家》相对于你的阅读背景,传承于哪里,突破在哪里?在汉语写作背景下,你的突破又在哪里?
我觉得当代汉语写作太缺乏突破了,一些所谓的先锋写作往往为了突破而突破,
这种目的性使得突破背离了文学。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忘掉写作的目的和之前构建的写作体系,在“不知道”和“模糊”的状态下写作,我认为这种“不知道”和“模糊”应该可以作为是当代小说的的一种写作方向和审美体验。
5,和“在路上”的垮掉一代相比,你的逃跑家更具个人性,尤其在当下这个宅男宅女和间隔年者背包客现象同时并存不分伯仲的时代。逃跑家的孤独和忧伤简直催人泪下,这个人物(复数)与你本人的重合度有多大?这样的人物与作家重合度较大的写作的弊端或曰副作用,通常是一段时间的枯竭。除非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写作面临这样的瓶颈或困境吗?
事实上,我本人要比小说里的人物更为困惑和痛苦,我要面临小说和现实两个世界(或两者混合的世界)的折磨,我一直在“灾难”中写作,而且这不会停止——除非我停止写作——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多年还不停止写作。我想,这就是“万有坏力”的作用。
6,你有没有想过工作,结婚这种社会与习俗要求的规范化轨道上的生活的可能性?我是说,既然丁西拌可以在星巴克遇见宇宙主宰者和宇宙主宰者的主宰者,你也可以在工作时遇到蒲松龄。
想过啊,但我觉得这太复杂了——比起自杀。
7,除了成为《逃跑家》的作者,究竟为什么要不停地走?你看上去既不热爱风景,也不享受旅行,对人也不甚感兴趣。如果说你要说自己是个彻底虚无的与死神赛跑的人,我将不太理解你伟大的幽默感所从何来。
关于我的情况我不知道。关于幽默感,我发誓这不是来自我,而是阅读者(只有极少数的阅读者会感受到你所说的“伟大的幽默感”,这部分阅读者比如你,是伟大的你们改变和创造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我估摸这是你们的天赋)。
 RSS
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