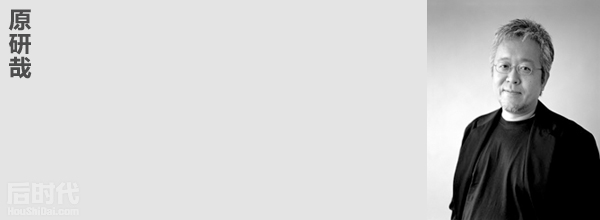《最后一班地铁》特吕弗的转折
艺术只是生活的麻醉剂,而生活仍在痛苦中继续。

《最后一班地铁》(The Last Metro)是舞台版的《日以继夜》,以戏中戏的方式描写战争、人性、爱情,戏剧性丰富,演员的表现也有吸引力。虽然不是导演的最佳作品,但仍具有相当高的水准,获十项法国凯撒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最后一班地铁》是由弗朗索瓦·特吕弗执导,凯瑟琳·德纳芙,杰拉尔·德帕迪约,保利特,达波斯特等联袂主演的一部爱情片。本片描述二战期间,在德军占领下的巴黎,戏剧照常上演,犹太籍的剧场主人兼编剧吕卡斯为了躲避纳粹的种族迫害,一直住在剧院的地下室,继续领导和排练他所编的剧目。这一切全都是通过他的妻子、著名女演员玛丽翁来完成。每次他靠地下室内的伪装通风系统来倾听舞台上的排练,同时也感觉到了玛丽翁和男主角的扮演者格朗惹之间产生了微妙的爱情。考虑到自己的处境,他决定成全了他们。但格朗惹见到吕卡斯之后,决定到抵抗运动中去。巴黎解放了,玛丽翁站在舞台上,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拉着情人,向观众频频谢幕。影片于1980年9月17日上映。
1980年,曾经是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旗手的特吕弗拍出了自己在本土票房最成功的一部电影——《最后一班地铁》。因其在电影语汇上的完美展示,和演员无懈可击的表演,而一举夺得了当年法国电影恺撒奖的11项大奖。其中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重要奖项。这是特吕弗的倒数第二部电影,真可谓是大师的一次完美的谢幕。
特吕弗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了沦陷的法国,在一个危机重重的剧院里展开。剧院的经理吕卡斯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藏在剧院的地窖,等待时机成熟时逃往国外,然后在那里重新开始自己的艺术事业。可是德军占领了北部自由区的消息使他的计划变成了泡影。他的妻子玛丽恩掌管着剧院,在各色人等——丈夫、情人、投靠纳粹者和德国人之间周旋。抵抗组织成员贝尔纳通过应聘成为话剧《失踪》一剧的男主角。在和合作演戏的过程中他爱上了玛丽恩。在地下百无聊赖的吕卡斯敲开了暖气管道,听着舞台上的动静指挥着戏剧的排练。剧场始终不能保持宁静,种种社会上的矛盾开始牵扯到剧院里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创作。在贝尔纳的帮助下吕卡斯逃过了纳粹的搜查。在重重的阻挠下,《失踪》终于演出了,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几年过去了,巴黎光复。吕卡斯重新回到了地上,继续指导话剧。玛丽恩也在吕卡斯和贝尔纳之间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在影片的结尾,蒙玛特剧院上继续上演着叫好的话剧。台上,玛丽恩一手拉着自己的丈夫,一手拉着自己的合作者——情人,将这两个极具象征性的符号高高举起。
这部电影已经看不到特吕弗当年的风格了,大部分镜头全在摄影棚内完成,狭窄的空间,中近景的推拉,明亮的布光。影片就像一部室内剧。没有了早年《400下》的自由和灵性,但却多了几分老练和完整,有一种信手拈来的感觉。特吕弗用这部电影告诉世界,他不仅可以拍出飘逸的《400下》,也可以有《最后一班地铁》的经典叙事。
特吕弗在这部电影里对政治的态度相当模糊,他没有将什么反犹主义、地下军等政治意象拿来逐一点评。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这部电影里的巴黎是“是个小孩子眼睛中的巴黎”。但是电影里却有处处体现出了政治——这里的政治指的是政治对电影中的人物的生活的影响,而不是具体的意识形态。特吕弗同时又在这部电影中设问和思考——艺术是不是逃避现实的理由?艺术家是否该面对世俗的纷争?像最后一班地铁,那是从沦陷区到自由区的唯一出路。所有的剧场工作人员都要乘坐着最后的一班地铁才能回家。而艺术,是不是情感的最后一班地铁呢?是不是情感的唯一的释放点呢?吕卡斯是一个很纯粹的艺术家,他对纳粹的仇恨仅仅是因为战争使他暂时无法从事艺术工作,而对纳粹的反犹主义却丝毫没有兴趣。他蜷缩于地下,于是艺术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但是他不知道没有现实意义的艺术、不反映饥饿、死亡、痛苦的艺术不会成为灵魂的净化剂,他只是个悲伤哀怨的个体旁观者。玛丽恩比她的丈夫要更为现实,她为了活下去,只好将自己的感情倾注于舞台,在那里她又一次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和最后的归宿。贝尔纳则是现实(政治)和艺术的综合体,一方面他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演技高超的话剧演员。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他选择了现实,用我们的话来讲这叫“以积极的态度入世”。玛丽恩在这种冲突下选择了走在老路上,以不变应万变。其实电影中的所有人都在找自己的出路,包括那个做戏服的犹太小女孩也是这样。艺术只是生活的麻醉剂,而生活仍在痛苦中继续。最后玛丽恩同时举起了丈夫——艺术和情人——现实的手,表现了特吕弗崇高的艺术理念和人文思想。
戏剧仍在上演,但是电影却拉下了帷幕。特吕弗这部晚年的代表作,用最辉煌的手势对戈达尔对他不讲政治的指责做出了强势的回答。这辉煌的答辩无愧于大师晚年最完美的一次谢幕。

最后一班地铁 Le dernier métro (1980) 影评:
当你的国家被敌人占领时,你将怎样?奋勇的反抗?顽强的生活?继续事业?在爱情中苦恼与快乐?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就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区内的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看完电影,我才明白了在那段时期的日常生活一样是复杂和多样的,你无法用一个“屈辱”来概括,因为其中也有抗争,有欢笑,有幸福,有趣味,在敌占区的生活没有改变生活本身的多样与复杂,但是,敌占区的背景又为它抹上了一丝平常不见的顽强与坚韧。
影片并没有太跌宕起伏的情节,故事线索很简单,吕卡斯和他的妻子本来经营着一座还算不错的剧院,但是他的犹太人身份使他不得不藏身于剧院的地窖之下指导演出,而他美丽的妻子玛丽翁则走向前台,维持着剧院的运营。在排练一出新的话剧时,具有反抗精神的演员贝尔纳走入其中。一方面玛丽翁要掩护他的丈夫,另一方面她又要牵扯于与贝尔纳的爱中,直到战争结束前夕,她紧握两个男人的手,完美谢幕。尽管有犹太人深藏地窖,躲避纳粹的情节,但是影片中处理的没有想象中那么惊心动魄,特吕弗更多的还是为我们展示了被德占领下法国的人情百态。
我们习惯于歌颂在外敌入侵时,挺身而出,以生命捍卫民族的英雄,对于默默生活的人们往往有些不以为然。那些挺身而出的英雄们当然值得赞颂,但是那些顽强生活的人同样有他们值得尊重的一面。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普通法国人的生活,他们或许没有直接的向敌人发抗,但是他们以一种继续生活的态度进行着默默的反抗,影片中随处可见这种无声的反抗。比如一个德国兵摸了孩子的头,孩子的母亲说“我们现在快点回家洗头”;比如贝尔纳在夜总会正要将衣帽托放在前台,却发现那里许多德国军帽时,马上收回了衣帽。更多的体现还是剧院在巨大的压力下顽强的坚持他们的事业的故事上,在吕卡斯在地窖中藏身八百余天继续他的戏剧事业的坚持中。吕卡斯在地下世界通过一个通道倾听着地上世界的演出,他也有焦躁与不安,有沮丧和失落,但是,我相信他更有对事业的爱和希望,否则他无法在地窖里倔强的生活两年多的时间。当然,还有他妻子玛丽翁的支持,玛丽翁是片中真正的主人公,一个令人可敬的女主人,她希望平安的生活,希望可以继续上演她和丈夫的话剧,为此,她在地下与地上的世界里穿梭忙碌,要与当局的审查周旋,更要为生活操劳,更令她疲惫的是,她要在丈夫和贝尔纳之间陷入感情的纠缠。而贝尔纳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有些像个玩世不恭的花男人,但是他却又支持着同伴的抵抗事业。在他和玛丽翁的关系上,导演处理的颇具悬念,一直到最后才揭示了他和女主角那深藏的爱情。在这部片子中,三个主要演员的演技都非常出色,使这部描述相对平淡生活的影片又很亮色。
虽然有对占领者的抵抗,但是我看到的还是法国普通人的生活景象,片中法国人并不是想象的苦大仇深,双眉深锁的样子,他们一样在生活,在娱乐,一样赶在最后一班地铁前在剧院里享受艺术,纵情鼓掌。我曾听说过在大萧条时期,美国人醉心于电影世界带给他们的片刻欢乐中,而好莱坞也是在人们寻求痛苦中的欢乐期待中兴起。那么,作为国土被占的法国人,他们更企盼着那怕片刻的安宁,面对侵略者,大部分人充满了鄙夷与愤怒,但是能直接起来不顾性命反抗的只是部分。那么剩下来的不愿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的人们,只能选择好好生活,因为只有顽强的生活才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就像吕卡斯那样,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像在剧院的人都是平凡的,他们很多人即使在战争中也充满了平凡的愿望,寻找亲人的老太太,渴望飞黄腾达的学生,埋身与琐碎生活的剧务,周旋于社交界的剧院经理,种植烟草玩耍的孩子,这些普通人与抵抗者,同流合污者加上占领者才构成了一幅真实的占领区生活,而对这些普通人,我们过去总是关注的太少,所以我要说,特吕弗令人尊敬。
《最后一班地铁》上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认为它是一部视听艺术的经典之作,不管这样的评价是否过誉,不过我承认,在视觉上这部影片确实很有特色,红色是一个片中的主色调,不过不是张艺谋爱摆弄的那种大红。整部影片始终笼罩在一种淡淡的深红色彩中,这样既给观众以美感,同时有增添了一丝历史感。该片作为反映战时平凡人的影片,没有战场的硝烟与声浪,没有生离死别的紧张与沉重,最终,平凡生活的人们等到了胜利,他们终于可以尽情的在剧场获得快乐,而影片也没将女主角置于在两个男人间选择的尴尬,在一次谢幕时,玛丽翁一手牵着战时与他在地下相伴的吕卡斯,一手牵着战时与他在地上相伴的贝尔纳,发出会心的微笑,而影片也就此结束,给我们留下一个同样悠长完美的谢幕。
 RSS
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