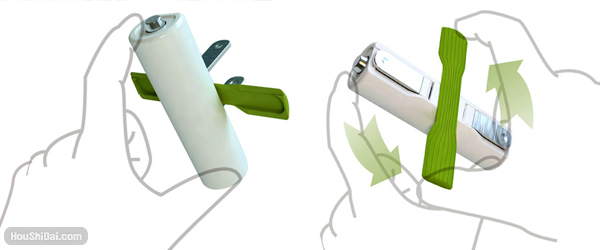гҖҠжҪңж°ҙй’ҹдёҺиқҙиқ¶гҖӢз»ҷдҪ дёҖж¬Ўжҝ’з”ҹзҡ„дҪ“йӘҢ

“йҷӨдәҶжҲ‘зҡ„зңјзқӣеӨ–пјҢиҝҳжңүдёӨж ·дёңиҘҝжІЎжңүзҳ«з—ӘпјҡжҲ‘зҡ„жғіиұЎпјҢд»ҘеҸҠжҲ‘зҡ„и®°еҝҶгҖӮеҸӘжңүжғіиұЎе’Ңи®°еҝҶпјҢжүҚиғҪд»ӨжҲ‘ж‘Ҷи„ұжҪңж°ҙй’ҹзҡ„жқҹзјҡгҖӮ”
科еӯҰз ”з©¶пјҢдёҖдёӘдәәеңЁж„ҸиҜҶеҲ°жӯ»дәЎеҚіе°ҶжқҘдёҙзҡ„йӮЈдёҖз§’й’ҹзҡ„ж—¶й—ҙйҮҢиғҪеӨҹеӣһеҝҶиө·ж•ҙдёӘдёҖз”ҹдёӯеҸ‘з”ҹзҡ„жүҖжңүдәӢжғ…гҖӮиҝҷе°ұжҳҜжҲ‘们йҖҡеёёжүҖиҜҙзҡ„”жҝ’жӯ»дҪ“йӘҢ”гҖӮ
гҖҠжҪңж°ҙй’ҹдёҺиқҙиқ¶гҖӢйҮҢзҡ„з®ҖеӨҡпјҢз»ҸеҺҶзҡ„дёҚжҳҜжҝ’жӯ»дҪ“йӘҢпјҢиҖҢжҳҜ”жҝ’з”ҹ”дҪ“йӘҢгҖӮ
е…Ёиә«йҷӨдәҶе·Ұзңјзҡ®д№ӢеӨ–дёҚиғҪеҠЁеј№пјҢдёҚиғҪиҜҙиҜқиҝӣйЈҹпјҢдёҚиғҪеғҸзҲёзҲёдёҖж ·жҠҡж‘ёеӯ©еӯҗзҡ„еӨҙпјҢдёҚиғҪеңЁжғізңӢдёҖеңәжңҹеҫ…е·Ід№…зҡ„жҜ”иөӣеҚҙиў«еҢ»з”ҹе…іжҺүз”өи§Ҷж—¶еҸҚжҠ—гҖӮд»–иғҪзҡ„пјҢеҸӘжҳҜеңЁеәҠдёҠпјҢиҪ®жӨ…дёҠжғіиұЎпјҢеӣһеҝҶгҖӮиҝҷи¶іеӨҹдәҶд№Ҳпјҹиҝҷи¶іеӨҹдәҶгҖӮ

жҳҜдёҚжҳҜеҸӘжңүеҲ°дәҶеҚіе°Ҷжӯ»дәЎзҡ„йӮЈдёҖеҲ»пјҢжҲ‘们жүҚдјҡејҖе§Ӣйқҷйқҷең°жҖқиҖғдёҖдәӣдәӢжғ…пјҢдёҖдәӣжҲ‘们жӣҫз»Ҹд»ҺжқҘйғҪдёҚеҺ»жғіпјҢдёҚж•ўжғізҡ„дәӢжғ…пјҹеёҢжңӣиҝҷдёӘиҜҚпјҢеңЁд»Җд№Ҳж—¶еҖҷжңҖжңүеҠӣйҮҸпјҢжҲ‘们жғіиҝҮд№ҲпјҹжҲ‘们зҡ„з”ҹжҙ»е……е®һд№ҲпјҹжҲ‘们зҡ„зІҫзҘһдё–з•Ңе……е®һд№ҲпјҹжҲ‘们з»ҸеёёиҙЈй—®иҮӘе·ұпјҢеҸҚзңҒиҮӘе·ұд№ҲпјҹеңЁзү©иҙЁз”ҹжҙ»д№ӢдёӢзҡ„жҲ‘们пјҢд»Җд№Ҳж—¶еҖҷиғҪеӨҹйқҷйқҷең°жҖқиҖғиҝҷдәӣй—®йўҳпјҹдёҖйғЁз”өеҪұпјҢд№ҹеҸӘиғҪжҳҜдёҖйғЁз”өеҪұиҖҢе·ІпјҢдҪ еҫ—зңҹзҡ„жҳҺзҷҪйӮЈдәӣйҒ“зҗҶпјҢжүҚдјҡзңҹжӯЈзҗҶи§ЈдёҖйғЁз”өеҪұе•ҠпјҢдёҚжҳҜиҜҙдёҖйғЁжІЎжңүзңӢжҮӮзҡ„зүҮеӯҗе®ғе°ұжҳҜй—·зүҮпјҢдёәд»Җд№ҲзҺ°еңЁзҡ„дәәдёҚж„ҝж„ҸзңӢиҝҷж ·зҡ„зүҮеӯҗпјҢжҳҜе®ғеӨӘжІүйҮҚд»ҘиҮідәҺдәә们йғҪдёҚж•ўжҺҘеҸ—дәҶд№ҲпјҹиҝҳжҳҜиҜҙдәә们еңЁзү©иҙЁз”ҹжҙ»д№ӢдёӢпјҢе·Із»Ҹе°ҶзІҫзҘһдё–з•ҢжҠӣеҫ—дёҖе№ІдәҢеҮҖдәҶпјҹеҸҜеә”иҜҘжҳҺзҷҪзҡ„жҳҜпјҢиҝҷе°ұжҳҜзҺ°е®һпјҢдәәзұ»зӣ®еүҚжүҖйқўдёҙзҡ„пјҢд№ҹи®ёжңӘжқҘпјҢиҝҷдёӘй—®йўҳе°ҶдјҡжӣҙдёҘйҮҚгҖӮдёҚиҝҮжҲ‘дёҖзӣҙзӣёдҝЎзҡ„жҳҜпјҢеҸӘиҰҒиҝҷж ·зҡ„з”өеҪұдёҖзӣҙеӯҳеңЁпјҢжҖ»жңүйӮЈд№ҲдёҖдәӣдәәжҳҜдёҚдјҡеҝҳи®°пјҢдёҚдјҡеҝҪи§Ҷзҡ„гҖӮжүҖд»ҘпјҢжҖ»жҳҜйңҖиҰҒдёҖдәӣеёҢжңӣзҡ„гҖӮ
е°ұеғҸеҪұзүҮжңҖеҗҺпјҢеҖ’еЎҢзҡ„еҶ°еұұеҸҲд»Ҙеӣһж”ҫзҡ„еҪўејҸжҒўеӨҚж—¶пјҢеҘҪеғҸз®ҖеӨҡеңЁе‘ҠиҜүжҲ‘们пјҡжҠҠжҸЎдҪҸз”ҹжҙ»пјҢжҠҠжҸЎдҪҸиә«иҫ№жүҖжңүзҲұдҪ зҡ„дәәгҖӮеҪ“иҝҷдёҖеӨ©зңҹжӯЈжқҘдёҙж—¶пјҢдҪ иҝҳиғҪе‘ҠиҜүиҮӘе·ұпјҢдҪ еҺҹжқҘиҝҷд№Ҳе№ёзҰҸпјҢз”ҹжҙ»еҺҹжқҘиҝҷд№Ҳе№ёзҰҸгҖӮ

гҖҠжҪңж°ҙй’ҹдёҺиқҙиқ¶гҖӢз”өеҪұдёҺеҺҹи‘—еҢәеҲ«
гҖҠжҪңж°ҙй’ҹдёҺиқҙиқ¶гҖӢеҺҹи‘—дҪңиҖ…Jean Dominique Bauby(1952вҖ”1997)жң¬дёәжі•еӣҪж—¶е°ҡжқӮеҝ—ELLEжҖ»зј–иҫ‘пјҢеҗҺжқҘеҸ‘з”ҹж„ҸеӨ–пјҢе…Ёиә«зҳ«з—ӘпјҢе”Ҝжңүе·Ұзңјзҡ®иғҪеӨҹжҙ»еҠЁгҖӮе”ҜдёҖзҡ„жІҹйҖҡж–№жі•жҳҜпјҢдәә们иҜ»еҮәеӯ—жҜҚпјҢдёҖзӣҙеҲ°BaubyзңЁзңјзӨәж„ҸпјҢдёҖеӯ—дёҖеӯ—пјҢдёҖиҜҚдёҖиҜҚпјҢз»„еҗҲжҲҗдёҖеҸҘпјҢеҸҘеӯҗеҶҚз»„еҗҲжҲҗж®өиҗҪпјҢ然еҗҺжҳҜдёҖзҜҮж–Үз« пјҢжңҖз»ҲжҲҗд№ҰвҖ”вҖ”гҖҠжҪңж°ҙй’ҹдёҺиқҙиқ¶гҖӢгҖӮз”өеҪұеҜјжј”Julian SchnabelиҠұдәҶеӨ§жҰӮеӣӣеҚҒдә”еҲҶй’ҹпјҢз”ЁPOVзҡ„дё»и§Ӯи§’еәҰпјҢи®©и§Ӯдј—иҝӣе…ҘBaubyзҡ„и§Ҷи§’пјҢд№ӢеҗҺжүҚд»Ҙиқҙиқ¶иҝҷдёӘйӣҶи®°еҝҶеҠӣдёҺжғіиұЎеҠӣдәҺдёҖиә«зҡ„иұЎеҫҒејҖеұ•жғ…иҠӮгҖӮеңЁж—¶й—ҙиҝҗз”ЁдёҠпјҢеҜјжј”жңӘе…ҚиҝҮдәҺеҘўдҫҲдәҶеҗ§гҖӮ
еҺҹи‘—гҖҠжҪңж°ҙй’ҹдёҺиқҙиқ¶гҖӢејҖеұ•дәҶи®°еҝҶе’ҢжғіиұЎзҡ„еӨ©ең°пјҢжҲ‘жңҖе–ңж¬ўгҖҲзҡҮеҗҺгҖүзҡ„жңҖеҗҺдёҖж®өпјҢж–Үдёӯзҡ„иүҫзҸҚеҰ®зҡҮеҗҺжҳҜжӢҝз ҙд»‘дёүдё–зҡ„еҰ»еӯҗпјҢд№ҹжҳҜеҢ»йҷўзҡ„иөһеҠ©дәәгҖӮBaubyжҒ¬йҖӮжғ¬ж„Ҹзҡ„иғҢеҗҺжҳҜе‘Ҫиҝҗж’ӯеј„зҡ„жӮІеҮүпјҢдёӨз§ҚжһҒз«Ҝзҡ„ж„ҹеҸ—еңЁе№Ҫй»ҳзҡ„иҮӘеҳІе’ҢжғіиұЎд№Ӣдёӯжө‘然жҲҗдёәеҠЁдәәзҡ„еҸҷиҝ°пјҢиҝҷдёҖз§ҚжӮІе–ңдәӨжқӮзҡ„жғ…з»ӘеёҰеҠЁзқҖиҮӘдј зҡ„д№ҰеҶҷпјҡ
гҖҢиҝҷж—¶еҖҷпјҢдёҖиӮЎж— д»ҘеҗҚд№Ӣзҡ„жҒ¬йҖӮж„ҹж¶ҢдёҠеҝғеӨҙгҖӮжҲ‘дёҚдҪҶжҳҜйҒӯеҸ—жөҒж”ҫгҖҒдёҚдҪҶжҳҜзҳ«з—ӘдәҶгҖҒе“‘е·ҙдәҶгҖҒжҲҗдәҶеҚҠдёӘиҒӢеӯҗпјҢдёҚдҪҶжҳҜжүҖжңүзҡ„ж¬ўд№җйғҪиў«еүҘеӨәдәҶпјҢдёҖеҲҮзҡ„еӯҳеңЁйғҪиў«еҮҸзј©дәҶпјҢжүҖеү©дёӢзҡ„д»…д»…жҳҜиӣҮеҸ‘йӯ”еҘізҫҺжқңиҺҺиҲ¬зҡ„жғҠжӮҡйӘҮдәәпјҢз”ҡиҮіпјҢе…үзңӢжҲ‘зҡ„еӨ–иЎЁе°ұеӨҹжҒҗжҖ–зҡ„дәҶгҖӮиҝҷдёҖиҝһдёІжҺҘиёөиҖҢиҮізҡ„зҒҫйҡҫпјҢдҪҝжҲ‘дёҚеҸҜйҒҸжҠ‘ең°з¬‘дәҶиө·жқҘпјҢеҫҲзҘһз»ҸиҙЁең°з¬‘дәҶиө·жқҘпјӣиў«е‘Ҫиҝҗд№Ӣй”ӨйҮҚйҮҚеҮ»жү“д№ӢеҗҺпјҢжҲ‘еҶіе®ҡжҠҠжҲ‘зҡ„йҒӯйҒҮеҪ“жҲҗдёҖдёӘ笑иҜқгҖӮжҲ‘е‘је‘је–ҳзқҖж°”зҡ„ејҖжҖҖ笑声пјҢеҲҡејҖе§Ӣж—¶и®©иүҫзҸҚеҰ®зҡҮеҗҺжҖ”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дҪҶжҳҜеҗҺжқҘеҘ№д№ҹж„ҹжҹ“еҲ°дәҶжҲ‘зҡ„еҘҪжғ…з»ӘгҖӮжҲ‘们笑еҫ—зңјжіӘйғҪжөҒеҮәжқҘгҖӮиҝҷж—¶еҖҷпјҢеёӮж”ҝеҺ…жүҖеұһзҡ„й“ңз®ЎеҶӣд№җйҳҹејҖе§Ӣжј”еҘҸеҚҺе°”е…№гҖӮеҰӮжһңиҝҷдёҚдјҡеҶ’зҠҜиүҫзҸҚеҰ®зҡҮеҗҺпјҢжҲ‘е®һеңЁеҫҲд№җдәҺз«ҷиө·жқҘйӮҖиҜ·еҘ№и·іиҲһгҖӮжҲ‘们иҰҒеңЁз»ө延数公йҮҢзҡ„ж–№з –ең°жқҝдёҠиҲһеҠЁгҖҒйЈһж—ӢгҖӮд»ҺиҝҷдёҖж¬Ўд»ҘеҗҺпјҢжҲ‘жҜҸеҲ°еӨ§еҺ…е»ҠпјҢдёҖзңӢеҲ°зҡҮеҗҺзҡ„и„ёпјҢе°ұеҜ№еҘ№йӮЈдјјжңүиӢҘж— зҡ„еҫ®з¬‘дәҶ然дәҺеҝғгҖӮгҖҚ(йӮұз‘һйҠ®иҜ‘пјҢеӨ§еқ—пјҢ1997пјҢйЎө25)
з”өеҪұгҖҠжҪңж°ҙй’ҹдёҺиқҙиқ¶гҖӢжІЎжңүзқҖеҠӣеӨ„зҗҶд»ҘдёҠе№»жғіеҢ–зҡ„ж®өиҗҪпјҢеҜјжј”зҡ„ејәйЎ№дјјд№ҺжҳҜеҲ»еҲ’дәәйҷ…ж„ҹжғ…гҖӮз”өеҪұзҡ„дә®зӮ№жҳҜзҲ¶еӯҗжҲҸпјҢз”ұеҪ“е№ҙиӢұзҺӣиӨ’жӣј(Ingmar Bergman)гҖҠ第дёғе°ҒеҚ°гҖӢ(The Seventh SealпјҢ1957)дёӯдёҺжӯ»зҘһеҜ№еҘ•зҡ„йӘ‘еЈ«Max von SydowйҘ°жј”иҖҒзҲ¶пјҢеҪ“然жҳҜз»қдҪійҖүжӢ©пјҢдёҖеңәеүғйЎ»пјҢеҸҰдёҖеңәйҖҡз”өиҜқпјҢе·Іи¶ід»ҘеҸ«дәәеҠЁе®№гҖӮ
еҸҜжғңзҡ„жҳҜпјҢз”өеҪұж—¶жңүдҪіеҸҘпјҢж•ҙдҪ“иҖҢиЁҖеҚҙз•ҘдёәжӢ–жІ“пјҢд№ҹдёҚеӨҹиұӘж”ҫиҮӘеҰӮпјҢжҖ»дҪ“жқҘиҜҙ并дёҚеӨӘеңҶж»ЎгҖӮеҸҰдёҖдёӘдҪіеҸҘе·ІжҳҜе°ҫж®өпјҢжқңйІҒзҰҸ(Francois Truffaut)гҖҠеӣӣзҷҫеҮ»гҖӢ(The 400 BlowsпјҢ1959)зҡ„йҹід№җе“Қиө·пјҢBaubyй©ҫиҪҰз©ҝи¶Ҡе·ҙй»Һзҡ„еҹҺеёӮе’Ңд№ЎйғҠпјҢжҺҘе„ҝеӯҗеҺ»еҗғз”ҹиҡқпјҢеҸҜжғңдәӢдёҺж„ҝиҝқгҖӮиҮіжӯӨпјҢе…ідәҺз”өеҪұпјҢе·ІдёҚеҝ…еӨҡиҜҙдәҶпјҢе–ңж¬ўзҡ„дәәдёҖе®ҡдјҡзҝ»йҳ…еҺҹи‘—иЎҘе……з”өеҪұзҡ„дёҚи¶ігҖӮдјјд№ҺпјҢж–Үеӯ—зҡ„жғіиұЎз©әй—ҙжҜ”з”өеҪұиҝҳиҰҒеӨ§пјҢиҖҢдё”иҜ»иҖ…жңүжӣҙеӨ§зҡ„иҮӘз”ұгҖӮиҝҳжңүдёҖзӮ№жҳҜз”өеҪұдёҚеҸҠеҺҹи‘—зҡ„пјҢдҪҶиҝҷдёҚиғҪиҙЈжҖӘJulian SchnabelпјҢиҖҢжҳҜBaubyзҡ„ж„ҹеҸ—еӨӘж·ұеҲ»дәҶгҖӮдҪ зңӢзңӢпјҢд№Ұзҡ„з»“е°ҫжҳҜиҝҷж ·зҡ„пјҡгҖҢеңЁе®Үе®ҷдёӯпјҢжҳҜеҗҰжңүдёҖжҠҠй’ҘеҢҷеҸҜд»Ҙи§ЈејҖжҲ‘зҡ„жҪңж°ҙй’ҹпјҹжңүжІЎжңүдёҖеҲ—жІЎжңүз»ҲзӮ№зҡ„ең°дёӢй“Ғпјҹе“ӘдёҖз§ҚејәеҠҝиҙ§еёҒеҸҜд»Ҙи®©жҲ‘д№°еӣһиҮӘз”ұпјҹеә”иҜҘиҰҒеҺ»е…¶е®ғзҡ„ең°ж–№жүҫгҖӮжҲ‘еҺ»дәҶпјҢеҺ»жүҫжүҫгҖӮгҖҚ(еҗҢдёҠпјҢйЎө127)

жҲӣзәіжңҖдҪіеҜјжј”еҘ–еҫ—дё»гҖҠжҪңж°ҙиЎЈдёҺиқҙиқ¶/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гҖӢжғіиҰҒи®Іиҝ°зҡ„зңҹе®һж•…дәӢпјҢж”№зј–иҮӘгҖҠELLEгҖӢдё»зј–и®©В·еӨҡзұіе°је…ӢВ·жіўиҙқзҡ„иҮӘдј дҪ“е°ҸиҜҙпјҢ97е№ҙжі•еӣҪжңҖз•…й”Җеӣҫд№ҰгҖӮз”·дё»дәәе…¬и®©еӨҡпјҲдҪңиҖ…пјүжҹҗдёҖеӨ©зӘҒ然иә«жӮЈйҮҚз—…пјҢеӣӣиӮўиәҜдҪ“дё§еӨұжҙ»еҠЁиғҪеҠӣпјҢеҸӘжңүж„ҸиҜҶж—¶иҖҢжё…йҶ’гҖӮйқ зқҖе”ҜдёҖеҸҜд»Ҙжҙ»еҠЁзҡ„е·Ұзңјзҡ®пјҢйҖҡиҝҮдёҖз§Қзү№ж®Ҡзҡ„ж–№ејҸдёҺеӨ–з•ҢдәӨжөҒпјҢиү°йҡҫзҡ„еҶҷдёӢдәҶд»–еңЁз”ҹе‘ҪжңҖеҗҺж—¶е…үйҮҢзҡ„дёқзј•ж„ҹеҸ—пјҡиӮүдҪ“еҰӮеҗҢжқҹзјҡеңЁеҺҡйҮҚзҡ„жҪңж°ҙиЎЈдёӯпјҢж— жі•еҠЁеј№пјҢиҖҢжҖқз»ӘеҚҙеҰӮиҪ»зӣҲзҡ„иқҙиқ¶пјҢиҮӘз”ұзҡ„йЈһзҝ”гҖӮ
жі•еӣҪеҪұзүҮзҡ„зҫҺеӣҪеҜјжј”жңұеҲ©е®ү.ж–Ҫзәіиҙқе°”еҸҜжҳҜеҗҚеүҜе…¶е®һзҡ„вҖңж–°иЎЁзҺ°дё»д№ү画家вҖқгҖӮдҪңдёәе…«еҚҒе№ҙд»Јд»ҘжқҘжңҖйҮҚиҰҒзҡ„зҫҺеӣҪеҪ“д»ЈиүәжңҜ家пјҢж–Ҫзәіиҙқе°”зҡ„еӨ©еҲҶи§ҰеҸҠеҲ°иүәжңҜзҡ„еҗ„дёӘи§’иҗҪпјҢз”өеҪұд№ҹдёҚдҫӢеӨ–гҖӮжӯӨзүҮд»…д»…жҳҜ画家第дёүе№…вҖҳ第дёғиүәжңҜдҪңе“ҒвҖҷпјҢд»–е·Із»ҸеҸҜд»ҘеЁҙзҶҹзҡ„жҠҠз»ҳз”»зҡ„иүІеҪ©ж„ҹеёҰе…Ҙй•ңеӨҙпјҢйқ еӨ§йҮҸзҡ„иҷҡй•ңпјҢй—Әеӣһе’Ңи¶…зҺ°е®һпјҢжқҘйҮҚеЎ‘з”·дё»и§’зҡ„дәәз”ҹпјҢз”ЁеҺӢзј©зҡ„ж—¶з©әж„ҹеҲҮжҚўдәәзү©е’Ңи§Ӯдј—зҡ„еҝғзҗҶгҖӮдёҖдёӘз”·дәәпјҢеңЁз”ҹе‘ҪжңҖеҗҺзҡ„ж—¶е…үйҮҢпјҢиҝҪеҝҶиҮӘе·ұзҡ„зҲұжғ…пјҢи°ғдҫғжӣҫз»ҸзІҫеҪ©зҡ„дәәз”ҹпјҢз”ҡиҮійҮҚж–°иҝ·жҒӢдёҠж–°зҡ„еҘідәәгҖӮиҝҷдәӣж··д№ұпјҢжүӯжӣІзҡ„еҸҷдәӢйҖ»иҫ‘пјҢзңҹе®һдёҺжғіиұЎе№¶дёҫпјҢз«ҹ然иғҪиў«ж–ҪзәіжҜ”е°”еӨ„зҗҶзҡ„еҰӮжӯӨзҫҺеҰҷпјҢи®©и§Ӯдј—йғҪдёҚзҰҒзҲұдёҠдәҶеү§дёӯзҡ„з”·з”·еҘіеҘігҖӮ
еңЁеҫҲеӨҡжғ…еҶөдёӢпјҢи§Ӯдј—жҳҜз«ҷеңЁи®©еӨҡзҡ„дё»и§ӮдҪҚзҪ®пјҢд»Һд»–е”ҜдёҖеҸҜд»Ҙж„ҹзҹҘзҡ„и§Ҷи§’пјҢжҺҘи§ҰйҖҗжёҗиҗҺзј©жЁЎзіҠзҡ„еӨ–йғЁдё–з•ҢгҖӮиҖҢдёҺеӨ–еңЁж„ҹи§үз”ұз№ҒеҲ°з®Җзӣёе№іиЎҢзҡ„пјҢжҳҜдё»дәәе…¬еҶ…йғЁзІҫзҘһеұӮйқўзҡ„жё…жҷ°жўізҗҶгҖӮж„ҲеҲ°еҪұзүҮеҗҺеҚҠйғЁпјҢи®©еӨҡзҡ„еӣһеҝҶж„ҲеҠ жҳҺжң—пјҢж„ҹжғ…еҜ№иұЎд№ҹжӣҙеҠ дё°еҜҢз«ӢдҪ“гҖӮд»–дёҺдёҚеҗҢеҘідәәзҡ„зҲұжғ…жёёжҲҸпјҢе’ҢеүҚеҰ»еӯ©еӯҗ们зҡ„еӨ©дјҰд№Ӣд№җпјҢд»ҘеҸҠе№ҙиҝҲиҖҒзҲ¶зҡ„еқҰиҜҡеҖҫиҜүпјҢйғҪз»Ҷи…»зңҹе®һзҡ„жү“еҠЁзқҖи§Ӯдј—гҖӮе°Өе…¶жҳҜи®©еӨҡдёҺзҲ¶дәІзҡ„йӮЈеңәжҲҸпјҢиҷҪзқҖеўЁдёҚеӨҡпјҢеҚҙжҳҜжң¬зүҮзҡ„йҮҚзӮ№гҖӮд№ҹе°ұжҳҜиҜҙеҜјжј”ж–ҪзәіжҜ”е°”жң¬дәәе°ұжҳҜдёәдәҶз”Ёиҝҷж®өжғ…з»ӘжқҘиҝҪеҝҶзҲ¶дәІпјҢжҺўи®Ёжӯ»дәЎпјҢжүҚдјҡжғіеҲ°жӢҚеҮәиҝҷйғЁеҪұзүҮгҖӮ

ж‘„еҪұеҸ–жҷҜпјҢз”»еӨ–йҹіе’Ңй…Қд№җеңЁеҪұзүҮдёӯз»ҷдәәз•ҷдёӢжңҖж·ұеҲ»зҡ„еҚ°иұЎпјҢеҗҢж—¶д№ҹжҳҜеҜјжј”йўҮдёәеҫ—ж„Ҹзҡ„дёӘдәәйЈҺж јж ҮзӯҫгҖӮдё»и§Ӯй•ңеӨҙзҡ„еӨ§йҮҸиҝҗз”ЁпјҢеҝҪи§Ҷжһ„еӣҫзҡ„е®Ңж•ҙжҖ§пјҢиө°з„ҰпјҢз©әй•ңйҡҸеӨ„еҸҜи§ҒпјҢдёәзҡ„жҳҜи®©и§Ӯдј—еҲҮиә«дҪ“йӘҢеҲ°дёҖдёӘзҳ«з—Әз—…дәәзҡ„з—ӣжҘҡгҖӮиҖҢжңүж—¶иҝҷз§Қз—ӣиӢҰеҸҲдјҙйҡҸзқҖдёҖз§ҚиҜ—ж„Ҹзҡ„е®ҒйқҷпјҢйңІеҸ°дёҠзҡ„ең°е№ізәҝжҷҜи§Ӯи®©дәәжғіеҲ°дәҶе®үдёңе°јеҘҘе°јзҡ„гҖҠеҘҮйҒҮгҖӢпјҢжө·ж°ҙзҡ„еҢ…е®№еҸҲдјјд№Һж¶ҲиһҚдәҶвҖҳжҪңж°ҙиЎЈвҖҷзҡ„жқҹзјҡгҖӮз”»еӨ–йҹійҮҢзҡ„и®©еӨҡжҳҜйӮЈд№Ҳзҡ„д№җи§ӮпјҢиў«иҮӘе·ұзҡ„иәҜдҪ“з»‘жһ¶ж—¶пјҢд№ҹиғҪж”ҫйЈһжҖқжғізҡ„иқҙиқ¶пјҢи®©жӯ»дәЎзҡ„жҒҗжғ§и¶ҠйЈһи¶ҠиҝңгҖӮеҪ“и®°еҝҶзҡ„зўҺзүҮиў«дҝЎжүӢжӢҲжқҘпјҢжӢјжҲҗдәҶж–°зҡ„еҜ„иҜӯпјҢйӮЈе°ұйҖҡиҝҮе·ҰзңјйҮҢзҡ„зӘ—еҸЈпјҢз•ҷз»ҷзҫҺдёҪзҡ„жҠӨеЈ«пјҡвҖңE,S,A,R…йҖүдёӯдәҶеӯ—жҜҚе°ұзңЁзңјгҖӮиӮҜе®ҡзңЁдёҖдёӢпјҢеҗҰе®ҡзңЁдёӨдёӢвҖқпјҢеңЁе°ҸиҜҙеҮәзүҲеҗҺзҡ„第еҚҒеӨ©пјҢи®©В·еӨҡзұіе°је…ӢВ·жіўиҙқзҰ»ејҖдәҶдәәдё–пјҢеҚҙжҠҠиҮӘе·ұзҡ„з”ҹе‘Ҫз•ҷз»ҷдәҶжҲ‘们гҖӮ
жӯЈжҳҜеҜјжј”жң¬дәәзҡ„жҖ§ж јдёҺеҺҹдҪңиҖ…жңүйўҮеӨҡзӣёдјјпјҢж„ҹжҖ§пјҢзғӯжғ…пјҢе……ж»Ўе№Ҫй»ҳпјҢд»–жүҚиғҪжҠҠиҝҷдёӘе…ідәҺжӯ»дәЎзҡ„ж•…дәӢеӨ„зҗҶзҡ„еҜҢеҗ«вҖҳ笑ж„ҸдёҺиҮӘз”ұвҖҷпјҢдёҚиҗҪдҝ—еҘ—гҖӮйҮҮи®ҝж—¶зҡ„ж–Ҫзәіиҙқе°”дёҖиә«зқЎиЎЈпјҢйҡҸж„Ҹзҡ„ејҖзқҖзҺ©з¬‘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еҜ№й…’еә—еӨ–зҡ„е–§й—№иЎЁзӨәеҺҢжҒ¶е’ҢжҠұжҖЁж—¶пјҢд№ҹдёҚеҝҳеҠ дёҠдёҖеҸҘпјҡвҖңеә”иҜҘи®©иҝҷдәӣжұЎжҹ“з©әж°”зҡ„дәәеҺ»еқҗзүўпјҒ..е“ҰдёҚпјҢиҝҷд№ҲиҜҙеӨӘйҮҺиӣ®дәҶпјҢдёҚеә”иҜҘжңүд»»дҪ•дәәеқҗзүўпјҢ他们йғҪеә”иҜҘеҺ»еқҗз”өжӨ…гҖӮвҖқ
дәәйқ д»Җд№Ҳжҙ»зқҖпјҹжҳҜеҝғи„ҸжҸҗдҫӣз»ҷдәәдҪ“зҡ„еҠЁеҠӣпјҢиҝҳжҳҜеӨ–з•Ңз»ҷдәҲдәә们иҮӘиә«зҡ„ж— ж•°еӨ–еҠӣж”Ҝж’‘пјҢдәҰжҲ–жҳҜеҘҮиҝ№еңЁеҶҘеҶҘд№ӢдёӯйҷҚдёҙдёҺдәәзұ»зҡ„дёҖз§ҚйқһиҮӘ然зҡ„зІҫзҘһеҠӣйҮҸпјҹиҝҷз§ҚеҠӣйҮҸд№ҹи®ёд»ҺжңӘиў«дәә们еҸ‘и§үпјҢжҳҜдёҚе№ёдҪ“зҺ°еҮәдәҶдәәзҡ„жң¬жҖ§пјҢеҪ“дҪ и®Өдёәз”ҹе‘Ҫдёӯзҡ„дёҖеҲҮйғҪеңЁжӮ„жӮ„д»ҺдҪ иә«иҫ№жәңиө°зҡ„ж—¶еҖҷпјҢдәәзҡ„жң¬жҖ§еҸ‘жҢҘеҮәиҖҖзңјзҡ„е…үиҠ’пјҢзәөдҪҝиә«дҪ“дёҠзҡ„дёҚе№ёдҪҝд»–еғҸжҪңж°ҙй’ҹдёҖж ·жІүе…Ҙж·ұжө·д№ӢдёӯпјҢжҖқиҖғпјҢжҖқжғізҡ„жҢЈжүҺи®©иқҙиқ¶жҲҗдёәд»–зҝұзҝ”зҡ„еҸҰдёҖдёӘиә«дҪ“пјҢжөҒиҝһдәҺдё–з•ҢдёҠд»»дҪ•дёҖеӨ„ең°ж–№пјҢиҮӘз”ұй©°йӘӢпјҢз”ҹе‘ҪеңЁдёҖеҸӘзңјзқӣзҡ„иҪ¬еҠЁдёӯжүҫеҲ°дәҶе®Јжі„зҡ„еҮәеҸЈпјҢз»Ҫж”ҫеңЁж— еЈ°ж— жҒҜзҡ„йқҷжӯўеҪ“дёӯгҖӮ

йҳҝе…°еҫ·жіўйЎҝиҜҙпјҡдёҖдёӘиҝҮзЁӢзӘҒ然еӨұеҺ»зӣ®зҡ„пјҢдәәдјҡж„ҹеҲ°иҚ’и°¬гҖӮиҚ’и°¬жҳҜжё…йҶ’зҡ„дәәзҡ„ж„ҹи§үгҖӮиҝҷдёӘеӨұеҺ»дәҶзӣ®зҡ„зҡ„иҝҮзЁӢпјҢй•ҝ久延з»ӯдёӢеҺ»пјҢдәәе°ұдјҡз–Ід№ҸпјҢйә»жңЁиҖҢиҚ’и°¬ж„ҹд№ҹе°ұиў«ж— иҒҠж„ҹеҸ–д»ЈдәҶпјҢд»…еңЁжҹҗдәӣжё…йҶ’зҡ„зүҮеҲ»жө®зҺ°еҮәжқҘгҖӮиҖҢйІҚжҜ”зҡ„жҖқжғіе’Ңи®°еҝҶжҳҜд»–еӯҳеңЁзҡ„зӣ®зҡ„пјҢиҚ’и°¬ж„ҹд»ҺжңӘдә§з”ҹпјҢеңЁз”ҹе‘ҪеҚіе°Ҷз»“жқҹеүҚеӨ•пјҢз”ҹе‘Ҫд»Қ然жҢЈжүҺзқҖпјҢеңЁе»¶з»ӯпјҢдёҚзҹҘз–Ід№ҸгҖӮ
 RSS
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