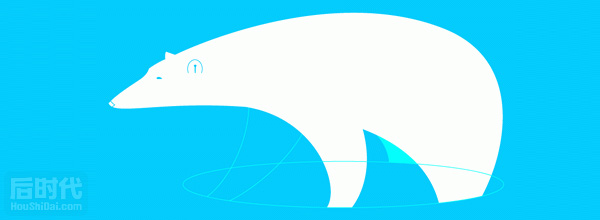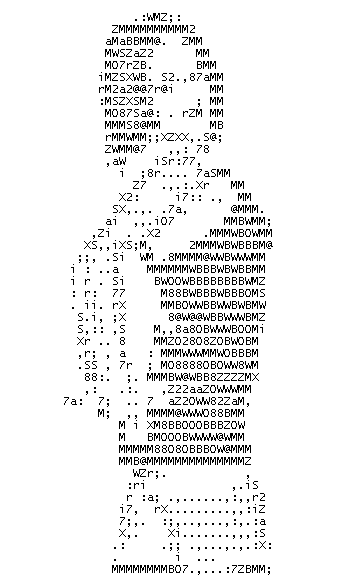萨特为什么拒领诺贝尔奖

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萨特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十月十五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有决定。这时我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科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给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科学院做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权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做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 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做出的拒绝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萨特传》
“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并没有资格来授予。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我认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给我的荣誉,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从没有对准我。我完全反对诺贝尔奖,因为它把作家分成等级。如果15世纪或者16世纪就有诺贝尔奖,我们就会看到,克莱芒?马罗得了奖,而康德没有得到它──他本应该得到的,但因为混乱或因为评审团的某些成员做了这事那事,这奖没有给他──当然,维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这时,文学好像完全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
“我发表了《词语》,他们认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给了我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这就给了我的作品一种新的价值。但人们本该在一年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在我还没有发表这本书时,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我非常喜欢海明威,我个人也认识他,我在古巴同他见过面。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萨特简介——
让-保罗·萨特,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
萨特生活——
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与许多人把笔耕看成是一种苦役不同,萨特把它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一张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
萨特与他的勤奋和声望不相称的是,他的物质生活极其简陋粗淡。在这方面,他是本质先于存在。他的收入并不少,有时甚至有成百万的钱在口袋里。但他乐施好舍,不知经纪,加上视财富如粪土,再多的钱也放不了几天。 萨特在巴黎最后的住处在爱德加·基内大街29号,第10层楼上。从楼上能望见他长眠的公墓。那是个很小的被称之为“悲惨”的套房,现在已换了房客,没有任何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的标志。即使保留原貌的话,里面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少的不能再少的旧家具,几个烟灰缸,小半架子零乱的书。这个生前对身外之物极端不在乎的人,对死后人们如何纪念他也同样不在乎。
终生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法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女权主义者,著有《第二性》)
萨特一直和波伏娃同居,他俩结识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两人的爱情建立在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爱好上。萨特去世后物,波伏娃为他写过一部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仪式》,死后和萨特一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萨特生平——
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法国巴黎的富裕阶层家庭。父亲让-巴浦蒂斯特·萨特是海军工程师。在萨特1岁零3月去世。四岁时萨特由于角膜翳导致右眼斜视。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来有些丑陋。母亲是安-玛丽 萨特(婚前姓史怀哲)在萨特父亲去世后带着萨特前往阿尔萨斯,在做法文教师的外祖父家里生活,尽管他日后排斥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里的知识氛围让萨特在写作和文学上受益很多。而据说他读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
萨特最初在蒙田公立学校上学,在祖父的要求下校长让萨特直接上8年级(最低年级是10年级预备班),但很快以基础太差而被要求从10年级开始就读。祖父则在一气之下让他退了学。请老师在家给他上课。这使得萨特接触同龄人的时间被推迟了几年。10岁萨特进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学校,后来转到了拉罗舍尔公立学校,3年后,他又随外祖父重新就读亨利四世学校。在就读了2年后家里让他转到了路易大帝学校。因为后者的文科预备班可能要好。不久萨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攻读哲学。在这期间,萨特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主要著作。这对他后来有了不小的影响。巴黎高师每年的戏剧演出活动,这使萨特开始重新对戏剧喜好起来。并写了他的第一个独幕剧《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萨特在大学期间通过朋友关系认识了在巴黎大学就读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后来被称为萨特的“终生伴侣”。当时他们都在准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
1929年,萨特萨特在一个气象台里服兵役,为期1年半。1931年4月,萨特去了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La Havre),在高中教哲学,同时写作小说和哲学论文。
1933年,萨特前往柏林,进修胡塞尔的现象学。1934年,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或译《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一文。1936年又发表了《影像论》(或译《想象》)(《L’Imagination》)这是萨特对现象学研究后的论文。
1936年萨特完成了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的第三稿。萨特将它定名为《忧郁》,起初这篇稿子被出版社拒绝。后又几经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出版社终于又重新接受了这份作品。但名字建议改为《恶心》(Nausea)。1938年4月,《恶心》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虽然不是特别畅销,但评论界反应不错。有人把萨特和卡夫卡相提并论。称他为法国的卡夫卡。萨特认为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书。
在小说《恶心》出版之前,萨特得到了出版社的几个短篇的约稿,于是《墙》、《艾罗斯特拉特》和《不自在》相继发表。而《房间》和《亲密》也都接近完稿。伽利玛出版社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艾罗斯特拉特》、《墙》等其他几篇已经发表的小说合在一起,作为小说集《墙》出版。这本小说集非常受欢迎。萨特也真正的开始有名气起来。
 RSS
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