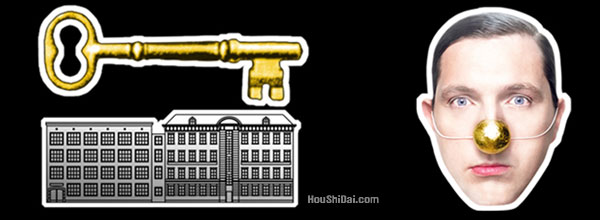жЧ†еН∞иЙѓеУБй£Ож†ЉеРѓз§ЇпЉЪжЬ±йФЈиЃњи∞ИељХ

жЧ†еН∞иЙѓеУБй£Ож†ЉеРѓз§ЇпЉЪеОЯз†ФеУЙиЃЊиЃ°е±ХиІИеЬ®еМЧдЇђеЙНй׮姩еЃЙжЧґйЧіиЙЇжЬѓй¶Же¶ВзБЂе¶ВиНЉзЪДдЄЊи°МзЭАпЉМиЃ©жИСдїђйЗНжЦ∞еЃ°иІЖдЄАдЄЛжЧ†еН∞иЙѓеУБеѓєжИСдїђзЪДеРѓз§ЇеРІгАВ
дЄЦзХМеМЦзЪДиЃЊиЃ°пЉМеЬ®еОЯз†ФеУЙењГзЫЃдЄ≠пЉМжШѓдЄНе≠ШеЬ®зЪДгАБжШѓдЄНеРИйАїиЊСзЪДпЉЪвАЬжЧ•жЬђзЪДиЃЊиЃ°е∞±ж∞ЄињЬжШѓжЧ•жЬђзЪДиЃЊиЃ°гАВе∞±дї•MUJIдЄЇдЊЛпЉМж∞ЄињЬйГљдЄНдЉЪзФ±дЄАдЄ™жЧ•жЬђеУБзЙМеПШжИРдЄЦзХМеУБзЙМгАВ жАїеЕ±6000е§ЪдЄ™й°єзЫЃзЪДMUJIпЉМйГљжШѓзФ±ељУеЬ∞жЛ•жЬЙеЕ±йАЪиѓ≠и®АзЪДиЃЊиЃ°еЄИпЉМдї•ељУеЬ∞дЇЇзЪДзФЯжіїж®°еЉПеПКдє†жГѓдЄЇеЯЇз°АиАМеЃМжИРзЪДиЃЊиЃ°гАВдљЬдЄЇдЄАдЄ™жЬЙжВ†дєЕиЃЊиЃ°еОЖеП≤зЪДеЫљеЃґпЉМжИСдїђеєґдЄНзГ≠и°ЈдЇОжИРдЄЇеЕ®зРГеМЦзЪДдЄАеИЖе≠РпЉМињЗеИЖеНХзЇѓеМЦзЪДжЩЃеПКжШѓжИСдїђењЕй°їеК™еКЫйБњеЕНзЪДгАВ
дЄ≠еЫљзЪДй£ОеЇ¶жАОдєИеЖНеЫЮжЭ•
жЬ±йФЈпЉЪжЧ†еН∞иЙѓеУБзЪДж¶ВењµжШѓзФ∞дЄ≠дЄАеЕЙеЕИзФЯеЬ®1980еєідї•вАЬжЬАйАВеРИзЪД嚥жАБе±ХзО∞дЇІеУБжЬђиі®вАЭдЄЇжМЗеѓЉжАЭжГ≥жПРеЗЇжЭ•зЪДпЉМеЃГињљж±ВеЄ¶зїЩжґИиієиАЕвАЬињЩж†ЈжЬАе•љвАЭзЪДжї°иґ≥жДЯпЉМеєґе∞ЖдљњвАЬињЩж†ЈжЬАе•љвАЭзЪДжї°иґ≥жДЯе∞љйЗПжПРеНЗеИ∞жЬАйЂШзЂѓдЄЇзЫЃж†ЗгАВ
жИСжЫЊеЬ®зФ∞дЄ≠дЄАеЕЙиЃЊиЃ°дЇЛеК°жЙАеЈ•дљЬпЉМжЧ†еН∞иЙѓеУБеЫЊељХе∞±жШѓжЧ•еЄЄеЈ•дљЬдєЛдЄАгАВжККжЧ†еН∞иЙѓеУБзЪДзЬЯж≠£жДПдєЙдї•е±ХиІИзЪД嚥еЉПеБЪеИ∞дЄ≠еЫљжЭ•пЉМжШѓжИСе§ЪеєізЪДжДњжЬЫгАВињЫжЭ•пЉМжИСжЬАињСдЄАзЫіеЬ®жАЭиАГе±ХиІИзЪДдЇЛгАВжИСдЄНеЄМжЬЫдї•жЧ†еН∞иЙѓеУБз≤ЙдЄЭзЪДиІТеЇ¶жЭ•еБЪе±ХиІИпЉМдЄНжШѓжККдЄАдЄ™еЉЇеКњеУБзЙМеБЪеИ∞дЄ≠еЫљжЭ•пЉМиАМжШѓдїОжО•зЇ≥зЪДиІТеЇ¶жЭ•еБЪгАВе±ХиІИеРНдЄЇвАЬжЧ†еН∞зЪДдЄ≠еۚ姩穯вАЭпЉМжИСиЃ§дЄЇпЉМ вАЬеЬ®дЄ≠еЫљвАЭињЩдЄ™жАБеЇ¶еЊИйЗНи¶БгАВжИСдїђдї•еє≥иІЖзЪДиІТеЇ¶пЉМиАМдЄНжШѓдї∞иІЖгАВ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еЕґеЃЮпЉМдЄ≠еНОж∞СжЧПзЪДеРМеМЦиГљеКЫжШѓеЊИеЉЇе§ІзЪДгАВеЬ®еП§дї£пЉМдїЦдїђе∞ЖдЉКжЛЙеЕЛзЪДеОЯжЦЩињРеИ∞дЄ≠еЫљпЉМеПШжИРдЇЖйЭТиК±зУЈпЉМдЄЙељ©йЗЙдєЯжШѓзФ±и•њйГ®зЪДиГ°дЇЇињЫеП£иАМжЭ•пЉМе∞±еПШжИРжИСдїђжЦ∞зЪДдЉ†зїЯзЪДдЄАйГ®еИЖгАВжЙАдї•иѓіпЉМдЄ≠еЫљдЉ†зїЯжЦЗеМЦзЪДз≤ЊйЂУе∞±жШѓе∞ЖжЙАжЬЙзЪДжЦЗеМЦйГљиЮНеРИеЬ®дЄАиµЈгАВжИСиЃ§дЄЇпЉМзО∞еЬ®ињЩзІНз≤Њз•ЮдєЯдїНзДґе≠ШеЬ®гАВеЬ®зО∞дї£пЉМеЃМеЕ®еНХжЦєйЭҐжО•еПЧе§ЦеЫљжЦЗеМЦзЪДзГ≠жљЃдєЯе∞ЖжШѓзЙєеИЂзЯ≠жЪВзЪДжЧґйЧігАВдЄ≠еЫљеП§дї£жФєжЬЭжНҐдї£йВ£дєИе§ЪпЉМж±ЙжЦЗеМЦеТМж±Йе≠Чж≤°иҐЂжґИзБ≠пЉМдєЯж≤°жЬЙеПШжИРиТЩеП§жЦЗжИЦиЧПжЦЗгАВпЉИжЬ±пЉЪжЬАзїИзХЩдЄЛзЪДињШжШѓж±ЙжЧПгАВпЉЙжЙАжЬЙе§ЦжЭ•зЪДжЦЗеМЦйГљеГПжШѓи°Ажґ≤йЗМзЪДеРДзІНиР•еЕїпЉМеЃГиГљдљњиВМдљУеЉЇе§ІиАМдЄНжШѓеЙКеЉ±пЉМињЩжШѓдЄ≠еЫљзЪДе§ІеЫљй£ОеЇ¶гАВзО∞еЬ®зЪДйЧЃйҐШжШѓпЉМдЄ≠еЫљзЪДй£ОеЇ¶жАОдєИеЖНеЫЮжЭ•пЉЯ
жЬ±йФЈпЉЪињЩзВєйЭЮеЄЄйЗНи¶БгАВжИСдїђдЄАеЃЪи¶БжККжАБеЇ¶йЭЮеЄЄжШОз°ЃгАВињЩж†Је∞±еПѓдї•еЃМеЕ®дЄНеРМдЇОдїїдљХдЇЇжЭ•еБЪMUJIињЩдїґдЇЛпЉМзЫЃеЙНпЉМеЫізїХеЬ®жИСдїђзФЯжіїеС®иЊєзЪДеХЖеУБеЈ≤зїПдЄ§жЮБеМЦпЉМдЄАзІНдї•дЇІйЗПзЪДз®Ае∞СжАІгАБж≥®йЗНжПРйЂШеУБзЙМиЗ™иЇЂдїЈеАЉдЄЇжЦєеРСпЉЫеП¶дЄАзІНзЂ≠е∞љжЙАиГљжО®и°МдљОдїЈз≠ЦзХ•гАВжЧ†еН∞иЙѓеУБеИЩеЬ®зФЯжіїзЪДвАЬеЯЇжЬђвАЭдЄОвАЬжЩЃйБНвАЭйЧіеѓїеЊЧжЦ∞зЪДдїЈеАЉиІВпЉМеЬ®йА†еЮЛзЪДвАЬжЬізі†вАЭдЄОвАЬзЃАзЇ¶вАЭ дЄ≠е°СйА†еЗЇдЇЖжЦ∞зЪДеЃ°зЊО嚥еЉПгАВеПѓдї•жГ≥еГПдЄАдЄЛпЉМе¶ВжЮЬжЧ†еН∞иЙѓеУБињЩдЄАж¶ВењµжШѓеЬ®еЊЈеЫљиѓЮзФЯпЉМдЉЪжШѓжАОж†ЈзЪДеХЖеУБпЉЯеЬ®жДПе§ІеИ©иѓЮзФЯеПИдЉЪе¶ВдљХпЉЯжЫійЗНи¶БзЪДжШѓпЉМеЖНжГ≥еГПдЄАдЄЛпЉМиЛ•жШѓеЬ®зФЯжіїжДПиѓЖйАРжЄРжИРзЖЯзЪДдЄ≠еЫљйЗМпЉМжЧ†еН∞иЙѓеУБдЉЪе±ХзО∞жАОж†ЈзЪДжЩѓи±°еСҐпЉЯжИСиІЙеЊЧпЉЪињЩзІНзЬЛдЉЉеє≥еЄЄзЪДжГ≥еГПеЬ®дїКжЧ•йЭЮеЄЄйЗНи¶БгАВжЧ†еН∞иЙѓеУБпЉМжЧ†зЦСжШѓдЄЇжИСдїђжПРдЊЫдЇЖйЂШеЇ¶зЪДж†ЗжЭЖеТМеПѓдЊЫеПНзЬБзЪДйХЬе≠РгАВ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еИЖеѓЄйЬАи¶БжККжП°гАВжЧ†еН∞жШѓдЄ™еУБзЙМпЉМеЃГеЕЈжЬЙиІЖиІЙиѓЖеИЂжАІгАВеЃГзЪДдЇІеУБжАОдєИж†ЈпЉМйҐЬиЙ≤жАОдєИж†ЈпЉМзїЩдЇЇзЪДжДЯиІЙе¶ВйАПжШОгАБеНКйАПжШОгАБеГПиҐИи£ЯдЄАж†ЈйїСиЙ≤еТЦеХ°иЙ≤зБ∞иЙ≤зЪДи°£жЬНз≠Йз≠ЙгАВеБЪдЇЫдїАдєИдЄЬи•њеП™и¶БдЄНињЭеПНињЩдЇЫжДЯиІЙе∞±еПѓдї•гАВдЄНи¶БиіђдљОпЉМдєЯдЄНи¶БжХЕжДПжКђйЂШпЉМе∞ЖеЃГеЃҐиІВе±Хз§ЇеЗЇжЭ•гАВ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зО∞еЬ®пЉМеБЪжЧ†еН∞иЙѓеУБзЪДдЇЛжГЕжЬЙдЄАдЄ™е∞КдЄ•зЪДйЧЃйҐШгАВжИСдїђжЫЊзїПж≤°жЬЙе∞КдЄ•пЉМй¶ЩжЄѓжЯРеУБзЙМзФ®зЃАеНХзЪДж®°дїњеТМеНСеК£зЪДеХЖдЄЪи°МдЄЇе∞ЖвАЬжЧ†еН∞иЙѓеУБвАЭињЩдЄ™еУБзЙМж≥®еЖМпЉМдљњеЊЧжЧ•жЬђзЪДжЧ†еН∞ињЫдЄНдЇЖдЄ≠еЫљпЉМиАљиѓѓдЇЖеЊИе§ЪеєігАВеРОжЭ•пЉМжЧ•жܐ赥дЇЖеЃШеПЄпЉМ赥зЪДйВ£е§©ж≠£е•љжШѓз¶ПзФ∞й¶ЦзЫЄиЃњйЧЃдЄ≠еЫљпЉМжШЊзДґдЄ≠еЫљжШѓжККињЩдЄ™дљЬдЄЇдЄАеЉ†жФњж≤їзЙМжЭ•жЙУгАВзО∞еЬ®зЪДзКґеЖµиѓБжШОдЄ≠еЫљеПШеЊЧжЬЙжЦЗеМЦдЇЖпЉМжИСдїђеЬ®еє≥з≠ЙзЪДеє≥еП∞дЄКе∞Ждљ†жО•жФґињЫжЭ•пЉМжЧҐдЄНжШѓжО†е§Їдљ†пЉМдєЯдЄНжШѓи¶БжКДиҐ≠дљ†пЉМдєЯдЄНжШѓи¶БиіђдљОдљ†гАВдљЖжШѓпЉМињЩйЗМйЭҐжЬЙиЗ™еЈ±зЪДдЄАж†євАЬз≠ЛвАЭпЉМе∞±жШѓжИСдїђе∞ЖеЃГжґИеМЦињЫжЭ•пЉМжО•жФґињЫжЭ•гАВ
MUJIе∞Жз¶ЕжЦЗеМЦжЧ•еЄЄеМЦ
еЯОеЄВзФїжК•пЉЪжЧ†еН∞иЙѓеУБињЫдЄ≠еЫљпЉМзїЩжИСдїђеЄ¶жЭ•жАОж†ЈзЪДжАЭиАГпЉЯ
жЬ±йФЈпЉЪжЧґдї£еЬ®дЄНжЦ≠еПШеМЦпЉМдљЖиЃЊиЃ°зЪДдїЈеАЉдЄНеЇФиѓ•жЬЙжЙАжФєеПШгАВеЬ®ињЗеЊАзЪДеЗ†еНБеєідЄ≠пЉМжИСдїђеИЫйА†дЇЖдЄАдЇЫдљЖеПИжЙФжОЙдЇЖеЊИе§ЪдЄЬи•њпЉМеП™и¶БиГљжО®еК®зїПжµОеПСе±ХпЉМе∞±еПѓдї•еЉ†жЙђиЗ™еЈ±зЪДдЄ™жАІгАВдљЖзО∞еЬ®пЉМжИСдїђеЇФиѓ•жДПиѓЖеИ∞ењЕй°їиАГиЩСиµДжЇРгАБзОѓеҐГгАБзЫЄдЇТйЧізЪДзРЖиІ£дї•еПКеЕґдїЦеЗЇзО∞зЪДйЧЃйҐШгАВиЃЊиЃ°еЄИдЄАдЄ™дЇЇжШѓеИЫйА†дЄНеЗЇдїїдљХдЇІеУБзЪДгАВеП™жЬЙељУиЃЊиЃ°еЄИеПСзО∞дЇЖињЩдЄ™з§ЊдЉЪжЙАйЬАи¶БзЪДдЄЬи•њдєЛжЧґпЉМдїЦдїђжЙНеПѓдї•иЃЊиЃ°дЇЫдЄЬи•њжЭ•жї°иґ≥ињЩдЇЫдЇЇзЪДйЬАи¶БгАВиЃЊиЃ°зЪДзЙєзВєжШѓзФ±з§ЊдЉЪйЬАж±ВеЖ≥еЃЪзЪДпЉМиЃЊиЃ°дљЬеУБзЪДжЧґеАЩжИСдїђењЕй°їиАГиЩСеИ∞з§ЊдЉЪзОѓеҐГгАВ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жЧ†еН∞иЙѓеУБзїЩдЇЖжИСдїђдЄАдЄ™еРѓз§ЇпЉМиЃ©жИСдїђйЗНжЦ∞еѓїжЙЊдЄ≠еЫљдЉ†зїЯдЄ≠е•љзЪДдЄЬи•њгАВеЫ†дЄЇпЉМжЧ†еН∞еЖЕйЗМеЃ£жЙђзЪДжШѓз¶ЕеЃЧзЪДзЊОе≠¶пЉМеЃГжШѓз¶ЕзЪДжДПењµзЪДжЧ•еЄЄеМЦпЉМиЃ©з¶ЕдЄНеЖНеП™жШѓеЃЧжХЩзЪДзРЖењµпЉМжИЦжШѓе∞ПеЬИе≠РдЄ≠дЉ†жТ≠зЪДжАЭжГ≥гАВеЕґеЃЮпЉМдЄ≠еЫљињСдї£жЦЗеМЦдЄАзЫіеИ∞жШОжЄЕпЉМжЬАжШОжШЊзЙєеЊБжШѓжККдЄ≠еЫљйЂШзЂѓжЦЗеМЦгАБжЦЗдЇЇжЦЗеМЦгАБеЃЂеїЈжЦЗеМЦгАБзїЉеРИжЦЗеМЦжЭ•жЧ•еЄЄеМЦгАВжѓФе¶ВпЉМжШОжЬЂжЄЕеИЭиСЧеРНзЪДжИПжЫ≤еЃґжЭОжЄФпЉМдїЦеЖЩеЙІжЬђпЉМзФЯжіїеЊЧйЭЮеЄЄиЙЇжЬѓгАВеОЖеП≤дЄКж≤°жЬЙеУ™дЄАдЄ™еЫљеЃґжИЦж∞СжЧПеГПдЄ≠еЫљињЩж†Је∞ЖиЙЇжЬѓзФЯжіїеМЦпЉМе∞ЖиЙЇжЬѓеєњж≥ЫжЄЧйАПеИ∞зФЯжіїзЪДжѓПдЄАдЄ™иІТиРљгАВдљЖжШѓеИ∞дЇЖж∞СеЫље∞±жЦ≠дЇЖпЉМеۆ䪯襀е§ЦеЫљеИЧеЉЇдЊµзХ•пЉМдЇЇж∞СзФЯжіїж∞іеє≥йЭЮеЄЄдљОгАВдЄ≠еНОж∞СеЫљзЪДжЧґеАЩпЉМйАЪиіІиЖ®иГАпЉМж†єжЬђи∞ИдЄНдЄКиЙЇжЬѓеМЦгАВжЧ•жЬђдЄНдЄАж†ЈпЉМжЧ•жЬђзЪДзФЯжіїжЬђжЭ•е∞±йЭЮеЄЄиЙЇжЬѓпЉМеЃГзЪДзФЯжіїиµЈе±ЕжЦєеЉПгАБжЬНи£ЕгАБи£Ей•∞гАБй£ЯеУБпЉМе∞±ињЮиЗ™зФ±еЄВеЬЇйЗМзЪДж§НзЙ©еТМй£ЯзЙ©йГљжСЖжФЊйГљйЭЮеЄЄиЙЇжЬѓеМЦгАВMUJIеЬ®ињЩж≠§еЯЇз°АдЄКеПИжПРйЂШдЇЖдЄАдЄ™е±Вжђ°пЉМеЫ†дЄЇMUJIжККз¶ЕжЦЗеМЦжЧ•еЄЄеМЦгАВељУMUJIзЪДдЄЬи•њжФЊеИ∞и•њжЦєпЉМе§ІеЃґйГљиГљиЊ®жЮРеЗЇеЃГжШѓдЄЬжЦєзЪДжЦЗеМЦгАВдљЖжШѓпЉМе§ІеЃґйГљзЯ•йБУпЉМз¶ЕзЪДдЉ†жТ≠жЄ†йБУе∞±жШѓйАЪињЗеН∞еЇ¶еИ∞дЄ≠еЫљпЉМдїОдЄ≠еЫљеИ∞жЬЭй≤ЬеНКе≤ЫпЉМеЖНзФ±жЬЭй≤ЬеНКе≤ЫдЉ†еИ∞жЧ•жЬђгАВдЄЇдїАдєИжЧ•жЬђдњЭзХЩдЇЖеЃГзЇѓз≤єзЪДдЄЬи•њпЉМеєґе∞ЖеЃГзО∞дї£еМЦпЉМе∞ЖеЃГињЗеОїзЪДдїЈеАЉиІВиљђдєЙдЇЖпЉЯињЩжШѓMUJIдЉ†еИ∞дЄ≠еЫљеРОпЉМжЬАеАЉеЊЧиЃ©жИСдїђжАЭиАГзЪДйГ®еИЖгАВ
жЬ±йФЈпЉЪ”жЧ†еН∞иЙѓеУБ”зЪДиЃЊиЃ°еЄ¶жЬЙеЕЄеЮЛжЧ•жЬђзЊОе≠¶ж∞Фиі®гАВеЕґиЃЊиЃ°зЪДеНУиґКеЬ®дЇОињљж±Вз≤ЊеЗЖгАВжЧ•зФ®еУБиЃЊиЃ°еЊИеЃєжШУеПШжИРеИїжДПжИРдЄЇжЯРз±їдЇЛзЙ©зЪДйЪРеЦїгАВдљЖжШѓпЉМжЧ†еН∞иЙѓеУБеєґжЬ™зїЩдЇЇдї•ж≠§зІНеН∞и±°пЉМиАМдїњдљЫеП™дЄЇиЃ∞ељХзФЯжіїжЧґйЧіиАМе≠ШеЬ®гАВ
еЯОеЄВзФїжК•пЉЪзО∞еЬ®дЄ≠еЫљељУеЙНзЪДзФЯжіїдЄ≠пЉМз¶ЕзЪДдњ°ењµйЭЮеЄЄз®АзЉЇгАВе§ІеЃґйГљеЊИжµЃиЇБгАВ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дЄ≠еЫљдїОжЭ•ж≤°жЬЙеЊИе•љеЬ∞е∞Жз¶ЕзЩљеМЦгАВз¶ЕзЪДзРЖењµжШѓз¶Еж†єжЬђдЄНиѓіз¶ЕпЉМз¶Еж≤°жЬЙжЦЗе≠ЧпЉМж†єжЬђдЄНжПРз¶ЕгАВдљЖжШѓз¶ЕзЪДи°МдЄЇгАБжДПењµгАБжАЭжГ≥пЉМеЊИе§ЪжЦєеЉПжШѓз¶ЕзЪДгАВ
еЯОеЄВзФїжК•пЉЪзО∞еЬ®дЄ≠еЫљзЪД姩穯дЄЛпЉМз¶ЕзЪДжДПењµиГљдЄНиГље§ЯеМЕеЃєпЉЯ
жЬ±йФЈпЉЪзО∞еЬ®дЄНжШѓдЄ≠еЫљзЪД姩穯дЄЛжЬЙж≤°жЬЙзЪДйЧЃйҐШгАВжИСжГ≥пЉМеЇФиѓ•жШѓжЬЙзЪДгАВе¶ВжЮЬзО∞еЬ®ж≤°жЬЙпЉМйВ£жИСдїђе∞±еБЪдЇЫдЇЛжГЕжЭ•еСЉеФ§еЃГгАВжИСдїђжЬАжХПжДЯзЪДеЬ∞жЦєпЉМзО∞еЬ®еНіеПШеЊЧжЬАињЯйТЭгАВжИСиІЙеЊЧжИСдїђињЩжђ°иК±йВ£дєИе§ІеКЫж∞ФжЭ•еКЮињЩдЄ™е±ХиІИпЉМжИСдїђзЪДжАБеЇ¶и¶БжСЖеЊЧйЭЮеЄЄе•љпЉМйЭЮеЄЄз≤ЊеЗЖжЙНи°МгАВеЬ®ињЩдЄ™еЕЕжї°йЭЮжЧ•еЄЄзЪДзФЯжіїзОѓеҐГйЗМпЉМжЧ†еН∞иЙѓеУБжПРдЊЫзЪДжШѓжЧ•еЄЄгАВеЫ†дЄЇдЄНжЦ≠еПНе§НпЉМжИСдїђеЈ≤зїПжДЯиІЙдЄНеЗЇеЃГзЪДзЙєжЃКзЪДжЙНеПѓдї•еПЂдљЬвАЬжЧ•еЄЄвАЭгАВжЦ∞иЃ§иѓЖжЯРзІНдЇЛжГЕпЉМжИЦиАЕзђђдЄАжђ°жО•иІ¶жЬ™зЯ•зЪДдЄЬи•њпЉМеєґйЭЮ вАЬжЧ•еЄЄвАЭгАВ?еИЈзЙЩгАБжіЧзҐЧз≠Йз≠ЙеЃґеЄЄдЊњй•≠еЊЧеЗ†дєОиЃ©жИСдїђжДПиѓЖдЄНеИ∞е≠ШеЬ®зЪДдЄЬи•њеПЂвАЬжЧ•еЄЄвАЭпЉМжЧ†еН∞иЙѓеУБжШѓйАЪињЗжПРдЊЫиІВеѓЯжЧ•еЄЄзФЯжіїзЪДиІВзВєпЉМжПРдЊЫжЮБеЕґжЧ•еЄЄзЪДдЄЬи•њпЉМиЃ©е§ІеЃґеЬ®дљњзФ®ињЗз®ЛдЄ≠пЉМйЗНжЦ∞еЃ°иІЖжЧ•еЄЄзФ®еУБзЪДиЃЊиЃ°еПКйЗНжЦ∞еЃ°иІЖжЧ•еЄЄзФЯжіїгАВжЧ†еН∞иЙѓеУБе∞ЭиѓХйАЪињЗиЃЊиЃ°пЉМдљње§ІеЃґеПѓдї•йЗНжЦ∞еПСзО∞йЪРиЧПеЬ®жЧ•еЄЄзФЯжіїйЗМзЪДжЩЇжЕІпЉМеєґеК™еКЫиЃ©дЇЇдїђзРЖиІ£иЃЊиЃ°еЬ®зО∞еЃЮзФЯжіїдЄ≠зЪДдїЈеАЉгАВ
MUJIжККеЕ®дЄЦзХМељУжИРеЃГзЪДеОЯжЭРжЦЩеЇУ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иЗ™зДґзЪДдЄЬи•њжШѓжЬАеЉЇе§ІзЪДгАВжИСеЙНйШµеОїеЫЫеЈЭзЬЛеИ∞дЇЇеЈ•зЪДжИње≠РеАТдЇЖдЄНе∞СпЉМеПѓж†Сж≤°еАТпЉМиНЙдєЯж≤°еАТгАВеЃГзФЯжЭ•е∞±жЬЙжЯФиљѓжАІеТМеПѓе°СжАІпЉМеЃГиГљжКµеЊ°й£ОжЪігАБйЫ®гАБеѓТжµБгАБеЬ∞йЬЗз≠Йз≠ЙгАВжЙАдї•пЉМжИСжДЯиІЙеЬ®еБЪдЇЇеБЪдЇЛеБЪзЙ©зЪДжЧґеАЩпЉМйЬАи¶БжЬЙињЩзІНеЉЇйЯІзЪДзЙєжАІеЬ®йЗМйЭҐгАВжИСдїђеПѓдї•дїОиЗ™зДґйЗМе≠¶еИ∞еЊИе§ЪдЄЬи•њгАВеГПMUJIжЬЙеП•иѓЭеПЂвАЬиЗ™зДґељУзДґжЧ†еН∞вАЭпЉМеЃГзЪДеОЯжЦЩжШѓзЇѓиЗ™зДґзЪДпЉМжѓФе¶ВеН∞еЇ¶зЪДгАБеНЧзЊОзЪДгАБдЄ≠еЫљйЂШе±±еЬ∞еМЇзЪДз≠Йз≠ЙгАВдЄЇдїАдєИжЙЊињЩдЇЫдЄЬи•њеСҐпЉЯеЫ†дЄЇеЃГи¶БзЪДжШѓеЕґжЬАеОЯжЬђзЪДеУБиі®еТМж∞Фиі®гАВдїЦдїђдЉЪеОїдЄ≠еЫљзЪДдЇСеНЧгАБйЭТиЧПйЂШеОЯеОїеѓїжЙЊпЉМињЩдЇЫеЬ∞жЦєжЬЙеЕґдїЦжµЈжЛФеЬ∞еМЇжЙАдЄНеЕЈжЬЙзЪДдЄЬи•њгАВињЩе∞±жШѓMUJIзЪДз≤Њз•ЮгАВжЬАеИЭпЉМдїЦдїђеЬ®еѓїжЙЊеОЯжЦЩзЪДжЧґеАЩпЉМдїЦдїђиµ∞дЇЖеЊИе§ЪиЈѓпЉМзІѓзіѓдЇЖеЊИе§ЪзЯ•иѓЖгАВдЄНиЃЇжШѓеН∞еЇ¶зЪДжИЦжШѓйЭЮжі≤зЪДеОЯжЦЩпЉМ襀жЛњеИ∞жЧ•жЬђжХідЄ™MUJIз≠ЦеИТзїДжЧґеЖНињЫи°Ми∞ГеТМпЉМељУеЃГеБЪжИРеХЖеУБзЪДжЧґеАЩпЉМжФЊеЬ®MUJIеЇЧйЗМеєґдЄНдЉЪиЃ©дЇЇиІЙеЊЧдЄНеНПи∞ГгАВдЊЛе¶ВеФҐеСРжЛњеИ∞жЧ•жЬђеОїдЇЖпЉМи∞Ге≠РдЄНиГљиЃ©дЇЇжО•еПЧпЉМе∞±жФєйА†жИР MUJIзЪДжЧЛеЊЛгАВMUJIжЬЙиЗ™еЈ±зЪДдЄАе•ЧжЧЛеЊЛгАВ
жЬ±йФЈпЉЪжЙАдї•еИ∞дЇЖзО∞еЬ®ињЩдЄ™жЧґдї£пЉМжИСдїђжКЫеЉАиЃЊиЃ°зЪДдє†жГѓгАБиЃЊиЃ°зЪДе§Ц嚥дЄНиѓіпЉМе∞±жЭРжЦЩжЭ•иѓіпЉМжЧ•жЬђжШѓдЄ™йЭЮеЄЄзЉЇдєПеОЯжЭРжЦЩзЪДеЫљеЃґпЉМдљЖжШѓеЬ®йВ£дЄ™еЬ∞жЦєпЉМMUJIжККеЕ®дЄЦзХМељУжИРеЃГзЪДеОЯжЭРжЦЩеЇУпЉМеИ∞жЬАеРОдЇІеЗЇжЭ•зЪДдЇІеУБдЊЭзДґжЬЙеЃГиЗ™иЇЂзЪДжШОжШЊзЪДдЉШеКњгАВе¶ВжЮЬењљзХ•MUJIзЪДжЭРжЦЩпЉМеЃГеЬ®йА†еЮЛжЦєйЭҐеєґж≤°жЬЙйВ£дєИе§ІзЪДдЉШеКњгАВдљЖжШѓеЃГзЪДйА†еЮЛеТМеЃГзЪДжЭРжЦЩеРИеєґеИ∞дЄАиµЈзЪДжЧґеАЩпЉМеЃГзЪДзЙєжАІе∞±еЗЇжЭ•дЇЖпЉМеЃГзЪДйВ£зІНжЄЕењГеѓ°жђ≤зЪДдЄЬи•ње∞±еЗЇжЭ•дЇЖгАВ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MUJIдЄАеЗЇжЭ•жИСе∞±еЉАеІЛзФ®пЉМиАМдЄФжШѓдЄНйЧіжЦ≠еЬ∞зФ®гАВжИСдїОMUJIйВ£йЗМеЊЧеИ∞зЪДз≤ЊеНОпЉМеПѓдї•зФ®дЄАдЄ™е≠ЧжЭ•ж¶ВжЛђпЉМйВ£е∞±жШѓвАЬзі†вАЭгАВзі†пЉМе∞±жШѓжЧ†йЬАи£Ей•∞пЉМжККе§ЪдљЩзЪДйГ®еИЖеОїжОЙгАВињЩзІНвАЬзі†вАЭдЄНжШѓи£ЕеЗЇжЭ•зЪДжЧґйЂ¶пЉМдєЯдЄНжШѓиЃЊиЃ°еЗЇжЭ•зЪДеЕ≥йФЃиѓНпЉМеЃГжШѓдЇЛзЙ©жЬђиі®зЪДиЗ™зДґеСИзО∞гАВMUJIзі†дЇЖдЇМеНБе§ЪеєіеЊИеЃєжШУдљњдЇЇйЇїжЬ®пЉМе•љеЬ®еЃГдЄАзЫіеїґзї≠еЃЮй™Мз≤Њз•ЮпЉМдЄНжЦ≠еЬ∞еЉХињЫжЦ∞зЪДж¶ВењµпЉМдљЖдњЭжМБеЕґжЬђиі®дЄНеПШгАВжѓФе¶ВMUJIжЧЧдЄЛзЪДйЂШзЂѓз≥їеИЧMUJI LABOгАВLABOжШѓеЫљйЩЕйАЪзФ®зЪДиѓНпЉМеН≥жШѓеЃЮй™МзЪДжДПжАЭгАВMUJI LABOзЪДзђ¶еПЈеЉХзФ®дЇЖжЧ•жЬђз¶ЕеЃЧйЗМзЪДзРЖиЃЇвАФвАФеЬЖгАВеЬЖињЩдЄ™еی嚥еЕґеЃЮдїОдЄ≠еЫљдЉ†ињЗеОїзЪДпЉМдї£и°®еЃЗеЃЩдЄЗзЙ©зЪДзФЯе≠ШдєЛйБУгАВжЧ•жЬђзЪДзФїеЃґзФїдЄАдЄ™еЬЖдї£и°®еЃЗеЃЩпЉМдЇЇйЧіжШѓдЄЙиІТ嚥пЉМжЦєеЭЧдї£и°®еЬЯеЬ∞пЉМжИРдЄЇеЃЗеЃЩзЪДдЄЙдЄ™зђ¶еПЈгАВLABOзЪДзђ¶еПЈеєґдЄНжШѓеЬЖиІДзФїзЪДеЬЖпЉМиАМеГПжШѓж∞іеҐ®зЪДзЧХињєпЉМеЃГиЃ©MUJIзЪДжЬђиі®еЬ®жѓПдЄ™еЬ∞жЦєеЊЧеИ∞жЄЧйАПгАВ
жЬ±йФЈпЉЪдЇЇдїђжѓП姩еПНе§НдљњзФ®зЪДдЄЬи•њдњГжИРдЇЖеЈ•еЕЈзЪДдЇІзФЯгАВиЃЊиЃ°еЇФељУжЫіеЕЈжЬЙзЫЃзЪДжАІгАВ襀䯯俐зЪДзИ±зФ®дљЖж≤°жЬЙеРНзЪДзЪДиЃЊиЃ°дљЬеУБеТМиЃЊиЃ°еЄИжЬЙзЫЃзЪДжАІзЪДиЃЊиЃ°дљЬеУБдїОжЬђиі®дЄКиЃ≤жШѓдЄНеРМзЪДгАВе¶ВжЮЬпЉМиЃЊиЃ°дїОеЉАеІЛе∞±дї•дЉ†жТ≠дЄЇзЫЃзЪДиѓЭпЉМиЃЊиЃ°еЄИдїђеЬ®иЃЊиЃ°дљЬеУБжЧґжАЭиАГжЬАе§ЪзЪДжШѓиÚ襀姲дЉЧжЙАжО•еПЧзЪДдЄЬи•њпЉМжГ≥зЭАпЉЪвАЬдљњзФ®иАЕдЄАеЃЪдЉЪиІЙеЊЧињЩдЄ™иЃЊиЃ°еЊИеЗЇиЙ≤зЪДпЉБвАЭдїЦиЃЊиЃ°дљЬеУБжЧґеП™жШѓеЄМжЬЫиÚ襀姲дЉЧжЙАжО•еПЧгАВзЫЄеПНпЉМиЛ•жШѓеЗЇдЇОдљњзФ®жЙАйЬАиЃЊиЃ°дЇЖдЄАж†ЈдЄЬи•њпЉМиАМеП¶дЄАдЄ™дЇЇйЭЮеЄЄеЦЬзИ±пЉМдЇОжШѓдєЯж®°дїњзЭАеОЯж†ЈеБЪдЇЖдЄ™зЫЄдЉЉзЪДдЄЬи•њгАВињЩж†ЈпЉМеРМдЄАдЄ™иЃЊиЃ°е∞±еГПйУЊжЭ°дЄАж†ЈдЉ†жТ≠еЉАжЭ•пЉМињЩзІНиЃЊиЃ°еПѓдї•зІ∞дєЛдЄЇжЧ†еРНзЪДиЃЊиЃ°гАВиЃЊиЃ°жШѓдЄАзІНжЬЙзЫЃзЪДзЪДеИЫйА†жАІжіїеК®пЉМMUJIе∞±жШѓеЊИе•љзЪДдЊЛе≠Р гАВ
MUJIжЬђиЇЂдєЯдЄАзЫіеЬ®жФєйЭ©
жЬ±йФЈпЉЪеЊИе•ЗжА™пЉМMUJIеЬ®жђІжі≤дЄНе¶ВеЬ®дЇЪжі≤еПЧ搥ињОгАВ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MUJIеЬ®зЇљзЇ¶ињШжѓФиЊГеПЧ搥ињОпЉМеЫ†дЄЇйВ£йЗМжЄЄеЃҐдЉЧе§ЪгАВеЬ®жђІжі≤еЉАзЪДеЇЧеЊИе∞ПпЉМжѓФе¶ВзСЮеЕЄзЪДеЇЧиЃЊеЬ®еЊИе§ІзЪДеєњеЬЇжЧБиЊєзЪДдЄАдЄ™иІТиРљпЉМйВ£йЗМж†єжЬђж≤°дїАдєИдЇЇгАВеЫ†дЄЇ MUJIиЈЯеМЧжђІй£ОжГЕзЪДдЄЬи•њеѓєжѓФпЉМеЃГзЪДз≤ЊиЗіеЇ¶дЄНе§ЯгАВжѓФе¶ВпЉМжИСдїђеЄЄзФ®зЪДжіїеК®йУЕзђФпЉМдЇЇж∞СеЄБ7еЕГпЉМйУЕиКѓеЃєжШУжЦ≠гАВеЫ†дЄЇдљњеКЫзЪДеЬ∞жЦєж≤°жЬЙеК†еЫЇпЉМдљЖеЊЈеЫљзЪДеУБзЙМе∞±дЄНдЄАж†ЈпЉМеЃГдЉЪеЬ®йЗМйЭҐзФ®йЗСе±ЮеК†еЫЇгАВињЩе∞±еПЂеУБиі®пЉМеПѓжШѓMUJIж≤°жЬЙињЩж†ЈзЪДеУБиі®гАВжИСиІЙеЊЧMUJIзЪДиЃЊиЃ°еЄИеЬ®иЃЊиЃ°зЪДжЧґеАЩж∞іеє≥ж≤°иЊЊеИ∞йВ£дЄ™е±Вжђ°пЉМиАМдЄФйВ£ж†ЈеБЪе∞ЖеҐЮеК†жИРжЬђгАВеєґдЄФпЉМMUJIеЊИе§ЪдЇІеУБињШжШѓеЬ®дЄ≠еЫљгАБиґКеНЧгАБж≥∞еЫљзФЯдЇІзЪДгАВ
жЬ±йФЈпЉЪжИСдЄНиІЙеЊЧMUJIиЃ§иѓЖдЄНеИ∞ињЩзВєгАВдЄНиЃЇељУеєіжИЦжШѓзО∞еЬ®зЪДMUJIйГљдЄНжШѓдЄАдЄ™йЂШзЂѓеУБзЙМпЉМиѓіеИ∞еЇХжШѓдЄАдЄ™дЄ≠зЂѓзЪДгАВеЬ®дЄ≠еЫљпЉМеͳ襀жНІжИРдЇЖйЂШзЂѓдЇІеУБгАВ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еЕґеЃЮпЉМжЬАжЧ©зЪДMUJIеЊИеНХзЇѓпЉМеЊИеЃЮеЬ®пЉМеЬ®еИЂзЪДеХЖеУБдЄ≠дЄАдЄЛе∞±иЈ≥еЗЇжЭ•дЇЖгАВMUJIеРНе≠ЧжЬђиЇЂдєЯеЊИеОЙеЃ≥пЉМжЧ†еН∞иЙѓеУБвАХвАХињЩе∞±жШѓжЬАе•љзЪДдЄАдЄ™еХЖж†ЗгАВињЩеРНе≠ЧиЃ©дЇЇжЬЙе•ље•ЗжДЯгАВињЩжШѓдїАдєИпЉЯж≤°еХЖж†ЗпЉЯињЩдЄНжШѓжЬЙеРЧпЉЯеЖНзЬЛзЬЛеХЖеУБйГљжШѓдЄАдЇЫеЊИжЬізі†зЪДе∞ПзђФиЃ∞жЬђгАБеЬЖзП†зђФгАБдЄАдЇЫзФЯжіїзФ®еУБпЉМдєЯдЄНиіµпЉМеПѓдї•дє∞еЫЮеОїзФ®пЉМзФ®еЃМеЖНињЗжЭ•дє∞гАВжЕҐжЕҐзЪДпЉМдєЯиГљзЬЛеИ∞еЃГзЪДеПШеМЦгАВй£ЯеУБжЭ•дЇЖпЉМзБѓеЕЈдєЯжЭ•дЇЖпЉМеЮГеЬЊж°ґдєЯжЭ•дЇЖпЉМй£ЯеУБжѓФе§ЦйЭҐеНЦзЪДињШдЊњеЃЬгАВзФЯжіїдЄ≠иГљжГ≥еИ∞зЪДеЃГйГљжЬЙпЉМMUJIжЬђиЇЂдєЯдЄАзЫіеЬ®жФєйЭ©гАВ
жЬ±йФЈпЉЪ2001еєідєЛеЙНзЪДжЧ†еН∞еТМдєЛеРОзЪДжЧ†еН∞жЬЙеЊИе§ІеПШеМЦгАВеИЫеІЛдЇЇдєЛдЄАзЪДзФ∞дЄ≠дЄАеЕЙпЉМеЬ®еОїдЄЦеЙНжЙЊеИ∞дЇЖиЃЊиЃ°еЄИеОЯз†ФеУЙдљЬдЄЇжО•зП≠дЇЇгАВеОЯз†ФеУЙеЬ®дЇІеУБжЬђиЇЂзЪДиІДиМГжАІдЄКиµЈдЇЖеЊИе§ІзЪДдљЬзФ®гАВдї•еЙНзЪДMUJIзЪДжДЯиІЙжШѓвАЬйЗНвАЭзЪДпЉМеМЕжЛђжХідЄ™иЙ≤з≥їгАБзФ®жЭРйГљеЊИйЗНпЉМдљЖжШѓжФєйЭ©дєЛеРОзїЩдЇЇзЪДжХідљУжДЯиІЙйГљжШѓвАЬиљївАЭзЪДгАВйАПжШОзЪДеОЛеЕЛеКЫзЪДе§ІйЗПдљњзФ®пЉМиЃ©дЇІеУБеЊЧеИ∞еЊИе§ІжФєеПШгАВдљЖжШѓпЉМжЧ†еН∞зЪДж¶Вењµж≤°жЬЙдїАдєИжФєеПШгАВзЫЃеЙНпЉМеЫізїХеЬ®жИСдїђзФЯжіїеС®иЊєзЪДеХЖеУБеЈ≤зїПдЄ§жЮБеМЦпЉМдЄАзІНдї•дЇІйЗПзЪДз®Ае∞СжАІгАБж≥®йЗНжПРйЂШеУБзЙМиЗ™иЇЂдїЈеАЉдЄЇжЦєеРСпЉЫеП¶дЄАзІНзЂ≠е∞љжЙАиГљжО®и°МдљОдїЈз≠ЦзХ•гАВжЧ†еН∞иЙѓеУБеИЩеЬ®зФЯжіїзЪДвАЬеЯЇжЬђвАЭ дЄОвАЬжЩЃйБНвАЭйЧіеѓїеЊЧжЦ∞зЪДдїЈеАЉиІВпЉМеЬ®йА†еЮЛзЪДвАЬжЬізі†вАЭдЄОвАЬзЃАзЇ¶вАЭдЄ≠е°СйА†еЗЇдЇЖжЦ∞зЪДеЃ°зЊО嚥еЉПгАВ
еПѓдї•жГ≥еГПдЄАдЄЛпЉМе¶ВжЮЬжЧ†еН∞иЙѓеУБињЩдЄАж¶ВењµжШѓеЬ®еЊЈеЫљиѓЮзФЯпЉМдЉЪжШѓжАОж†ЈзЪДеХЖеУБпЉЯеЬ®жДПе§ІеИ©иѓЮзФЯеПИдЉЪе¶ВдљХпЉЯжЫійЗНи¶БзЪДжШѓпЉМеЖНжГ≥еГПдЄАдЄЛпЉМиЛ•жШѓеЬ®зФЯжіїжДПиѓЖйАРжЄРжИРзЖЯзЪДдЄ≠еЫљйЗМпЉМжЧ†еН∞иЙѓеУБдЉЪе±ХзО∞жАОж†ЈзЪДжЩѓи±°еСҐпЉЯжИСиІЙеЊЧпЉЪињЩзІНзЬЛдЉЉеє≥еЄЄзЪДжГ≥еГПеЬ®дїКжЧ•йЭЮеЄЄйЗНи¶БгАВжЧ†еН∞иЙѓеУБпЉМжЧ†зЦСжШѓдЄЇжИСдїђжПРдЊЫдЇЖйЂШеЇ¶зЪДж†ЗжЭЖеТМеПѓдЊЫеПНзЬБзЪДйХЬе≠РгАВ
жККеє≥еЗ°зЪДдЇЛжГЕеБЪеИ∞жЮБиЗ≥
еЯОеЄВзФїжК•пЉЪе¶ВжЮЬеЬ®дЄ≠еЫљеЗЇзО∞дЄАдЄ™еГПMUJIињЩж†ЈзЪДеУБзЙМпЉМеЃГеЇФиѓ•дЉЪжШѓдїАдєИж†ЈпЉЯ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еЊИйЪЊгАВй¶ЦеЕИпЉМдЄ≠еЫљдЄНжШѓеНХдЄАж∞СжЧПпЉМе∞±жШѓжГ≥дЇЛзЪДжЧґеАЩдЉЪжГ≥еИ∞и¶БиЃ©е§ІеЃґйГљиГље§ЯжО•еПЧгАВ
жЬ±йФЈпЉЪдїОеМЧдЇђе••ињРдЉЪзЪДеЉАеєХеЉПдЄКпЉМжИСе∞±еПСзО∞йЭЮеЄЄеЉЇзГИзЪДдЄАзВєпЉМе∞±жШѓдЄ≠еЫљињЩдЄ™ж∞СжЧПзЬЯзЪДдЄНжШѓеіЗе∞ЪжЮБзЃАдЄїдєЙзЪДгАВжБ∞жБ∞зЫЄеПНпЉМдЄ≠еЫљжЙАжО®еіЗзЪДпЉМиГљеРСе§ЦзВЂиААзЪДжШѓеЃГзЪДе§НжЭВжАІгАВжЦЗеМЦпЉМжШѓжМЗеЬ®иЗ™еЈ±еЗЇзФЯзЪДеЬЯеЬ∞дЄКе¶ВдљХеПСжМ•иЗ™иЇЂзЪДзЛђеИЫжАІгАВеЬ®зЛђдЄАжЧ†дЇМзЪДжЬђеЬЯжЦЗеМЦзОѓеҐГдЄЛеИЫйА†еЗЇжЭ•зЪДдЄЬи•њпЉМеЖНе∞ЖеЕґжФЊеЬ®еЫљйЩЕеє≥еП∞дЄКпЉМињЩж†ЈжЙНдЉЪдї§дЇЇиА≥зЫЃдЄАжЦ∞гАВжЙАдї•жЬђжЭ•е∞±дЄНе≠ШеЬ®жЙАи∞УвАЬеЫљйЩЕжАІжЦЗеМЦвАЭпЉМдєЯиЃЄдї•еРОдЉЪжЕҐжЕҐеЗЇзО∞пЉМдљЖжШѓзЫЃеЙНжИСдїђеП™иГљзЬЛеИ∞дЇТзЫЄжѓФиЊГињСдЉЉзЪДжЦЗеМЦгАВеПНдєЛпЉМе¶ВжЮЬе§ЪзІНжЦЗеМЦжЈЈеРИзЪД姙еОЙеЃ≥пЉМеБЪеЗЇжЭ•зЪДдЄЬи•ње∞±дЉЪеПШеЊЧдЄ≠жАІгАВжИСиЃ§дЄЇпЉМжЙАи∞УеЫљйЩЕдЇ§жµБпЉМе∞±жШѓи¶БжККеЬ®иЗ™еЈ±еЫљеЬЯдЄКеЯєеЕїзЪДжЦЗеМЦпЉМеЬ®жБ∞ељУзЪДжЧґеАЩеНБеИЖжЮЬжЦ≠еЖ≥зїЭеЬ∞жФЊеИ∞дЄЦзХМеє≥еП∞дЄКеОїгАВжИСжГ≥йАЪињЗе±ХиІИзЪДеИЇжњАпЉМжЭ•жњАеПСдЄ≠еЫљзЪДдЇІдЄЪдЇЇпЉМиЃЊиЃ°еЄИдїђжЫіе§ЪеПСзО∞дЄ≠еЫљиЗ™иЇЂвАЬеОЯзВєеТМеОЯеЮЛвАЭжљЬеЬ®зЪДеПѓиГљжАІгАВжИСжЫіеЄМжЬЫињЩдЄ™е±ХиІИпЉМиГљиЃ©дЄ≠еЫљзЪДдЇІдЄЪдЇЇпЉМиЃЊиЃ°еЄИжДПиѓЖеИ∞еП™жЬЙжККиЗ™еЈ±еЃЪдљНдЇОдЄАдЄ™еЬ®дЄ≠еЫљињЩж†ЈзЛђзЙєзЪДжЦЗеМЦзОѓеҐГйЗМеЈ•дљЬзЪДпЉМдї•ињЩж†ЈзЪДдЄ™жАІеОїеЕ≥ж≥®дЄ≠еЫљзЪДвАЬеОЯзВєеТМеОЯеЮЛвАЭпЉМжЙНдЉЪжЬЙз™Бз†ігАВеѓєжИСжЭ•иѓіпЉМз≠ЦеИТвАЬжЧ†еН∞иЙѓеУБ2008дЄ≠еЫље±ХвАЭпЉМжЙАи¶Бињљж±ВзЪДе∞±жШѓеЄМжЬЫдЄ≠еЫљзЪДдЇІдЄЪдЇЇеТМиЃЊиЃ°еЄИпЉМиГљеПЧеИ∞жЧ†еН∞иЙѓеУБињЩдЄ™ж†ЗжЭЖеТМйХЬе≠РзЪДеРѓз§ЇпЉМеЫЮе§іжЭ•жЄЕзРЖеЯЛеЬ®иЗ™еЈ±иДЪдЄЛзЪДвАЬиЗ™иЇЂдїЈеАЉвАЭгАВ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дЄ≠еЫљеЕґеЃЮжШѓдЄАдЄ™еЊИдЄЦдњЧзЪДеПЧдЉЧгАВе§ЪжХ∞дЇЇйЬАи¶БиІ£еЖ≥зФЯжіїдЄКзЪДйЧЃйҐШпЉМињШдЄНдЉЪжЬЙеЊИе§Ъз≤Њз•ЮдЄКзЪДињљж±ВгАВзЬЛе••ињРдЉЪдєЯжЬЙеЊИе§ЪеРѓз§ЇпЉЪељУињРеК®еСШжЛњеИ∞дЄЦзХМзЇІзЪДеЖ†еЖЫпЉМдїЦињЩдЄАзФЯзЪДиН£иААзФ±еОЖеП≤еЖ≥еЃЪгАВиґКжШѓзЙ©иі®дЄ∞еѓМгАБиґКжШѓйГљеЄВеМЦгАБиґКеШИжЭВеТМдЄЦдњЧзЪДж∞ЫеЫідЄ≠пЉМдљ†и¶БжЛњеИ∞жИРзї©пЉМе∞±дЄАеЃЪи¶БжККиЗ™еЈ±еЕ≥еЬ®еНХзЇѓзЪДзОѓеҐГйЗМзФЯжіїгАВ
еЯОеЄВзФїжК•пЉЪдљЖжШѓдљ†зЪДдЇІеУБеНЦдЄНеЗЇеОїпЉМеЫ†дЄЇдЄНдЄЦдњЧгАВ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еП™жЬЙдЄЦдњЧжЙНиГљеНЦеЗЇеОїеРЧпЉЯдЄНжШѓињЩж†ЈзЪДгАВжЙАжЬЙдЇЇйГљињЩдєИжГ≥зЪДиѓЭпЉМжХідЄ™з§ЊдЉЪе∞±йГљжШѓдЄЦдњЧзЪДгАВдљ†дЄЦдњЧеПИжАОдєИеПЦеЊЧжИРзї©еСҐпЉЯдЄЦдњЧеПИжАОдєИдЉЪжЬЙжЧ†еН∞еСҐпЉЯжЧ†еН∞е∞±дЄНжШѓдЄЦдњЧпЉМжЧ†еН∞е∞±жШѓењНиАРгАВеТ±дїђеѓєз≤Њз•ЮдЄКж≤°жЬЙи¶Бж±ВпЉМеЊИе§Ъе•љзЪДдЄЬи•њеИ∞жЬАеРОйÚ姱䊆дЇЖгАВеТ±дїђжЬЙдє¶ж≥ХпЉМжЧ•жЬђжЬЙдє¶йБУпЉМеТ±дїђжЬЙеЉУжЬѓпЉМдЇЇеЃґдєЯжЬЙеЉУйБУгАВ
еЯОеЄВзФїжК•пЉЪMUJIдЄНдЄЦдњЧпЉМдљЖеЬ®еХЖдЄЪдЄКињШжШѓеЊИжИРеКЯпЉЯ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ељУзДґжИРеКЯпЉМжАОдєИдЉЪдЄНжИРеКЯеСҐпЉЯдЄНжИРеКЯжИСдїђдїК姩жАОдєИдЉЪиЃЃиЃЇеЃГпЉМдљ†зЪДиЃЃиЃЇе∞±жШѓжИРеКЯгАВдїАдєИжШѓжИРеКЯпЉМе∞±жШѓи¶Биµ∞дЄ§е§іпЉМдљ†дЄНиГљеЬ®дЄ≠йЧіпЉМи¶БдєИжЬАе•љи¶БдєИжЬАеЭПгАВзЬЛзЬЛжЧ•жЬђзЪДжЬЇеЩ®зМЂпЉМдЇЇеЃґзЪДжЬЇеЩ®зМЂдїО60еєідї£еЗЇжЭ•зЫіеИ∞зО∞еЬ®ињШдЄАзЫіеЬ®еЗЇпЉМињЩе∞±жШѓеЭЪжМБгАВдЇЇеЃґеБЪеПШ嚥йЗСеИЪпЉМеЗЇдЇЖеНБдЇФдЇњдЄ™пЉМдљ†зЯ•йБУеБЪдЇЖе§Ъе∞СйТ±еРЧпЉЯињШжЬЙPR жГЕжК•жЭВењЧпЉМдїО70еєідї£еИЫеИКеИ∞зО∞еЬ®пЉМе∞±дЄАдЄ™дЇЇеЬ®зФїе∞БйЭҐвА¶вА¶ињЩе∞±еПЂжЮБиЗ≥пЉМжККжЩЃйАЪзЪДдЇЛжГЕеБЪеИ∞жЮБиЗ≥гАВдЄ≠еЫљињШжЬЙжЮБиЗ≥еРЧпЉЯжЧ©е∞±жНҐдЇЖгАВ
жЬ±йФЈпЉЪжЧ•жЬђзЪДдєМйЊЩиМґпЉМеБЪињЩдЄ™дЇІеУБзЪДеєњеСКеЕђеПЄеБЪдЇЖ25еєіпЉМиГљдЄНеБЪе•љеРЧпЉЯ
еЯОеЄВзФїжК•пЉЪжЬЙдЇЫдЇЇеЉАдЄАеЃґе∞Пе∞ПзЪДеЇЧпЉМзЙєеИЂдЄУењГеБЪиЗ™еЈ±зЪДдЇЛжГЕпЉМеПѓдї•еБЪдЄАиЊИе≠РгАВ
жЦєжМѓеЃБпЉЪеѓєпЉМињЩе∞±жШѓдєРиґ£гАВдЄ≠еЫљзО∞еЬ®зЉЇдєПзЪДе∞±жШѓињЩдЄ™з≤Њз•ЮгАВеЫ†дЄЇз§ЊдЉЪжШѓзФ±еЊИе§Ъе∞ПзЪДйГ®еИЖзїДжИРпЉМељУжѓПдЄ™дЇЇеК™еКЫеБЪдЄАдїґдЇЛжГЕпЉМз§ЊдЉЪе∞±жПРйЂШдЇЖгАВељУжѓПдЄ™дЇЇйГљеЊИжЗТжГ∞гАБйГљеЬ®з≠ЙеЊЕзЪДжЧґеАЩпЉМе∞±ж≤°жЬЙињЫж≠•гАВ
жЬ±йФЈпЉЪдЄАдЄ™дЇЇпЉМеЭЪжМБжККдЄАдїґжЩЃйАЪзЪДдЇЛеЄЄеєізіѓжЬИзЪДеБЪдЄЛеОїпЉМеБЪеИ∞жЮБиЗ≥пЉМжШѓдЄАзІНз≤Њз•ЮгАВ
 RSS
RSS